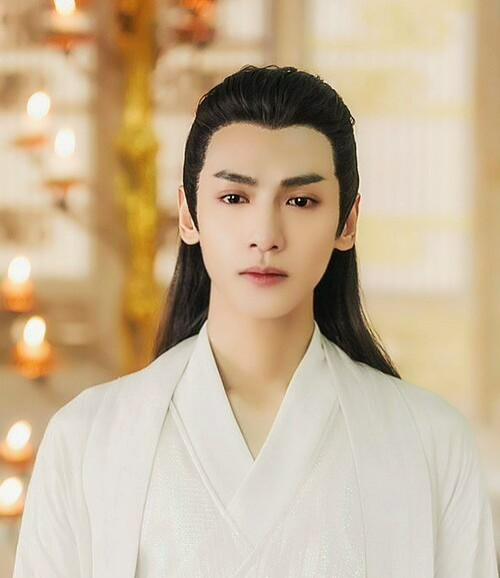詩詞優美的意境和辭藻,曆經千百年的時光,依舊讓人沉醉迷戀;字裡行間的故事和詩意,也吸引着後世不斷探尋詩中的智慧和哲思;自然流暢的言語和新奇貼切的修辭,往往令讀者歎為觀止。這一切的美好,都是詩人淵博的學識、過人的天資,以及精心的設計,在背後作為支撐。

毫無疑問,詩詞是藝術品,如果不精心設計,即便是有堯舜之德、孔孟之仁、孫吳之智,也無法将其完美呈現出來,所以古代詩人常說,“吟安一個字,撚斷數根莖”,畢竟,像李白那般鬥酒詩百篇的天才,數千年也隻有一個。
唐代的賈島,便非常注重煉字,這也是詩詞設計的一環。因為詩詞篇幅短小,優秀的詩人,往往能夠用幾個字的組合,傳達更豐富的内涵,和深邃隽永的意境,雖然“一句三年得”有些誇張,不過反複的錘煉,還是很有必要的。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也擅于作詩,他有一首非常著名的絕句,曾被選入語文教材,是千古傳誦的名篇,此詩便是《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隻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詩的首句,藝術手法有些像李白的《早發白帝城》,以“一水間”來形容船速之快,江潮之急,這句雖然沒有寫風,但有風的身影,好風憑借力,所以才能船隻才能如此之快。
第二句,則是對鐘山的眷戀。數重山,對于古代的交通來說,應該是一個比較遠的距離,但王安石卻用了一個“隻”字,在他眼中,這個距離是非常短的。鐘山便是江甯的鐘山,這是他曾經和父親定居的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

第三句則是說春風再一次拂過,江南千裡之岸,草木煥發生機,盡顯醉人之綠。同時,這又是運用了比興的手法,以春風吹綠,比喻他二度拜相,能夠推行新法,這種心情,十分含蓄的寄寓在了這一句中。
不過王安石心中還是有很大的顧慮,前度被罷相,已經讓他領略到了新法推行的阻礙,這再次進京,難道就能順利推行嗎?他不知道,雖然王安石一定會拼盡全力,不過很多事情,并非努力就有好的結果,最多是不讓自己留遺憾罷了,所以最後一句,王安石自問何時能夠功成身退,告老還鄉。

這首詩第三句的“綠”字,素來為人稱道,洪邁的《容齋續筆》,記載了王安石作這首詩的情景:
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雲“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複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
意思就是說,蘇州有位讀書人,家裡有王安石寫此詩的詩稿,王安石開始使用了“又到江南岸”,但覺得“到”不好,後來陸陸續續改了十幾個字,最終用了“綠”字。這個故事,流傳至今,成為詩歌史煉字的典範,但這個“綠”用得究竟好不好呢?
錢鐘書在《宋詩選注》說道:
但“綠”字這種用法在唐詩中早見而亦屢見,丘為《題農父廬舍》:“東風何時至?已綠湖上山”;李白“東風已綠瀛洲草”;常建“主人山門綠”。

錢鐘書用了一個“但”字,其中轉折之意,足見他對王安石“綠”的不以為然,并且說這種用法,在唐代屢屢可見,不算什麼創新。而且王安石跟李白的這一句結構,非常相似,不過是把瀛洲草換成了江南岸。
所以錢鐘書又在後面發出了一系列的疑問:
王安石反複修改,是忘記了唐人的詩句而白費心力呢?還是明知道這些詩句,而标新立異呢?他選定的“綠”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想起了唐人詩句而欣然沿用呢?還是自覺不能出奇制勝,終于向唐人認輸呢?
其實,這段話中,錢鐘書已給出答案。
王安石是博學出了名的,史載他“酷愛讀書、過目不忘”,而且活用“綠”字的唐詩比比皆是,若說他會忘記,在十分注重詩文的北宋,可能性很小。所以,第三個疑問“暗合”,也就是在不知情況下而與前人相合,可能性亦微乎其微。

第三個,标新立異,也可以否認,前文已分析,這句詩和李白的詩相比,除了替換詞彙,并無獨到之處。最後一個,王安石外号“拗相公”,什麼事都要争赢,前人寫詩“卷土重來未可知”,他偏要寫“肯與君王卷土來”,所以他怎麼會輕易認輸,唯一的答案,就是王安石沿用前人之句。
錢鐘書所表達的,便是王安石大的“綠”字并不新奇,對于這首詩,還是肯定的,隻是認為“綠”字沒必要大誇特誇。對此,臧克家說得更為直接:
但我嫌它太顯露,限制了春意豐富的内涵,扼殺了讀者廣闊美麗的想象。

雖然,這“綠”字,能夠給人以色彩鮮明的感覺,但藏克家認為還是太過直白。因為春天是豐富多彩、絢爛多姿的,花有百色、柳帶煙籠,王安石一個“綠”字,卻給春天定了性,使讀者腦海裡出現了一片“綠”的春天,但卻失去了一個繁花似錦、煙花三月的春天。
但我認為,無論這個“綠”字是否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都無法否定這首詩在文學中的地位。王安石描寫的,不僅是春風春景,更是懷着新法能夠一掃弊端,為北宋吹入一股春風,能夠讓百姓安居、國富民強。縱使此詩不能追逐“李杜陶謝”,但其中蘊含的精神,依舊能夠在千年的時光中,經久不衰,口口相傳。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