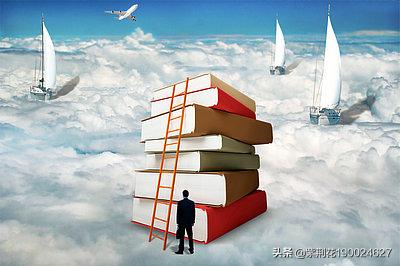本文作者: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李洪财,原文發表在《書法研究》2021年第1期。
本文已獲得作者授權,原文為繁體字,今轉為簡體,引用請參考原文。
内容提要:漢簡數量大,内容豐富,形式多樣,書寫情況相對複雜。本文通過舉例的方式歸納總結漢簡中特殊的書寫現象,揭示漢簡草書的符号化特點、筆畫拉長現象、避複現象,以及漢簡中的狂草與人名特殊寫法等問題。
關鍵詞:漢簡、符号化;避複;狂草;畫押
目前出土簡牍中數量最大的是漢簡。因為數量大,内容豐富,書寫情況也相對複雜多樣。我們曾專文讨論漢簡中的合文、連寫等特殊情況。[1]除此外還有不少特殊書寫現象值得進一步剖析,這對于深入考察漢代文書形制、書寫方式、草書構形演變,以及漢代簡牍書法的研習與創作都有重要指導意義。
一、書寫符号化文字符号化是漢簡草字簡化中非常顯著的特點。這在一些讨論漢代草書的論著中都多少有所言及,比如陸錫興《漢代草書概說》[2]、李洪智《談談草書符号》[3]等。我們這裡避開一些已有讨論或者比較常見的問題,主要介紹一些以前言之未盡或者比較特殊的問題。
由于書寫草率漢簡中很多比較常見的字或詞有時會簡省成符号,例如:

像上面簡中的隧、長,如果脫離開簡文很難釋讀出來。可以看出,這些字形已經失去了本字構形特征,簡化成符号。像這種簡化在漢簡中還有很多,上舉字形還能勉強看出一些本字的痕迹,還有些符号化的字完全看不出任何本字痕迹,例如:

上面這幾個字形如果脫離開簡文,很難準确識讀出來。上舉第一簡中的“騎”還能看出左側的“馬”形,但右側完全符号化作一短豎,已看不出與“奇”字的形體演變聯系。第二支簡肩73EJT3:7(見圖1)的符号化就更離譜了,整支簡中的“騎”字全部都書寫作符号,如果沒有簡文内容,完全看不出是“騎”字。

圖1
還有一些常見的慣用語也常書寫成符号。所謂慣用語就是簡牍行文中常出現的一些比較固定的短語,通常是一些禮貌、問候、寒暄類詞語。在漢簡中慣用語出現的頻率非常多,常以草字書寫。甚至在一些書寫比較工整的簡牍中,慣用語也常以草字書寫。慣用語的書寫很多已經完全符号化,如果将慣用語中的每個字分開,其中符号化的字就無法識别,例如:

上面這幾支簡中的常用語,在漢簡中比較常見,如果不看簡文内容,隻看字形很難識别出是什麼字。因為這些字都已經符号化,所以不能用分析正規文字的寫法來分析判斷。而且這些符号寫法,一般也隻有在固定的慣用語中才寫得這麼簡化,如:

其中“再拜”兩字寫法隻有在兩字同時出現時才如此簡寫。“叩頭”簡化得就更嚴重了,“頭”字基本上是一筆帶過了,但也隻有在“叩頭”兩字連用才這樣寫。離開具體文例限定,很少見到草化到這種程度。如果簡化得過大,脫離開相應的内容後,就容易誤讀,比如:

肩73EJT10:470中的“甚”,靠字形和文義都很難識别,隻有對漢簡中所有的“甚”字草寫情況有充分了解,才能釋讀出來。居140·4B簡中的“幸”,《居延漢簡甲乙編》[1]誤釋作“又”,這應該就是脫離常見的“幸甚”内容後,形體過于簡單造成的混淆誤認。

漢簡文字末筆拉長的現象非常多見,陸錫興曾經在《釋“卩”》中專門研究總結過拉長筆劃的各種情況。文中認為漢簡的長筆主要與簡文停頓配合,隻要是句讀停頓,就可用長筆,所以長筆又不限于行末。[1]我們也很贊同這種觀點,不過我們認為漢簡中長筆現象,應該還有個人的書寫習慣,和有意的增加裝飾趣味原因,例如:

這三支簡從内容和書寫特點上可以确定,應該是同一個人書寫的。漢簡中比較正常的“護”草寫作

(居補·L1)
最後的捺劃與上面所舉字形處理方式完全不一樣。上舉幾個“護”形應該屬于個人的書寫習慣,也可以說是個人書寫上的主觀裝飾。同樣的拉長筆劃有些末端的處理方法也不一樣,而且拉長的筆劃也不一定是末筆,如:

這幾個字形中有些長筆末端急促收起,形成勾劃,而且同樣的勾劃處理方法也不一樣。令、半的勾劃是急促挑起,“唯”的勾劃則是先緩和彎曲然後再挑起。并且,拉長的筆劃也不是全都向下,也有向兩側的,比如物寫作

(居4·1)
這是向佐拉長撇劃。這些情況如果不是書寫者自覺的創造,很難在無意中就形成這種效果。所以說,長筆使用很大原因是個人審美的需要,也不一定就在句讀停頓和末尾補空處使用。

筆劃拉長現象與簡牍形制有一定關系。陸錫興文中說漢簡中為了末筆拉長要改變筆劃,橫劃改為捺劃,彎折改為豎筆。實際也确實如此,不過改變筆劃方向也不一定隻是為了向下拉長,有些應該是受簡牍限制造成的。例如上舉敞、政、教、取,這些字拉長筆劃确實都改變了行筆方向。按照後世草書的書寫習慣這些字一般不會這樣誇張處理,這種情況唯獨漢簡中頻繁出現,有些應該是受簡牍形制書寫方式的影響。尤其是第一個“敞”字,明顯可以看出受右側空間限制,改變了行筆方向轉向下行筆。可以推想,書寫者在書寫“敞”字時,想拉長筆劃來表達個人的書寫情趣,但是簡牍的特點限制隻能迫使筆劃向下。

圖2、王獻之《思戀帖》

圖3、蘇轼《寒食詩帖》
漢簡中這種拉長筆劃頻繁出現,最初應如陸錫興文中所說,是在語句停頓處或者在末尾補空,發展以後可能多數是個人書寫習慣和審美趣味的原因了。後來草書定型後,這種方法也被繼承下來。我們後世很多書法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這種拉長筆劃的寫法。例如圖2和圖3兩種著名的法帖中,就有這種長筆現象。因此,這種筆劃拉長現象,既是後世草書相同寫法之源,也是漢代書寫審美意識提高和書法自覺性越來越明顯的體現。
三、漢簡中的“狂草”按照以往研究,漢簡草字屬于章草範圍,這樣歸屬常把漢簡草字中的一些特殊現象忽略掉了。下面讨論漢簡中的“狂草”就屬于被忽略的情況。先舉幾個單字“狂草”的例子,如:

上面這些字形無論在簡省程度,還是用筆圈轉纏繞上,都遠遠超過了傳統意義上的章草特點。甚至在東晉二王年代的今草中,這種書寫開張、纏繞程度也不多見,而在後世的狂草中才比較多見。如果這些單字不能說明“狂草”的程度的話,舉兩個比較完整簡牍例子:
請使奉诏伏地再拜(肩73EJT6:44A)
□尊止謝卿(居新EPT52·385B)

圖4、肩73EJT6:44A

圖5、居新EPT52·385B
從第一支肩73EJT6:44A(圖4)原簡圖中可以看到書寫者有意的安排了穿插、避讓、筆劃的粗細變化,第二支簡圖5筆劃的纏繞、開張大氣,這些絕不是偶然能做到的,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章草、今草所能輕易見到的。這種“狂草”的情況在漢簡中雖然不多見,但是絕不是個别一兩例而已。或者說,這些漢簡堪稱開後世“狂草”之先。
四、避複現象漢簡中已經有了明顯的書法審美自覺性。這有很多現象可以說明,比如書寫中的避複現象就是其一。所謂避複就是在書寫中遇到相同重複的字,為了減少書寫無變化産生的呆闆平庸,通過改變重複字寫法來增加文字美感或變化性的現象。避複在漢簡之前的古文字中就有了,到了漢簡中,這種現象顯得更加突出,更能顯出人為主觀意識因素。例如:


圖6

圖7
第一支敦837簡(圖6),這支簡書寫比較特别,簡中很多字都重複出現,例如簡中内、餘、升,兩次出現的形體全部變化了結構,不僅這個字,簡中其他字也都有意的變化了大小、筆劃粗細,隻是沒有這幾個字明顯。這應該不是無意造成的。還有第二支額濟納簡(圖7),“督蓬”兩字相鄰并排出現,如按照正常無意識書寫,一般兩字都會書寫得比較接近,但這支簡“督蓬”兩字都作了變化,可見是有意識的行為。像這種情況,在漢簡中比較常見。這也充分說明了漢代書法審美自覺性和審美意識的提高。
五、特殊的人名寫法我們在收集整理漢簡草字時,遇到很多人名用字釋讀問題。漢簡中的人名用字有兩個特殊現象,一是字形混同難辨,一是寫法怪異。
第一種主要是書寫不規範造成的混同難别。這種情況多數可以通過字形歸納對比解決釋字問題。但也有不少無法判斷的情況,例如:
【誤釋例】

敦1707A,《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認為“惠”應該釋作“竟”。[1],敦1797簡中的“惠”甘肅本[2]釋作“竟”字。其實這兩簡中的字,究竟是“竟”還是“惠”

第二種是寫法怪異的人名。這類草字主要是摻雜過多個人裝飾成分,書寫非常特殊,字形古怪難辨,如:

從簡文内容上看,這些簡中所舉字,可以非常确定用作人名。也可以看出,這些字形非常特殊,與漢簡中其他相同字寫法完全不一樣。總體上看,這些字形都帶有一些裝飾性,比如上面的“山”形,正常書寫中間的豎劃,一筆不容易寫出這個形狀,明顯是複筆特意寫出來的。還有“江”和“陽”形的彎曲筆劃,也都是特意寫出來的。這些特殊的人名寫法,也許就是書寫者在抄寫自己名字時或者遇到與自己名字相同的字時的特殊寫法,可能與後世的簽名類似,具有自己的個性裝飾色彩。不過由于這些人名用字具有特殊性,所以有些字很難識别,這和宋元時期流行的花押字一樣,很多隻有主人才能知道是什麼。漢簡中的人名用字有很多未釋情況,好在我們通過整個漢簡的梳理找到些可釋線索。

兩簡字形對比,可知就是相同的“裦”字。而且兩簡都用作人名,應該是同一個人名字的特殊寫法。
漢簡中文書簡居多,與典籍文獻内容簡牍相比,文書簡抄寫情況要複雜得多。但是文書簡大多内容不連貫,而且還有很多殘碎不完整的情況,如果不深入仔細考察每個字甚至每一筆的書寫情況,很多特殊現象就會被忽略掉。本文所說的特殊書寫現象隻是其中一部分,實際在漢簡中還有很多特殊的書寫現象值得去歸納總結,這對漢簡書法的研習與創作,文字構形的分析,漢簡釋文的整理都有重要意義。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