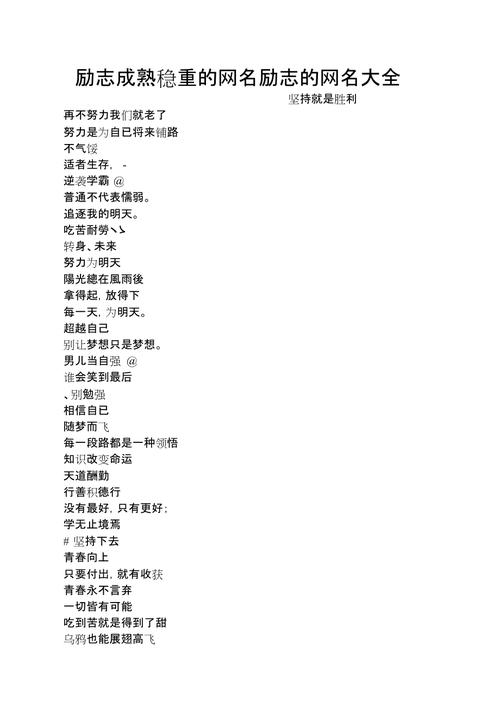2019年4月11日,廣州白水塘城中村。一名三歲的孩子因患神經母細胞瘤,治療要花費五十多萬,當時正通過水滴籌籌集醫療款,繼續做化療。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徐行/圖)
(本文首發于2019年12月19日《南方周末》)
截至2019年3月,水滴籌線下基層工作人員已擴大至三百多個片區經理,1.6萬多個志願者,覆蓋了中國400—500個城市。
水滴籌從一開始就不收任何手續費,籌款所得資金全部給予籌款人。好處就是能夠快速吸引流量。
水滴籌們能夠在短短幾年時間内狂飙突進,與法律尚無監管有關。
個人救助平台應将此業務獨立出來,由一個非營利組織來運行,與其他闆塊的業務往來必須明确規則。而無論采取哪種方式,向公衆披露必要的信息是基礎性義務。
近日,水滴籌因地推業務員被曝光“掃樓籌款”走上風口浪尖。
水滴籌于2016年7月上線,是目前中國最大的網絡大病互助平台。所謂大病互助,是指針對重症病人的網絡衆籌募捐行為。按照水滴籌披露的數據,截至2019年9月,水滴籌已累計為大病患者募得235億元的醫療救助款,近2.8億人支持了平台的救助項目,産生了超過7.5億人次的贈與行為。
在2019年1月舉行的水滴籌公益盛典上,水滴籌創始人沈鵬将水滴籌定位為一家社會企業,水滴籌也在近兩年多次獲得“社會企業”類獎項。
社會企業的目标是解決社會問題、增進公衆福利,而非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正是這種定位令許多人在“地推事件”爆發後,感覺自己被騙了,質疑水滴籌是将“公益做成生意”。
不過,在水滴籌官方最新回應中,沈鵬又明确向社會表明,水滴籌是一家商業公司,不是公益組織。
作為商業公司,水滴籌要通過地推等方式争搶流量,做大救助規模,才能通過後續諸如保險業務的開發實現盈利。
但商業與慈善之間的迷糊界限帶來的沖突,正在撕扯水滴籌。
被曝光的地推掃樓提成,在業内早就不是秘密,水滴籌等公司都擁有相當龐大的地推團隊。
2016年底,家住成都的楊琳成為水滴籌的一名“志願者”。她所在的西南片區是多家大病互助平台的“交火區”,這裡四五線城市密布、貧困人口衆多,對患病客戶的競争相當激烈。
名為志願者,實則是地推員。“叫志願者是為了好聽些,讓大家覺得我們在做公益,更容易被接受。”楊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據她回憶,自己所在片區的志願者最初大多是兼職,收入按照訂單數量提成,每單大約在50元。主要工作是在醫院蹲點發放傳單、尋找潛在的籌款發起人,有時還會承擔一部分審核工作。
志願者還得和醫院的宣傳部門、相關科室以及醫護人員搞好關系,這樣能夠打聽到一些病人的信息,比如某類疾病大概會花多少錢、又有哪個新病人住院了。“新病人都很搶手,因為患病時間不長,直接就可以排除掉已經在其他平台求助的風險。”楊琳說。
公開資料顯示,水滴籌陸續和不少醫院達成了戰略合作——醫院向水滴籌推薦在院治療的、經濟困難的大病患者,并協助驗證籌款所需資料,水滴籌則為大病患者提供籌款支持。在2019年1月舉行的水滴籌公益盛典上,水滴籌還向醫護人員頒發“向善天使”之類慈善獎項。
2017年之後,志願者之間的競争已相當激烈。楊琳說,不同平台在各家醫院都有據點,一些志願者通過買通醫院保安、壟斷醫院的相關科室來發展自己。志願者隊伍也迅速擴張,兼職的成了全職的,50元一單的價格上漲到了150元,每月不達标還要被淘汰。
楊琳親眼見過一家名為細雨籌的平台為了争奪單子,将提成拉升到八百多元一單,有的志願者一天拉了二十多單,當天就賺了一萬五千多元。但好景不長,細雨籌在2019年7月被爆跑路,病人籌款無法取現,被北京市工商管理局列入經營異常名單,如今該公司的官網已經無法打開。
在這場流量與地推的戰争中,存活下來的水滴籌進入行業第一梯隊。沈鵬在2019年接受采訪時介紹,除了在每個城市招募大量兼職人員和志願者輔導當地人籌款,他們還在各地農村做刷牆廣告。
水滴籌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3月,其線下基層工作人員已擴大至三百多個片區經理,1.6萬多個志願者,覆蓋了中國400—500個城市。水滴籌76%的籌款用戶來自三四五線城市,72%的捐款用戶來自三四五線城市。
水滴籌在地推業務上的摧枯拉朽或許與創始人沈鵬的個人經曆有關。他2010年就加入美團,成為公司10号員工。2013年美團與餓了麼之間爆發了“千團大戰”,美團赢得戰役靠的正是美團前COO幹嘉偉和美團前外賣負責人沈鵬等人所在的地推“鐵軍”。
在2019慧保天下保險大會上,沈鵬演講時稱,自己于1987年6月出生在中國人保家屬院。他的父親1985年就加入了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此後一直從事保險業直到2018年退休。而沈鵬的目标是“做更多傳統保險公司和保險中介不願意做的事情”。
水滴籌官方曾回應稱,水滴籌組建線下服務團隊的起因,是發現一些年紀偏大、互聯網使用水平較低的患者,在陷入沒錢治病的困境時,還不知道可以通過水滴籌自救。水滴籌向南方周末記者提供的數據是,40歲以上籌款人的比例占到七成左右。
激烈的市場争奪斬斷了平台審核的那根弦。
自媒體人梓泉在水滴籌事件曝光後做了一次實驗。2019年12月3日,他将自己用惡搞軟件修改後的病例發到了水滴籌上,打算籌款50萬元,病因是“精神分裂症”。
上傳診斷書和身份證信息後,梓泉編造了一段患病人的慘痛經曆,提交幾分鐘後系統自動将金額調成了10萬元。這時梓泉發現,雖然尚未完全通過審核,但自己已經可以先行籌款并轉發朋友圈衆籌,于是他象征性地捐了1元。
由于籌款數額過少,梓泉在2天内收到6條水滴籌的短信稱“籌款效果不佳”,建議其“加大力度轉發”。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完成1元捐款後,水滴籌彈出了一個水滴保險商城的頁面,建議捐款者購買保險。
在梓泉看來,這一設計相當巧妙,因為在看到籌款發起人的慘痛經曆後,無形中會給捐款人投射出一種焦慮,而要緩解焦慮的方法就是購買保險。
直到梓泉在自己的公衆号公開這一僞造的籌款前,水滴籌都沒有發現這一“騙局”。“籌款是12月3日發出的,直到12月10日,也就是公号文章發出的第二天下午3點,水滴籌才将這項籌款下線。”梓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此後,水滴籌發布了一份澄清說明,稱上述過程隻是初步審核,隻有進一步提交了醫療花費票據、出入院證明等資料後,才能實現籌款提現。水滴籌向南方周末記者提供的數據是,審核通過率為50%—60%。
即便通過審核,募集資金也有可能被挪作他用。
2019年11月6日,全國首例網絡個人大病求助糾紛在北京朝陽法院一審宣判。法院認定籌款發起人莫某隐瞞名下财産,并在水滴籌多個平台進行重複救助,違反約定用途将籌集款項挪作他用,構成違約,令莫某全額返還籌款153136元并支付相應利息。
朝陽法院同時向民政部、北京水滴互保科技有限公司(水滴籌運營主體)發送司法建議,推進相關立法、加強行業自律,建立網絡籌集資金分賬管理及公示制度、第三方托管監督制度、醫療機構資金雙向流轉機制等,切實加強愛心籌款的資金監督管理和使用。
龐大地推與審核漏洞背後,是一場關于流量的戰争。
實際上,網絡衆籌最初的賽道,距離公益或大病相去甚遠。2014年被稱為網絡衆籌元年,模仿美國知名衆籌平台Kickstarter的網絡平台相繼在中國出現。最初這類平台的衆籌項目包括購買智能硬件、拍電影、旅遊等等的各類項目,籌款的金額也多為幾十元到幾千元不等。
直到2015年底,一個名為“拯救創業攻城獅”的項目在輕松籌上“一炮而紅”。一位身患白血病的工程師僅一個晚上就籌集到三十餘萬元。
公益與衆籌的結合,讓輕松籌創始人楊胤看到了網絡衆籌的價值。朝着大病互助的方向奔跑,輕松籌短時間内成為行業第一,業内其他平台也相繼模仿,紛紛将自己從網絡衆籌平台調整為大病互助平台。
跟随者中就有水滴籌,但在當時,無論是流量還是規模,水滴籌都難以和輕松籌競争,一場源自線下推廣、争奪流量的戰争就此拉開帷幕。
水滴系逐步建立了水滴籌、水滴互助、水滴保、水滴公益四大模塊。其中,水滴籌和水滴公益負責大病救助,水滴互助為互助保險業務的開發,水滴保則是第三方保險代銷機構。水滴公益較為特殊,其拿到了民政部批準的慈善互聯網募捐信息平台牌照(共20家),目的是為慈善公募基金提供網絡募捐通道。
水滴系的商業模式是,通過水滴籌和水滴公益幫人籌款獲取流量,繼而經營流量,如向捐助者推銷商業保險,并向保險公司收取代銷費用。
這一循環的實現相當于多方共赢:患病家庭得到了資助,捐助者獻出了愛心又購買了商業保險,保險公司獲得客戶。
原本,輕松籌在早期采取的是向用戶收費模式,用戶募到資金後,輕松籌在提款中抽取2%左右作為手續費。“對籌款進行抽成,這在當時就是行規。”一家互助保險平台創始人肖楠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而水滴籌打破了這一行規。肖楠說,水滴籌從一開始就不收任何手續費,籌款所得資金全部給予籌款人。好處就是能夠快速吸引流量。
目前,幾乎所有大型網絡互助平台都不再收取手續費,除了提現時由微信平台抽取的0.6%提現費用。在水滴籌早期,平台甚至連這0.6%的提現費用都要幫患者墊付,完全是虧損經營。
水滴籌早期隻能依靠“燒錢”來獲得發展資金。工商資料顯示,截至目前,水滴旗下水滴互助已先後獲得3輪融資,總金額約17億元。騰訊、高榕資本、IDG等幾乎每一輪都做了領投。
“先要握住高流量,再和保險公司談判,能夠取得更高的傭金,經過兩三年的努力,我們已經在這個細分領域裡站穩腳跟了。”沈鵬在2019年3月的一次公開演講中說,水滴籌已與五十多家保險公司合作分銷平台,平均每月的保費傭金可以達到兩億多元。
憑借着這一塊收入,沈鵬稱,水滴公司整體已經實現盈虧平衡。
此外,若按照水滴籌的規則簡單計算,一次籌款大概持續30天,在這30天内,水滴籌可以将這筆資金委托第三方進行資金托管。水滴籌至今累計籌款超過235億元,平均每個月約為5.85億元的銀行流水,僅僅這部分的利息收入就相當驚人。
針對托管問題,水滴籌回複南方周末記者稱,水滴籌為保障平台所有籌款資金的運轉安全,已交予第三方銀行專管戶,與平台自有資金隔離。根據用戶協議約定,款項産生的利息全部用于因求助服務産生的相應費用,“事實上,因求助服務産生的第三方支付渠道手續費遠遠高于款項在平台上所産生的利息”。但水滴籌并未透露具體數據。
水滴籌們能夠在短短幾年時間狂飙突進,與法律尚無監管有關。
許多人以為水滴籌進行針對個人發起的大病互助屬于慈善,應該歸慈善法管,實際上慈善法并沒有覆蓋這一領域。
慈善法規定,對于慈善組織開展公開募捐活動(尤其是網絡公開募捐活動)必須通過民政部認定的網絡平台進行,受慈善法調整(監管)。但是諸如公益衆籌、大病互助基金以及個人求助行為等均無特别法律規定。
慈善法為什麼沒有覆蓋水滴籌這樣的公益衆籌?
複恩社會組織法律與研究中心理事長陸璇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慈善法下的慈善是指公益慈善,是一種公益活動,救助對象是不特定的社會公衆(如白血病患者群體、艾滋病患者群體),而不是私人救助,并非普通人理解下的“隻要是幫助特定他人,就是慈善行為”。
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則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慈善法之所以不監管,是因為立法時就意識到,任何深陷困境之人都有向他人和社會求助的權利,“這是天賦人權”。
涉及公益衆籌的法律,主要是民政部等相關部門2016年發布的《公開募捐平台服務管理辦法》,其第10條規定,個人為了解決自己或者家庭的困難,通過廣播、電視、報刊以及網絡服務提供者、電信運營商發布求助信息時,廣播、電視、報刊以及網絡服務提供者、電信運營商應當在顯著位置向公衆進行風險防範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屬于慈善公開募捐信息,“真實性由信息發布個人負責”。
換言之,如果求助者捏造虛假信息騙捐、詐捐,情節嚴重的,甚至可以以詐騙罪論處,适用刑法的相關規定,但發布信息平台并不負責。
對于水滴籌們來說,隻能靠自覺。2018年10月,愛心籌、輕松籌、水滴籌三家個人大病求助互聯網服務平台簽署自律公約,并向所有平台發出自律倡議。自律公約和倡議書提出,平台應加大資源投入,健全審核機制,配備與求助規模相适應的審核力量,實行機器智能和人工“雙審核”。
“自律公約裡面有一定的審核義務。是它自己對社會的一個承諾,但不具備強制性的法律效力。”陸璇說。
金錦萍認為,由于平台為個人發布的求助信息背書,所以不能簡單地承擔風險防範提示義務就可以免責。如上述朝陽區法院的判決中,水滴籌以原告身份向違反法律或者約定的籌款人提起訴訟并獲法院支持,這意味着法院也認定平台應承擔起向違反約定或者刻意欺詐的當事人提起訴訟責任,這本質上也是對平台義務的一種擴展。
金錦萍曾撰文指出,水滴籌早前對于自身定位模糊,這也模糊了慈善與企業的邊界。
沈鵬曾公開表示,水滴公司是一家社會企業。水滴公司聯合創始人徐憾憾還曾将水滴籌形容為一個Hybrid(混合型組織)。
但在金錦萍看來,隻有那些宗旨、過程和結果均以社會利益為目标的企業才能被稱作社會企業。
她認為,非營利組織的權責和普通商業企業完全不同。非營利組織可以獲得一定的免稅,沒有所有權人角色,不能進行利益分配等等。相應它也必須接受更為嚴格的信息披露要求,比私人企業更講求公開透明。
如果由營利組織來從事個人求助信息服務,則有許多弊端。例如信息不對稱,捐助者很難判斷個人救助平台是否值得信賴,追究平台的違約責任也就無從談起。如果平台是以營利為目的,也很難說服他人進行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捐款。倘若隐瞞商業模式和利益歸屬的具體情況,一旦公衆獲悉真相,勢必受到反噬。
金錦萍建議,個人求助平台應該成為商業組織中一個獨立的闆塊,但是與其他闆塊的業務往來需要有明确的規定;将此業務獨立出來,由一個非營利組織來運行。而且要求無論采取哪種方式,向公衆披露必要的信息是基礎性義務。
但就水滴籌來看,公司不僅沒有向公衆公布其具體财報,對于水滴籌一旦盈利後如何安排利潤的問題,水滴籌也沒有直接答複南方周末記者,而是表示“将繼續聚焦互聯網健康保險保障領域”。
水滴籌在2019年12月9日公開的官方回應中宣布,當周重啟線下服務。
(應受訪者要求,楊琳、肖楠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徐庭芳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