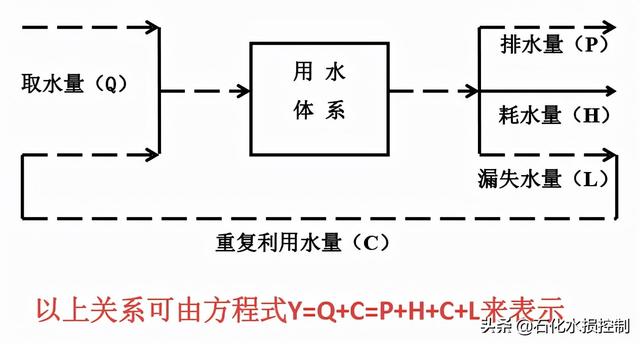2019年9月3日,王曉曉入職方晖公司,雙方簽訂勞動合同,約定月工資4.3萬元,合同期限為2019年9月3日至2022年9月30日,其中試用期6個月。
2020年2月18日,公司人事通知王曉曉,其試用期未通過,不能轉正,最後工作日為2月21日。
2020年2月21日中午,王曉曉通過電子郵件、手機短信方式,向部門副總裁和人事提出,為了便于下一次求職,雙赢起見,請求将離職時間延後到試用期之後,并提議最後工作日定到3月底,預先感謝公司的寬厚。
公司遂于當日先後通過微信及電子郵件方式向王曉曉提供《協商解除協議》,内載雙方于2020年3月15日解除勞動關系、薪資結算至2020年3月31日。王曉曉在微信中回複已閱沒問題。由于正值疫情期間,公司還未複工,人事要求王曉曉簽署協議後,掃描或拍照并發回。王曉曉以其需要找地方打印掃描等為由拖延。後在人事催促下,王曉曉于當晚十點多将協議送至公司保安室,并發短信告知人事。
2020年2月25日,王曉曉的上級向王曉曉發送郵件,請其在3月15日前交接公司物品。
2020年3月13日,王曉曉向人事發送短信,告知其沒有在《協商解除協議》上簽字,之前郵件中沒有一口咬定非本人簽字,是“留了餘地,有利于你們内部調查、分配責任時,HR有機會免責,這也是最後的善意吧”。王曉曉并提出,她在工作期間無任何失職,不同意與公司解約。公司則認為雙方已協商一緻,于3月16日向王曉曉出具了雙方已于3月15日解除勞動合同的離職證明。
2020年4月7日,王曉曉以公司違法解除為由申請勞動仲裁,要求公司恢複與其的勞動關系,并按月工資4.3萬元的标準支付3月16日至仲裁裁決之日為止的工資。仲裁裁決未支持王曉曉的請求,王曉曉不服,起訴至法院。

一審中,王曉曉提供了一份沒有簽名但有她手寫批注的解約協議,她稱這份才是她2020年2月21日晚向公司遞交的協議,公司的那份有她簽名的協議是假的,簽名是公司僞造的。
方晖公司否認王曉曉的說法,稱王曉曉在仲裁時未遞交過該份協議,也從未在訴訟前提出過協議上有諸多批注。
一審法院認為,因方晖公司對王曉曉提供的協議真實性有異議,且王曉曉無相關證據佐證該份協議就是她2020年2月21日晚向方晖公司所遞交的,故對該證據的證明目的不予确認。
同時,從雙方2020年2月21日期間往來的電子郵件、企業微信、手機短信,已經完整反應出雙方協商解除勞動合同的過程,上述勞動合同解除和薪資結算的時間均由王曉曉先提出,說明雙方已經形成合意。
王曉曉事後提出的相關說辭與證據,均不足以證明其在2020年2月21日對于雙方間的協商解除協議有不同意或明确拒絕的行為,故判決駁回王曉曉全部訴請。
王曉曉不服判決,上訴至上海一中院。
二審中,王曉曉提供了公司發送給員工的電子郵件以及部分工作手稿等證據,以此證明其未與公司解約,還在繼續工作。
經查,王曉曉提供的電子郵件内容并未體現2020年2月21日後方晖公司向她單獨布置、設定工作任務的安排,與本案處理結果也無直接關聯,故在本案中對此不作認定;工作手稿是王曉曉單方制作,亦未得到方晖公司認可,故對此不予确認。
上海一中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的争議焦點為方晖公司以與王曉曉達成一緻為由解除勞動合同,是否構成違法解除,以及可否成為王曉曉恢複勞動關系主張成立的充足依據。
首先,王曉曉在方晖公司通知其離職後,于該日向方晖公司提出希望将最後工作日定在2020年3月底,并表示預先感謝方晖公司的寬厚。
方晖公司為此而拟定了《協商解除協議》,并先後通過企業微信、電子郵件方式發送給王曉曉,同意将薪資結算至王曉曉先前所提出的最後工作日,僅是将解除勞動合同時間提前至2020年3月15日。
王曉曉在收到方晖公司人事通過企業微信方式發送的注明“協商解除協議”名稱的文件後明确表示“已閱沒問題”,此應可視為雙方已口頭就協商解除勞動合同的時間達成一緻。
其次,王曉曉該日将《協商解除協議》打印後,送至方晖公司門衛處,随後發送短信告知方晖公司人事,卻未提及其對《協商解除協議》有異議,甚而直至試用期滿也未見王曉曉告知方晖公司其對《協商解除協議》持有異議等事實,也可印證方晖公司有關雙方于2020年2月21日已就協商解除勞動合同達成合意之主張。
第三,從在案證據所反映的王曉曉在其與方晖公司協商解除勞動合同過程中之行為表現看,實難認定王曉曉系誠信善意磋商。如若雙方之間的協商解除勞動合同協議未能達成,王曉曉對此也存在締約過失,應就方晖公司由此所産生之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綜上,上海一中院遂認定方晖公司行為不構成違法解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以上人名、公司名均為化名)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