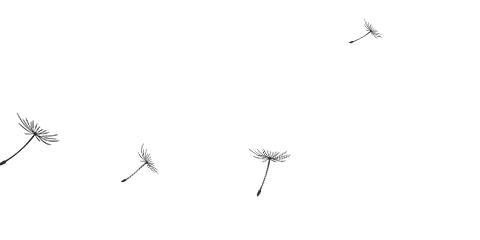公司減資中的形式與實質問題的再讨論
2022年9月29日,江蘇省高院在其官方微信公号中發布了《2020-2021年江蘇法院公司審判典型案例》,其中第二則案例“貨運公司訴陳某、徐某、楊某公司減資糾紛案”引起了不少業内前輩的批判,認為該案明顯違反《公司法》“股東有限責任”這一基本原則,應屬典型的“司法拉偏架”。但筆者認為南京中院的改判并未突破股東有限責任原則,相反在兼顧股東有限責任的基礎之上也平衡了公司、股東、債權人之間的利益,完善了“形式減資”在實踐中的一些問題。
【案情摘要】(來源:聚法案例)南京市江甯區人民法院作為一審法院已查明的事實如下(案号:(2019)蘇0115民初6846号):
2015年7月14日,司利德公司經公司登記機關登記設立,性質為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100萬元,股東為徐廣榮(出資額40萬元,出資期限2030年6月26日)、陳亞光(出資額30萬元,出資期限2030年6月26日)、楊某某(出資額30萬元,出資期限2030年6月26日);
2017年10月18日、徐廣榮、陳亞光分别向司利德公司銀行賬戶彙款40萬元、30萬元,備注為注冊資本金。2017年10月26日,楊某某向司利德公司銀行賬戶彙款30萬元,備注為投資款;
2018年6月26日,南京市浦口區人民法院作出(2018)蘇0111民初1278号民事判決,判決司利德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嘉翔公司支付代理費418274.5元及違約金(自2017年4月13日起按年利率24%計算至實際給付之曰止);
2018年9月14日,司利德公司做出股東會決議:同意将公司注冊資本從100萬元減至70萬元。本次減資後公司各股東出資及出資比例如下:股東陳亞光減少出資30萬元;股東徐廣榮持股40萬元,占注冊資本57%,股東楊某某持股30萬元,占注冊資本43%;
2018年9月15日,司利德公司在金陵晚報刊登公告,載明:根據2018年9月14日的拟将注冊資本從100萬元減至70萬元,現予以公告,債權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償債務或提供擔保;
2018年11月10日,司利德公司出具公司債務清償或提供擔保的說明:根據《公司法》有關規定,本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經股東(大)會決議,将公司注冊資本從100萬元減至70萬元。于2018年9月15日在金陵晚報上發布了減資公告。至2018年11月10日,公司職務清償和提供擔保情況如下:至2018年11月10日,公司已對債務予以清償或提供了相應的擔保;
2019年1月31日,南京市浦口區人民法院作出(2018)蘇0111執3529号執行裁定書,以未發現其他可供執行的财産,申請執行人也未能提供其他财産線索為由裁定終結該案的本次執行程序;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作為二審法院在本院查明部分載明如下(案号:(2020)蘇01民終11565号):
本院二審期間,雙方當事人均未提交新證據,且對一審查明的事實無異議。本院對一審查明的案件事實予以确認。本院經審理查明,各方當事人對嘉翔公司為司利德公司的已知債權人并且未直接通知均無異議。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作為再審法院在本院認為部分載明如下((2021)蘇民申5976号):
但本案而言,司利德公司在減資時不僅通知程序存在嚴重瑕疵,而且未依法編制财産清單及負債表,由于司利德公司的會計賬簿已經遺失,僅憑陳亞光提交的銀行流水,不能當然得出陳亞光未從公司取回财産的結論。且即便陳亞光未從司利德公司取回出資,陳亞光的股權也轉為了債權。另外,股東會決議系由三股東共同作出,二審法院判令徐廣榮、楊某某對減資股東陳亞光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并無不當。
另外摘抄《2020-2021年江蘇法院公司審判典型案例》中的【典型意義】部分如下:【典型意義】公司資本構成公司對外交往的信用基礎,與公司交易的相對方往往通過公司注冊資本額判斷公司資信狀況。公司減資會減少公司責任财産,減輕股東責任,影響公司償債能力,故公司法明确要求公司減資應自作出減少注冊資本決議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債權人,并于三十日内在報紙上公告。本案中,公司減資未通知已知債權人,存在程序瑕疵,即使股東未實際抽回資本,但其股權已轉為對公司的債權,等同于股東可以與債權人在同一順位獲得清償,變相減少了公司的責任财産。在實踐中,公司減資必須嚴格依照法定條件和程序實施,避免打擦邊球,否則不僅實際影響公司債權人利益,也容易給減資股東埋下後患。
【筆者觀點】一、形式減資與實質減資的關鍵在于有無利用減資抽回資金。
提到“形式減資”不得不提及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144号案件,該案件中最高院的二巡法官會議中将公司減資進一步區分為實質減資與形式減資兩種,同時就減資程序違法的情形下,形式上減資是否構成抽逃出資的出現兩種觀點:
否定說:股東抽逃出資導緻公司責任财産減少,本質上是股東侵犯公司财産權的行為,故應在抽逃出資本息範圍内對公司債務不能清償的部分承擔補充賠償責任。盡管操縱公司違反法定程序減資是股東抽逃出資的一種方式,但如果在公司減資過程中股東并未從公司中抽回出資、未導緻公司責任财産的減少,此種減資僅為形式上的減資。形式減資情形下,股東沒有利用公司的減資程序侵犯公司的财産權,沒有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因此不能僅以公司減資程序不合法而認定股東應承擔抽逃出資的責任。
肯定說:公司減少注冊資本應遵守嚴格的法律程序,包括通知債權人并按照債權人要求提供擔保或者清償債務。公司注冊資本減少, 意味着公司責任财産減少、償還債務能力降低,對公司債權人的債權實現具有不利影響。當公司未按法律規定進行減資且導緻在減資之前形成的債務不能得到清償時,公司股東應承擔抽逃出資的責任。
最終,法官會議意見采納了否定說,其認為:“公司在減資過程中存在程序違法情形,與股東利用公司減資而抽逃出資是兩個不同的問題,違法減資的責任主體是公司,抽逃出資的責任主體是股東,故不能僅因公司減資程序違法就認定股東抽逃出資。本案重點衡量股東在公司違法減資過程中是否存在抽逃出資行為。股東抽逃出資行為本質上是股東侵犯公司财産權的行為,導緻公司責任财産減少。如果公司減資過程中股東并未實際抽回資金,則屬于形式上的減資,即公司登記的注冊資本雖然減少, 但公司責任财産并未發生變化。這種情形下,雖然公司減資存在違法行為,應由相關管理機關對其實施一定的處罰, 但股東并未利用公司減資程序實際抽回出資、侵犯公司财産權,亦未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因此不能因公司減資程序不合法就認定股東構成抽逃出資。
筆者認為:
1、形式減資與實質減資的讨論基礎系建立在減資程序違法的前提下,意在解決減資程序違法,因為形式減資實質并未減損公司的償付能力,對債權人的利益不存在損害情形,故而不應混淆減資責任與抽逃出資責任主體。最高院的觀點其實是對現行《公司法解釋三》第十二條中“其他未經法定程序将出資抽回的行為”的拆解,即如若發生減資程序違法且确有股東減資過程中抽回出資的的那麼應屬“未經法定程序抽回出資”也就是實質減資,而如果雖然發生減資程序違法但是并不存在股東抽回出資的情況時,那麼自然很難符合第十二條中的“未經法定程序将出資抽回”的條件,也就不應再行利用該條認定股東利用減資抽逃資金。所以可見如若公司減資不存在程序違反法律規定的情況時,債權人利益也就必然未受損,此時形式減資與實質減資沒有區分的必要。
2、形式減資與實質減資的區分關鍵即“公司減資過程中股東有無實際抽回資金”,此處的“資金”還應進一步區分為“認繳資金”與“實繳資金”兩類,而根據《公司法解釋三》第十二條中的“未經法定程序抽回資金”中的“抽回”、“資金”的表述可見此處的“資金”明顯應指代“實繳資金”,否則不存在“抽回”的行為表述。但需要注意的是如若股東通過減資程序減少的是“認繳資金”時,那麼該行為性質是“實質減資”還是“形式減資”?還能不能認定抽逃出資?雖然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再144号法官會議中并未明确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沿用最高院法官會議中的“股東抽逃出資行為本質上是股東侵犯公司财産權的行為,導緻公司責任财産減少。”的觀點來看,即便減資減少的是“認繳資金”但是該認繳的義務主體為股東且受益主體為公司時,一旦出現減資程序違法情形的,那麼公司對股東的應收出資額預期也就遭到破壞,公司顯然也是違法減資的受損主體,該行為破壞了資本确定的基本原則。
但此處還能不能适用《公司法解釋三》第十二條的規定,認為股東違法減資減少“認繳資金”的應屬“抽逃出資”?
筆者認為應當區分具體如下兩種情況分析:
第一種:在股東認繳出資符合“加速到期”情形下,公司股東會違法減資減少股東“認繳資金”的可以視為“抽逃出資”。股東雖享有認繳期限利益,但在公司已經無法償付到期債務且公司作為被執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窮盡執行措施無财産可供執行,已具備破産原因,但不申請破産時,參照《九民會議紀要》的意見來看股東認繳期限加速到期即股東享有的認繳期限利益“加速到期”變成“現時義務”,此時減資程序違法下對“認繳資金”予以減免的本質已經是對“應付出資”的見面,自然會對公司償付能力産生減損,直接導緻債權人利益受損,所以符合《公司法解釋三》第十二條中的“未經法定程序抽回出資”的要件。
第二種:股東認繳出資不符合“加速到期”情形下,公司股東會即便違法減資減少股東“認繳資金”的也難以适用《公司法解釋三》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的規定以抽逃出資要求股東在未出資本息範圍内對公司債務不能清償的部分承擔補充賠償責任。因為認繳期限未到的情況下或者在未能成給“現時義務”時,就難以存在“抽回”的事實,自然無法依據《公司法解釋三》第十二條的規定,認定為抽逃出資。不過回過頭來說,公司都不存在到期債務無法履行的情形且未出現執行不能情形時,那麼也就自然不會出現損害債權人利益的可能。
二、本案沒有證據證明陳亞光減資符合“形式減資”,南京中院及省高院觀點與最高院并不沖突。
結合上述,南京中院或者江蘇省高院的觀點與最高院上述觀點是否沖突的關鍵即本案中“陳亞光有無從本次減資過程中實際抽回資金”,如果沒有抽回資金那麼就屬于形式減資,反之則應屬實質減資,應當認定為利用減資程序抽逃出資侵害公司的财産權。
結合筆者檢索到的查明事實部分可知:
1、陳亞光在公司設立時認繳30萬且享有認繳期限利益至2030年6月26日,但是其于2017年10月18日将30萬元出資款支付至司利德賬戶的行為表明了其本人放棄了認繳期限的利益;
2、司利德公司明知欠付貨運公司款項下卻單方面作出減資決議且并未通知已知債權人;
3、司利德出具的公司債務清償或提供擔保的說明至2018年11月10日,公司已對債務予以清償或提供了相應的擔保,但實際其并未按照規定通知已知債權人且實際并未履行任何清償或提供的擔保義務;
4、陳亞光僅出具個人銀行流水意圖證明并未未從公司取回财産,但因為司利德減資過程中并未依法編制财産清單及負債表,同時司利德公司的會計賬簿已經遺失,無法查明司利德公司真實的财務狀況。
所以:
1、本案中陳亞光在實際已經提前出資的情況下,其已經不享有相應的期限利益,而其本人在已經“實繳”的情況下,公司減資程序違法時,其本人提交的銀行流水僅能證明該特定銀行賬戶沒有發生從公司取回财産的事實,但是否存在其他銀行賬戶從司利德公司取回财産的行為明顯因為缺乏财産清單及負債表以及會計賬簿遺失,導緻該部分事實已經無法查明。而從舉證距離、舉證能力上來說,陳亞光及其他股東舉證證明自己沒有從公司取回财産的能力和距離都強于債權人,但在陳亞光等人無法說明公司财務狀況以及資産清單的情況下,應當由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後果,而不能将該部分舉證責任交由債權人,明顯不太現實。
2、本案中如果司利德公司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通知貨運公司其減資時,那麼按照規定貨運公司可以要求司利德公司立即清償債務或提供擔保即貨運公司的債權具有即時履行的可能,而司利德公司提交的虛假的債務償付直接導緻司利德公司的即時償付的機會喪失。
3、基于陳亞光有無從公司取回财産的事實無法查明且舉證責任應由陳亞光承擔的情況下,筆者認為難以陳亞光符合“形式減資”的條件。從心證角度出發,如果陳亞光減資且沒有從司利德取回财産,司利德為何大費周章隐瞞公司債務清償情況?為何不通知已知債權人?為何恰恰在公司減資以後公司的會計賬簿遺失?減資時不變質财産清單以及資産負債表?所以筆者認為陳亞光等人的陳述難以令人信服其未能取回财産。畢竟無論是裁判者甚至是代理律師,都不是客觀事實的參與者,我們僅可以依據現有的證據去還原零碎的事實并依據各方的陳述和補正拼湊出完整的“真相”,就本案而言無論是動機、行為都難以去認可陳亞光等人描述的“真相”是真。
4、正如高院所言,如果陳亞光真未從司利德公司中取回财産,但是在減資整體決議不因瑕疵而無效的情況下,陳亞光也享有了對司利德公司的債權,而該債權的清償必然導緻司利德公司償付能力的減損,所以依然屬于損害債權人利益的範疇。
綜上,南京中院和江蘇省高院的觀點與最高院(2019)最高法民再144号案件觀點并不沖突,相反筆者認為南京中院和江蘇省高院的觀點是對最高院“形式減資”的完善,諸如形式減資中“未抽回資金”舉證責任應由減資受益主體舉證、“認繳期限利益”因提前說實繳而不再享有。
三、本案未突破“股東有限責任”,相反是對“股東有限責任”的貫徹。
股東有限責任是個老話題,基本理論不多贅述,但根據現行規定來看“有限責任”的含義是指公司以以其全部财産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回到本案中南京中院判令陳亞光在減資30萬元的範圍内對司利德債務承擔補充賠償責任,徐廣榮、楊某某對陳亞光的上述第二項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是否是對“股東有限責任”的突破?
筆者認為本案是對股東有限責任原則的貫徹,而非突破。
1、有限責任的前提建立在股東能夠在法律規定的框架内自治,而本案中陳亞光等三人作為股東明知司利德對外負有債務且明知債權人的情況下,未能遵守減資程序的規定,本身是對公司自治邊界的破壞。對于陳亞光來說,其在不能提交司利德公司财産清單以及負債表、會計賬簿的情況下無法令人信服其故意不通知已知債權人并作出虛假償付擔保說明情況下的“形式減資”可能,所以按照《公司法解釋三》第十四條的規定,債權人請求抽逃出資的股東在抽逃出資本息範圍内對公司債務不能清償的部分承擔補充賠償責任,而中院判令其在減資30萬範圍内對債務承擔補充賠償責任本身系根據其減資受益部分即“實繳資金”範圍内的“補充賠償”,并沒有突破30萬的“有限責任”的範圍,要求陳亞光對司利德所有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而且第十四條也明确規定抽逃出資的股東已經承擔上述責任,其他債權人提出相同請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是對“股東有限責任”的再次明确,何來“突破”?
2、另外參考上海一中院發布的《注冊資本認繳制下公司瑕疵減資的股東責任問題 | 實務紀要》文章的觀點認為,即便減資程序存在瑕疵,也不應從整體上輕易否定公司減資的效力,但未被合法有效通知到的債權人可以主張減資行為對其個體不發生法律效力。所以從這個角度推導本案來看,陳亞光減資的行為因為存在瑕疵僅對特定債權人不發生效力,同時陳亞光因為已經于2017年10月18日實繳出資款30萬,故而好像可以得出即便本次減資對債權人不發生效力,也因為陳亞光實際實繳出資而滿足“以認繳出資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的條件,要求其在減資30萬範圍内承擔補充賠償責任的結果不公,這也是部分對該案例持批評意見的角度。
但是本案中不能忽略的事實是,司利德不僅未通知已知債權人,而且做出的償付和擔保說明中明确承諾已經償付或提供了擔保,同時該公司的财務狀況已無法核查有無實際讓陳亞光取回财産的狀況下,以陳亞光實繳出資且公司減資效力整體應為有效的情況下,那麼由此直接導緻的後果就是債權人喪失了要求司利德公司立即償付或提供擔保的機會,但陳亞光以及司利德公司卻并不因此承擔任何違法減資的責任,是否公允?
3、其他股東協助陳亞光抽逃出資的實際上參考侵權的構成要件,要求協助抽逃出資的其他股對此承擔連帶責任的也同樣是在“30萬範圍内”,即便其他股東已經實繳出資的情況下,該部分的“30萬”也并非基于其他股東未履行“出資義務”或“抽逃出資”所負擔,而是“協助抽逃出資”所負擔的義務,與股東有限責任中的“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本質是兩個概念。
說了這麼多,每個人的論調都有自己的案例支持,也都有自己解讀法條角度的支持,但就本案而言,筆者認為高院将該案例上升為“典型案例”推廣,是對公司形式減資與實質減資的細化明确,同時就形式減資下的舉證責任以及股東減資中的相關義務的再次明确,礙于能力有限,書寫難免出現錯誤,還請批評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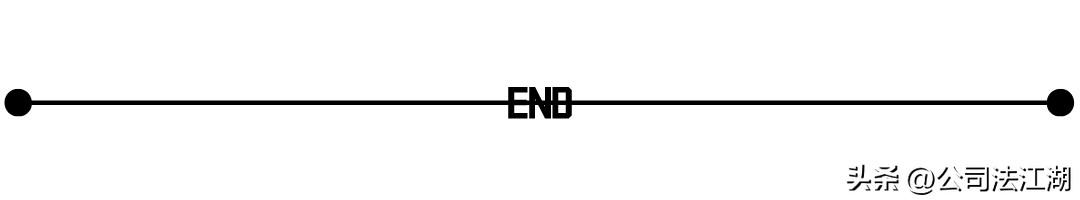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