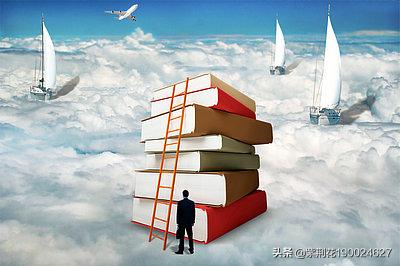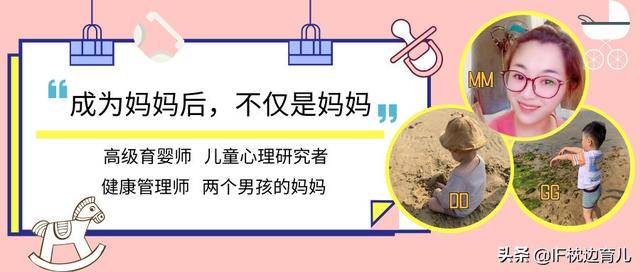随着我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逐漸好轉,各行各業的複工複産也正在有序推進。複工複産後該推行哪些健康的生活方式,讓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更安全、更文明、更美好,成為了人們極為關心的話題。最近,“分餐制”再次成為熱點話題,引發了社會各界人士的熱烈讨論:“古代人分餐嗎?”“在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曾廣泛實行過‘分餐制’嗎?”
帶着這些大衆關心的問題,新華網文化頻道近期特别專訪了相關領域的文化專家,請他們梳理中華傳統文化發展的曆史脈絡,解讀各個朝代的餐飲習慣,講講中國人的飲食文化如何從“分餐制”過渡到“會食制”、最後又為何演變成今日的“合餐制”,并從共同呼籲疫情過後“分餐不分愛”的倡議出發,談談全民實施“分餐制”的必要性。

追溯·古代人怎樣施行分餐制
“現代中國人聚會,不論是在家中或是在餐館,如果是享用中餐,一般都是采用圍桌會食的方式,隆重熱烈的氣氛會深深感染每一個與宴者。這種親密接觸的會食方式,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一個重要傳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開門見山地說,“但,其實這種在一個盤子裡共餐的‘會食方式’,曆史追溯起來也不過一千多年。比這更古老、更優良的傳統是地道的‘分餐方式’。”
讓我們跟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家具燙蠟技藝非遺傳承人于鴻雁,一起來追溯古代中國曾實行了至少三千年的分餐制的曆史脈絡與演變。

古代中國人分餐進食,一般都是席地而坐,面前擺着一張低矮的小食案,案上放着輕巧的食具,重而大的器具直接放在席子外的地上。“在商朝,人類發明了夯土技術,由于夯土技術可以把地面修理平整,于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室内家具開始出現了,那就是‘席’。”家具燙蠟技藝非遺傳承人于鴻雁指出,“那時候我們席地而坐,在席地上吃飯就叫宴席,最尊貴的位置叫主席,吃完飯叫退席。那時候吃飯跪在席上各吃各的,這就是分餐制。”後世所說的“筵席”中的筵和席,其實都是席子,正是這古老分餐制的一個寫照。
《後漢書·逸民傳》記隐士梁鴻受業于太學,還鄉娶妻孟光,夫妻二人後來轉徙吳郡(今蘇州),為人幫工。梁鴻每當打工回來,孟光為他準備好食物,并将食案舉至額前,捧到丈夫面前,以示敬重。孟光的“舉案齊眉”,成了夫妻相敬如賓的千古佳傳。
據于鴻雁介紹,故事裡面說的“案”,在漢朝是一個類似托盤的器具,就是從青銅器“俎”演變而來的盛放食物的木闆。由此可見,在漢時,人們還是施行分餐制,夫妻之間也是各吃各的。又據《漢書·外戚傳》說:“許後朝皇太後,親奉案上食。”因為食案不大不重,一般隻限一人使用,所以婦人也能輕而易舉。
王仁湘指出,在漢墓壁畫、畫像石和畫像磚上,經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飲場面,看不到許多人圍坐在一起狼吞虎咽的場景。低矮的食案是适應席地而坐的習慣而設計的,從戰國到漢代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實物,以木料制成的為多,常常飾有漂亮的漆繪圖案。漢代承送食物還使用一種案盤,或圓或方,有實物出土,也有畫像石描繪出的圖像。承托食物的盤如果加上三足或四足,便是案,正如顔師古《急就章》注所說:“無足曰盤,有足曰案,所以陳舉食也。”
王仁湘進一步介紹說,以小食案進食的方式,至遲在龍山文化時期便已發明。考古已經發掘到公元前2500年時的木案實物,雖然木質已經腐朽,但形迹還相當清晰。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發現了一些用于飲食的木案,木案平面多為長方形或圓角長方形,長約1米,寬約30厘米上下。案下三面有木條做成的支架,高僅15厘米左右。木案通塗紅彩,有的還用白色繪出邊框圖案。木案出土時都放置在死者棺前,案上還放有酒具多種,有杯、觚和用于溫酒的斝。稍小一些的墓,棺前放的不是木案,而是一塊長50厘米的厚木闆,闆上照例也擺上酒器。陶寺還發現了與木案形狀相近的木俎,略小于木案,俎上放有石刀、豬排或豬蹄、豬肘,這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一套廚房用具實物,可以想象當時長于烹調的主婦們,操作時一定也坐在地上,木俎最高不過25厘米。漢代廚人仍是以這個方式作業,出土的許多庖廚陶俑全是蹲坐地上,面前擺着低矮的俎案,俎上堆滿了生鮮食料。
王仁湘表示,陶寺遺址的發現十分重要,它不僅将食案的曆史提到了4500年以前,而且也指示了分餐制在古代中國出現的源頭,古代分餐制的發展與這種小食案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小食案是禮制化的分餐制的産物。在原始氏族公社制社會裡,人類遵循一條共同的原則:對财物共同占有,平均分配。在一些開化較晚的原始部族中,可以看到這樣的事實:氏族内食物是公有的,食物烹調好了以後,按人數平分,沒有飯桌,各人拿到飯食後都是站着或坐着吃。這是最原始的分餐制,與後來等級制森嚴的文明社會的分餐制雖有本質的區别,但在淵源上考察,恐怕也很難将它們說成是毫不相關的兩碼事。随着飲食禮儀的逐漸形成,正式的進餐場合不僅有了非常考究的餐具,而且有了擺放餐具的食案,于是一人一案的分餐形式出現了。
這樣看,分餐制的曆史無疑可上溯到史前時代,它經過了不少于三千年的發展過程。
據王仁湘研究,會食制的誕生則大體是在唐代,發展到具有現代意義的會食制,經曆了一個逐漸轉變的過程。
“周秦漢晉時代,筵宴上之所以實行分餐制,應用小食案進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王仁湘認為,雖不能絕對地說是一個小小的食案阻礙了飲食方式的改變,但如果食案沒有改變,飲食方式也不可能會有大的改變。
“其實,古代的分餐制轉變為會食制,并不是一下子就轉變成了現代的這個樣子,還有一段過渡時期。這過渡時期的飲食方式,又有一些鮮明的時代特點。在會食成為潮流之後,分餐方式并未完全革除,在某些場合還要偶爾出現。”以南唐畫家顧闳中的傳世名作《韓熙載夜宴圖》為例,王仁湘找出了有關的信息,“《韓熙載夜宴圖》為一長卷,夜宴部分繪韓熙載及其他幾個貴族子弟,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上,欣賞着一位琵琶女的演奏。他們面前擺着幾張小桌子,在每人面前都放有完全相同的一份食物,是用八個盤盞盛着的果品和佳肴。碗邊還放着包括餐匙和筷子在内的一套進食具,互不混雜。這裡表現的不是圍繞大桌面的會食場景,還是古老的分餐制,似乎是貴族們懷古心緒的一種顯露。其實這也說明了分餐制的傳統制約力還是很強的,在會食出現後它還有一定的影響力。”
在晚唐五代之際,表面上場面熱烈的會食方式已成潮流,但那隻是一種有會食氣氛的分餐制。“人們雖然圍坐在一起了,但食物還是一人一份,還沒有出現後來那樣的津液交流的事實。這種以會食為名、分餐為實的飲食方式,是古代分餐制向會食制轉變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發展階段。”王仁湘說,“到宋代以後,真正的會食,即具有現代意義的會食才出現在餐廳裡和飯館裡。”
從魏晉南北朝出現同桌而食,到隋唐出現了過渡餐制——會食制,直到宋代至明清合餐制從出現到完全成熟,延續至今。這樣,中國人的飲食文化從“分餐制”過渡到“會食制”,最後演變成今日的“合餐制”。
“當下,當我們現在倡導分餐制時,會遇到傳統觀念的挑戰,也會遇到一些具體的問題。會食制在客觀上是促進了中國烹調術的進步的,比如一道菜完完整整上桌,色香味形俱佳,如果分得零七八碎,不大容易讓人接受。其實,這也沒什麼要緊的,丢掉一些傳統的東西,意味着有更多的機會創造新的東西。”王仁湘認為,分餐制是曆史的産物,會食制也是曆史的産物,那種實質為分餐的會食制也是曆史的産物。我們今天正在追求的新的進食方式,看來隻須按照唐代的模式,排練出—套仿唐式的進食方式就可以了,不必非要從西方去引進。這種分餐制借了會食制固有的條件,既有熱烈的氣氛,又講究飲食衛生,而且弘揚了優秀的飲食文化傳統。
探索·現代社會如何實現分餐制

“當下的疫情帶給了我們深深的思考。這種思考涉及到一個很深刻的問題,我們的飲食制度如何改革?關于此次疫情,在全方位、多層次、立體的思考過程當中,一定要對我們的生活習慣,包括我們的餐飲方式,進行一次深刻的反思。如果暫時做不到,起碼要增進全面深層的讨論,從而形成一種合力來推動分餐制的實施。”複旦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孟建接受新華網文化頻道記者采訪時說。
“我們現在講的合餐制,實際上是圍餐制。圍餐制源于生活習慣,也有人把它上升到傳統文化的角度。其實,在北宋之前人們都是分餐制的,隻是到了宋代以後,人們才開始用合餐制。主要是生産力的發達帶來了生活的富庶,加上餐飲習慣的改變,慢慢就開始形成了合餐。”孟建認為,“合餐制既然已經進入到文化層面,要改變它,就不是太容易,需要在更深的問題上去進行思考。但,并不是不可以改變的。”
“大疫之後,我們的确要對分餐制這個問題進行很多的思考,在一些讨論之後,達到一定的共識,形成一次對科學生活方式的大倡導。新的科學生活方式當中,包括新的科學的飲食方式,分餐制可以作為其中的一個大類别定下來。”孟建建議道。
對此,他進一步提出,要采取不同的細化方案,以令分餐制在更大範圍有可行性,并具體推薦了三種方式:
第一種,圍桌分餐制。由于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大家不坐在一起,情感的交流、家族的交流都受影響。因此,我們還是可以圍着圓桌坐下去,但是坐下後采取分餐。實際上,我們現在接待重要的外賓,大部分都是采取這種分餐制。
第二種,非純粹的分餐制——公筷制。公筷制雖然沒有這麼純粹,但是中國的烹饪審美得以保留的程度比較高。為防止桌子上放兩雙筷子容易搞混,公筷可以設計要特别一點,容易辨認。
第三種,自助餐式分餐制。這個可作為一種特殊場合的方式,選擇的餘地也比較大。可以根據不同的客人、不同的活動要求等,采取不同的方式。
孟建相信,分餐制作為科學的飲食方式,在大家讨論的基礎上,通過方方面面的協調和努力,可以得到良好的踐行。

結語
經由疫情的洗禮,國人的衛生習慣、生活方式,産生了一系列新的變化。面對新的時代要求,人們必将面臨觀念上的不斷更新,更健康科學的新生活方式也将逐漸成為共識。分餐制便是在此背景下,得以被廣泛關注和提倡。我們将從傳統文化中吸取精華,以适應新的時代規範,“分餐不分愛”把良好的分餐習慣貫穿到人們的日常生活裡。
來源:新華網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