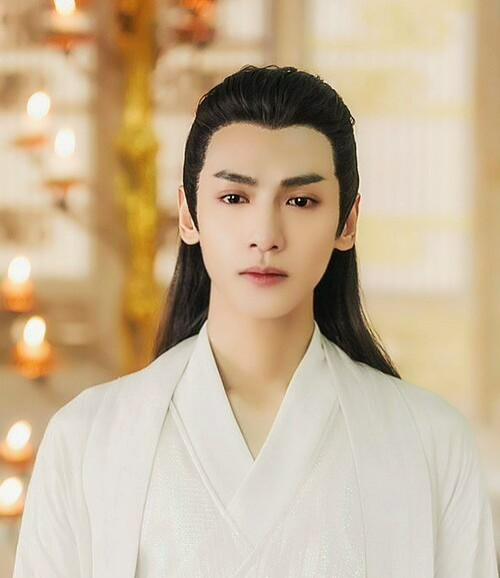在古代印度,種姓制和奴隸制是有區别的。奴隸制講的是階級關系,即奴隸和奴隸主這兩大階級之間的關系;而種姓制講的是等級關系,即婆羅門、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羅這四個種姓之間的等級關系。但這兩者又不能截然分開。在四個種姓中間有奴隸與奴隸主之分。反之,在奴隸與奴隸主中間也有四個種姓之别。一般來說,作為奴隸主的主要是由婆羅門、刹帝利和大商人吹舍中間的一些人組成;而奴隸,主要是由首陀羅和貧困吠含中間的一些人組成,特别是首陀羅,在這個種姓中間有相當數量的人是奴隸。但這不是說隻有低級種姓才成為奴隸,而高級種姓不會淪為奴隸。因此,種姓制和奴隸制這兩者既有區别,又有聯系。

在這一時期所出現的諸法經與法典以大量的條文記述了這種關系。法典為了鞏固高級種姓的特權地位,強調職業的世襲性,特别是嚴禁低種姓從事高級種姓的職業。例如《摩奴法典》規定:“低級出生者因貪欲而以高級種姓的職業為生,則國王剝奪其财産後,應立即放逐之”。
這就保證了高級種姓的特權。法典為了證明這種關系的合理性,說這是梵天大神對用他自己的口、手、腿,腳創造來的人所規定的義務。高級種姓為了保證其世襲化的特權地位不緻因通婚而混亂,法典強調各種姓間的通婚須以内婚制為原剛,歧視異姓通婚,特别是嚴禁低級種姓之男與高級種姓之女通婚,這叫做逆婚。
《摩奴法典》規定:向高級種姓之女求婚的低級種姓之男,應處以體刑。在這種原則下,首陀羅隻能從首陀羅種姓中娶妻了。在《佛本生經》中留下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理發師的兒子愛上了離車族的一個少女。他的父親勸告他說:“我的兒子,你不要把願望執著在一件辦不到的事情上。你是理發師的兒子,屬低級種姓(首陀羅),而離車族的少女屬高級種姓(刹帝利),刹帝利的女兒是不會和你成親的。”結果理發師的兒子在絕望中憂郁而死。

這樣,四種姓的不同地位便被進一步固定下來。
二、高級種姓為了維護他們的特權利益,對四種姓間的關系,在各個方面都規定了嚴格的區分和界限就宗教生活來說,在四種姓間有嚴格的區分,而且規定得非常繁瑣。特别是首陀羅,對這個種姓來說,根本無權參加雅利安人(前三種姓)的宗教生活,即使聽一聽或看一看雅利安人的聖書吠陀也是不能容許的。例如《高達摩法典》規定:假如首陀羅故意聽人誦讀吠陀,須向他的耳中灌以熔化的錫或蠟;假若他誦讀吠陀,須割去他的舌頭。
各種姓間的不平等關系特别明顯地表現在法律上的權利方面。諸如侮辱、傷害、通奸、盜竊和殺人等刑事罪,在四種姓之間都有不同的規定。特别是屬于雅利安人的前三種姓和屬于非雅利安人的首陀羅之間的不平等關系更為嚴重。僅以侮辱罪來說,《摩奴法典》規定:婆羅門侮辱了首陀羅隻罰款幾個錢,相反,如果首陀羅粗暴地辱罵雅利安人時,要割斷他的舌頭。

法律上的不平等關系也表現在民事方面。以債務為例:假若債務人無力償還債務,而其地位又低于債權人的種姓或屬于同一種姓,在這種情況下須以勞役償還;但如高于債權人的種姓,則可逐漸予以償還。《摩奴法典》的這一規定保證了高級種姓不緻因債務而淪為低級種姓的奴隸。
總之,法典關于種姓制度的一切規定都是為高級種姓的特權利益服務的,也就是為婆羅門和刹帝利等級服務的。前者壟斷宗教大權,而後者壟斷軍政大權,這兩者都屬于統治階級。

第三種姓吠舍,原屬雅利安人的一般公社成員。但随着階級的分化,在吠含中間出現了一些富裕的大商人和高利貨者,他們也應列入統治階級的行列。貧困化的吠舍則逐漸接近于首陀羅的地位,他們組成了當時的平民大衆,其中也有不少人淪為奴隸。第四種姓首陀羅基本上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土著居民,他們的社會地位最為低下,或為奴隸,或為雇工,或獨立過活。他們和貧困化的吠含一起組成為當時的被統治階級。
随着社會勞動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在首陀羅和吠會種姓中間産生了許多從事不同職業的集團。這些不同的職業集團,在瓦爾那制的影響下,也各自逐漸地脫離原來的瓦爾那而形成為一種具有職業世襲化特點并實行内婚制的獨立集團。這些集團印度人稱之為“迦提(Jati)”。
另外,有些落後的山林部落的居民(例如旃茶羅)也在瓦爾那制的影響下形成為這樣的迦提集團。因此,迦提是瓦爾那制的一個發展,在中國的古代文獻中對迦提也使用種姓這一概念。這種迦提在《摩奴法典》中記有五十餘種,其地位也有高有低。其中社會地位最為低下、最受歧視的是旃茶羅。他們被認為是一種不可接觸的人。

在《佛本生經》中曾提到某一年輕的婆羅門因饑餓而吃了同自己一起趕路的旃茶羅的剩飯,事後想起自己是出身高貴的人,非常悔恨,于是把食物和血一起從口中吐出而死。不僅接觸他們或他們的東西被認為是玷污,就是看見了他們也被認為是不幸的。
在《佛本生經》中有這樣一段故事:有兩個旃茶羅進城趕集,在途中為兩個貴族家的女兒所遇。她們本來是想進城趕節日的,但由于她們看見了旃茶羅,便立即跑回家去用香水洗眼晴,因為旃茶羅玷污了她們的眼晴。
《摩奴法典》對這種人有專門的記述:他們須住在村外,不許和他們以外的人來往,當然婚姻隻能在他們自己的卡斯特内進行;他們須穿死人的衣服,用被人家遺棄了的破容器吃飯,帶着鐵的裝飾品入夜,他們不得在村落和城市裡走動,白天工作時,須依國王的命令帶着标識行走。
關于他們的工作,按法典記載是,搬運沒有親人的屍體和執行對犯人的處刑。也有的記載說他們從事于屠夫的職業。這種非常離奇的現象,不僅确實存在于古代,而且一直延續到現代。

殘酷的奴隸制和森嚴的等級制必然要引起奴隸和平民大衆反抗貴族奴隸主的鬥争。關于這一鬥争,我們從佛教文獻和法典的一些教谕式的故事和條文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反映。
例如釋迦牟尼在為波斯置王圓夢時曾說:“王夢見狐上金床,食用金器,後世人,者當貴,在金床上坐,食飲重味,貴族大姓,當給走使,良人作奴婢,奴婢為良人”(《增一阿含經》)。在《摩奴法典》中也有同樣教谕式的條文:假若國王不善于運用懲罰,則“烏鴉就要啄食供神的餡餅”,“下層人就會占據上層人的位置”。這些教谕式的記述,無疑是現實階級鬥争的一個反映。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