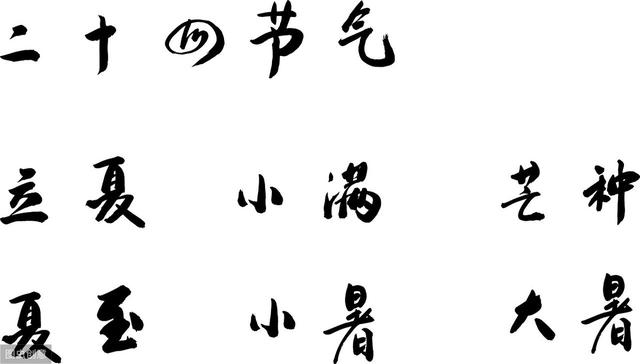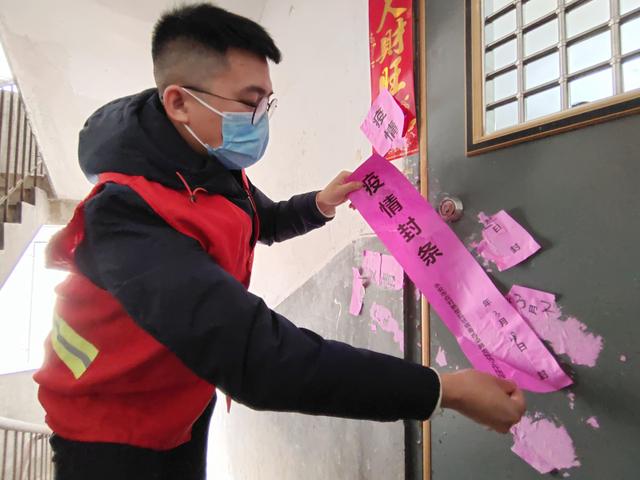羞臭是什麼意思?儒家的核心價值是仁義從儒學史看,孔子貴仁,仁義并重始于孟子《孟子》卷首特載孟子答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1·1)①,可謂揭橥全書宗旨孟子辟楊、墨,亦因其認為二者“充塞仁義”(《滕文公下》6·9)孟文其餘仁義并舉,不勝枚舉為此,朱熹《孟子集注·孟子序說》引程子之言說:“孟子有功于聖門,不可勝言仲尼隻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②無需多言,“仁—義”為孟子思想之基本架構,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羞臭是什麼意思?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儒家的核心價值是仁義。從儒學史看,孔子貴仁,仁義并重始于孟子。《孟子》卷首特載孟子答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1·1)①,可謂揭橥全書宗旨。孟子辟楊、墨,亦因其認為二者“充塞仁義”(《滕文公下》6·9)。孟文其餘仁義并舉,不勝枚舉。為此,朱熹《孟子集注·孟子序說》引程子之言說:“孟子有功于聖門,不可勝言。仲尼隻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②無需多言,“仁—義”為孟子思想之基本架構。
由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需要我們特别關注孟子的義論思想:其一,就孟子本人而言,他對仁義的核心界定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公孫醜上》3·6),然而,孟子對恻隐之心有所論證,仁之内涵亦較為明确,後世學者也有較多論述;但孟子對羞惡之心并無明言論證,其義論的思想内涵亦不甚明了,因此有待我們補證和闡明。其二,從儒家内部系統看,仁的觀念始終獨大,義的觀念隐晦不明,甚至依附于仁,理學家所謂“仁包四德”即其典型(詳下文),因此有必要給予義以獨立的理解和闡發。其三,從中西比較來看,西方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自古希臘的柏拉圖(Plato)、亞裡士多德(Arsitotle)到當代的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其基本主題是正義,相對而言,儒家傳統重仁愛而輕正義。實際上,儒家所謂“義”與西方所謂“正義”(justice)有部分交集,應給予揭示。其四,從古今之變來看,現代社會制度應該建立在義或正義的基礎上,而非仁或仁愛的基礎上。羅爾斯“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③的說法,明确表達了這一點。因此,有必要發掘儒家傳統的義論思想資源。縱觀儒學史,孟子的義論最具原創性和系統性,值得重點關注。
基于以上視域,本文從孟子“羞惡之心,義之端也”這一說法入手,在前賢相關解釋和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孟文的一些例子和論說,補充證明“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然後坐實“羞惡之心”與“義”的内在關聯,最後闡明和揭示孟子義論的實質内涵和理論立場。
一、從恻隐(仁)理解羞惡(義)及其不足
“義”之字形和含義的演變,前賢多有考證,此文聚焦孟子,不拟贅述。隻需說明,自《中庸》所謂“義者宜也”之後,這成了“義”字的一般訓诂,它也經常被用于解釋孟文之“義”論。然而,伊藤仁齋指出:“義訓宜,漢儒以來,因襲其說,而不知意有所不同……學者當照孟子‘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暨‘人皆有所不為,達之于其所為,義也’等語,求其意義,自可分明。設專以宜字解之,則處處窒礙,失聖賢之意者甚多矣。”④而且,“義者宜也”的訓诂乃同義反複,沒有增加任何實質内容,因為何謂“宜”或“合宜”,還得回到“義”本身。實際上,“義”除了較泛的形式化用法之外,尚有屬于它獨自的實質性含義,于孟子仁—義思想架構中的義論而言,更是如此。自然,闡明孟子義論的獨特内涵和理論旨趣,最可靠和直接的方法當然是看孟子本人如何界定和論說“義”。
孟子對“義”最為重要和最具特色的讨論就是把它與“羞惡之心”聯系在一起。孟子勸谏君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時,對“不忍人之心”有所論證: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恻隐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公孫醜上》3·6)⑤
孟子在此通過“孺子入井”這一情景構想來顯示人皆有“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這一訴諸心理經驗感受的論證是相當具有說服力的,無論這種恻隐情感是多麼微弱和短暫,但其真實性和普遍性卻很難被否認。可是,孟子在此對“人皆有羞惡之心”并未提供類似的經驗情景或邏輯論證。從孟子順勢提出人皆有四端之心來看,可能有兩種理由:(1)他認為沒有這個必要,人們完全可以根據“孺子入井”的情景不難設想足以闡明人皆有羞惡之心的類似情景。(2)可以直接從恻隐之心推導出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因此,證明了恻隐之心,也就同時闡明了羞惡之心等。
對此問題,曆代注疏大都囫囵而過,不予重視。不過,朱熹及其門人精研《四書》,铢分毫析,對于此問題自然不會放過。《朱子語類》卷53讨論此章:
又問:“明道先生以上蔡面赤為恻隐之心,何也?”曰:“指其動處而言之,隻是羞惡之心。然恻隐之心必須動,則方有羞惡之心。如肅然恭敬,其中必動。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皆自仁中出。故仁,專言則包四者,是個蔕子。無仁則麻痹死了,安有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仁則有知覺,癢則覺得癢,痛則覺得痛,癢痛雖不同,其覺則一也。”
問:“前面專說不忍之心,後面兼說四端,亦是仁包四者否?”曰:“然。”
恻隐是個腦子,羞惡、辭遜、是非須從這裡發來。若非恻隐,三者俱是死物了。恻隐之心,通貫此三者。⑥
這就是朱子經常談起的“恻隐包四端”和“仁包四德”說。這一觀點可分析出兩層含義:(1)就情感的産生而言,恻隐是前提條件,羞惡等“須從這裡發來”,“恻隐之心必須動,則方有羞惡之心”。兩個“須”字表明,無恻隐則羞惡等就不可能産生。質言之,恻隐是羞惡之必要條件。(2)就主次關系而言,恻隐為主,羞惡等為次,恻隐貫通後三者。如朱子說恻隐是個頭腦,若無此頭腦,羞惡等三者俱是死物。兩層含義亦可概括為一個觀念:恻隐為本,羞惡為末,由恻隐而羞惡。
陳少明先生對此問題的讨論,亦繼承了這一思路。他遵循朱子“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⑦的分别,首先分析了孟子有關“不忍人之心”的另外一個著名事例:齊人拟殺牛釁鐘,齊宣王偶遇,“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梁惠王上》1·7),認為此例中齊宣王因對受難者(牛)的不忍之情而引發對自身行為不當的反思,“這種意識就是羞恥心的萌發。簡言之,不忍或恻隐會觸發對傷害無辜的羞恥感”⑧。依據同樣的邏輯,陳先生又以孟子對“湯放桀、武王伐纣”和“湯征葛伯”等曆史事件的評論來說明不忍或恻隐亦會觸發對傷害無辜的作惡者的憎惡感,這種憎惡感進而引起挺身制惡的行動。其結論是:在孟子的概念中,義包括羞與惡兩層意義,兩者均與對無辜受難者的恻隐之心相關,前者因恻隐而反思悔過,後者則因恻隐而挺身制惡,共同構成儒家對待惡,或者說道德負面現象的完整态度,因此,羞惡與恻隐“在意識經驗中存在内在的關聯,義與仁便非外在的結合,而是一體兩面的事情”⑨。
以上是由恻隐來解釋羞惡的産生機制,就仁義關系言,此思路可概括為“仁包義”或“由仁及義”。與此思路有所不同的是龐樸先生的觀點。龐先生考證,“義”之本義與殺戮有關。他敏銳地注意到: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裡仁》4·3),表明孔子之仁,既講愛人,亦講憎人;孟子以羞惡之心來界定義,便是“原來存于‘仁’之内部的‘能惡人’一面的外現,與‘愛人’的‘仁’處于相反相成之中”⑩。又說:“‘義’被說成是‘羞惡之心’的道德表現,它同‘恻隐之心’的‘仁’相對,并且是對後者的一種節制……有了這一德目與‘仁’并存,‘恻隐’便不免形成一個界限,即隻供使用于所謂的善人善行,而不緻對一切都濫發慈悲。這就叫‘義者,仁之節也”。另一方面,羞之與惡,又是為自己之向善和與人為善,這可說是基于恻隐而起,這就叫‘仁者,義之本也’。”(11)确切地說,龐先生其實注意到仁義關系的兩條路向:一是恻隐(仁)為本,羞惡基于恻隐而起,但其說較模糊;一是羞惡(尤其是惡)對恻隐形成一種界限,義為仁之節制。總體上看,龐先生更為強調後者,對此也說得極為明白。他認為孟子特重義便是出自對墨家兼愛的節制。筆者以為,從孔—墨—孟之思想發展脈絡看,龐先生此說似乎極有道理。然而,就孟子仁義學說而言,其解釋多屬推測。他沒有給出孟子自己的例子,所引“義者,仁之節也”的說法也不是本自《孟子》,而是出自《禮記·禮運》。誠如陳少明指出:“龐先生的論述非常精緻……但它不能用來解釋孟子,因為孟文中沒有一處表現出對過度‘恻隐’或慈悲的擔心而認為需要對其加以限制的,相反,是唯恐擴之未盡。”(12)
筆者贊同這一批評。然而,宋明儒者對仁義的理解,除了“仁包四德”說之外,他們的整體思想傾向強調更多的正是龐先生所說的“義為仁之節制”。如程頤在論張載《西銘》時提出“理一分殊”說:“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無别而迷兼愛,至于無父之極,義之賊也。”(13)朱子繼承和發展了“理一分殊”理論并特别強調“分殊”:“仁,隻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個物事底便是義。仁隻是那流行處,義是合當做處。仁隻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裡,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于天下國家,隻是這一個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差等。”(14)就連大談特談“萬物一體”論的王陽明亦說:“《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逾越,此便謂之義。”(15)總而言之,宋明儒者基本上是把“義”理解為一種界限,一種對仁愛流于無差等之愛的節制。雖然在他們的論述中,這種界限和節制不是針對作惡者,而主要是就情感(愛)的親疏厚薄而論,但以意推之,宋明儒者對待作惡者的态度,不能濫施仁愛,自是題中應有之義(16)。筆者以為,把“義”理解為差等之愛,根源于秦漢以降“義者宜也”這一常見訓诂:宜親親而仁民,宜仁民而愛物,這無疑是儒家的核心觀念之一。然而,用“義”來表達或說明差等之愛的合理性,絕非孟子義論的本意和主要内涵,否則,孟子完全可以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也”。不難看出,在宋明儒者的解釋中,義的實質性内涵其實被虛化,它從相反的角度表明義從屬于仁,亦即義不過是仁的适當應用和節制罷了。
綜上所述,前賢對恻隐(仁)與羞惡(義)之關系的理解有三:(1)認為恻隐是羞惡的必要條件(朱子);(2)恻隐可觸發羞惡(朱子、陳少明);(3)義不過是仁之合宜的流行發用(宋儒)。就孟子本人的思想而言,筆者以為(1)和(3)顯然不對,因為後文将會看到,有些情況下羞惡的産生與恻隐無關;至于(3)則是宋儒之義論,與孟子義論無關,雖然他們經常把它與孟子聯系在一起,而且确實與孟子的某些思想相符。第(2)種觀點值得仔細分析。确實,一個麻木不仁的人我們很難想象他會有羞惡之心,而一個很容易義憤填膺(姑且不論是否得當)的人也往往是一個具有悲憫情懷的人,相較而言,恻隐确實比羞惡更為根本。但是,筆者更願意把羞惡理解為是對自己或他人不當行動的一種本能的情感反應(前引朱子對“羞惡”的注解即強調是對“不善”之恥、憎),如果這種不當行動造成了對無辜者的傷害,那麼這種羞惡情感則會因為主體對無辜受害者的恻隐同情而變得更加強烈。也就是說,羞惡的産生根源歸根結底是對不當行動本身的心靈反應,對無辜受害者的恻隐隻是加強了這種反應。此外,以上三種理解都強調恻隐的根本性,這于孟子來說,确實有此傾向。但是,從本文引言所述之中西視域和古今之變來看,作為當代的诠釋者,我們很有必要對羞惡與義盡可能賦予其獨立的理解。而且,後文我們将會看到,孟子本人也确實在一定程度上賦予其獨立性。
二、人皆有羞惡之心的例證與闡明
實際上,在孟子的思想中,羞惡的産生不必以恻隐為必要前提,義的内涵亦不必完全借助仁來界說,羞惡與義都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而且,孟子确實也提供了一些有關“羞惡之心”的例證和闡明。其中的典型例證便是“嗟來之食”。《告子上》載孟子之言曰: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11·10)
此章單獨論“義”,不涉及“仁”,主題是“舍生取義”。此種大義往往使人聯想到文天祥這類民族英雄,但卻很少留意孟子是通過一個小情景來顯示這番道理。孟子說:今有饑餓之人,有人施舍箪食豆羹,饑者得之則生,弗得則死,然若施舍者呼爾而與之,那麼即便是一般的行路之人也不會接受這種施舍;倘若施舍者蹴爾(以足踩踏箪食豆羹)而與之,那麼即便是瀕臨餓死的乞丐也不會接受這種施舍。路人和乞丐為何不接受此種施舍,原因即在于他們具有羞惡之心。孟子沒有明言,但朱子《孟子集注》于此明确點出了這一點:“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甯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于生死者,人皆有之也。”孟子此文末提到“失其本心”,所謂“本心”就是人所固有的恻隐、羞惡、辭讓(或恭敬)、是非之心,此處當特指羞惡之心。所以朱子《孟子集注》于此章宗旨又雲:“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17)
孟子所述此故事,讓人想起儒家所說的“嗟來之食”的典故。《禮記·檀弓下》載:“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屦,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18)在此故事中,施舍者吆喝餓者“嗟!來食”(類似孟文“呼爾而與之”),餓者因羞恥之心而不接受此嗟來之食;即便黔敖意識到自己的無禮行為後馬上向餓者緻歉,餓者亦終不接受而餓死。在此例子中,餓者具有非常強烈的羞惡感,這從此人來時“蒙袂輯屦”、之前再三拒絕嗟來之食,以及在黔敖緻歉之後仍不接受其施舍,都充分表明了這一點。所以曾子并不完全贊同其行為,認為實無必要如此:當黔敖嗟時可辭去,而當黔敖緻歉後則可接受。這裡涉及羞惡的适當與否,姑且不論。無疑,此例也足證“羞惡之心”的實有,沒準孟子所述或許就脫胎于此故事。此外,羞感和惡感似乎是同時産生,比如在“嗟來之食”(因其性質相似,筆者以此統稱孟子所述“呼爾”和“蹴爾”之食)的情形中,主體(路人和乞丐)因自尊而感到羞恥,同時也因施舍者的無禮而對彼感到厭惡。在此,主體羞惡感的産生并不需要恻隐或不忍來觸發,更不必說以其為必要條件了。
孟子通過饑者不願受嗟來之食,來顯示饑者羞惡之心之實有。然而,個殊羞惡之心的實有,并不能推出“人皆有羞惡之心”的普遍判斷。在孟子的思想體系中,從個殊到普遍的銜接,是通過“心有所同然”來完成的。《告子上》雲:“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刍豢之悅我口。”(11·7)從經驗觀察可知,人之口、耳、目等外感覺有共同的好惡;既然外感覺有共同的好惡,難道人之心這一内感覺反而沒有共同的好惡麼?在此,孟子通過感覺經驗和類比推論,對“心有所同好”做了緊縮論證。孟子的這一設問和反思,蘊含了肯定的答案。至于這一判斷是否為真,即便在哲學理論或經驗科學如心理學、生物學等高度發達的今天,恐怕仍難給出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答案;但我們每個人确實可以通過自身經驗和某種反思,大體上認可這一說法。在筆者看來,“嗟來之食”堪與“孺子入井”的例證等量齊觀,彼處旨在證明“人皆有恻隐之心”,此處旨在證明“人皆有羞惡之心”,雖然彼處是明言論證,此處是隐含論證,兩者都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就羞惡之心而言,我們甚至可以想像,即使饑者接受了嗟來之食,也很難就此否定他沒有羞惡之心,而隻能說明求生本能勝過了羞惡之心。
回到此章“舍生取義”的主題。孟子認為:欲生惡死,乃人之常情;然而,所欲有甚于生者,此就是“義”;所惡有甚于死者,此就是“不義”。因為有義(或羞惡之心),所以不為苟得;因為害怕陷于不義,為人恥笑,所以患有所不避。如果使人所欲莫甚于生,那麼,人們為了生存就什麼苟且之事都幹得出來;如果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那麼,則但凡可以躲避患難的行為,亦什麼都可以幹。而這種所欲有甚于生的“義”和所惡有甚于死的“不義”,就起源于羞惡之心。孟子認為此心“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随後他即以“嗟來之食”的例子來表明即便是饑餓的路人和乞丐亦有是心。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孟子這裡反複強調心之“所欲”和“所惡”,這就直接把“羞惡”與“義”或“不義”聯系起來了。情感能夠引起主體對某行動或事件的贊許或譴責(羞惡之心側重在“所惡”和譴責),換言之,引起主體的道德判斷,進而有可能引起主體的行動選擇。就此而言,孟子似乎表達了類似英國哲學家休谟的一個觀點,即道德區别或道德判斷的根基在道德情感(19)。在此段末尾,孟子說:如果萬鐘(代表權勢财富)不辨是否合乎禮義而一概接受,那麼這樣的士尚不如路人和乞丐能出于羞惡之心而斷然拒絕不當得利。若此羞惡之心一旦泯滅,則任何惡事皆有可能做得出,也正因為此,孟子反複強調“養心”和“擴而充之”。在孟子看來,即便這種富貴可以給自己帶來宮室之美,能夠奉養妻妾,甚至可以救濟窮乏者,但如果這種富貴不符合禮義,則仍不可取。無疑,這裡我們也看到孟子一貫強調“義利之辨”中義之于利的優先性。
三、擴充羞惡之心于事事物物
我們還可以從《孟子》那裡找到一個足證“人皆有羞惡之心”的經典例子,這就是“穿踰之心”。《盡心下》載孟子之言: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于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14·31)
在此,孟子同樣通過一種“以小見大”的方式來顯示羞惡之心的實有。此所謂“無欲害人之心”即恻隐之心,所謂“無穿踰之心”即羞惡之心。毫無疑問,人們都羞恥于自己為穿穴踰牆之盜行,也都憎惡他人為穿穴踰牆之盜行。總之,人們羞惡于為盜(哪怕是僅有為盜之心),因此也都知道為盜為非或為不義,這是十分顯白的事實,這亦可證“人皆有羞惡之心”。孫奭《正義》疏解此章便點出了這一點:“人能充大不欲害人之心而為仁,則仁道于是乎備,故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無穿踰奸利之心以為義,則義于是乎盡,故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不受人爾汝之實,是不為人所輕賤,故無所行而不為義者也,言所為皆可以為義矣。蓋恻隐有不忍者,仁之端也;羞惡有不為者,義也:但能充而大之,則為仁義矣。”(20)可以說,孟子此文是對“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和“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更為翔實的論述。此但就羞惡與義的關系論,所謂“人皆有所不為”即是羞惡之心不喜為或不欲為之事,如孟子在此提到的穿踰為盜和受爾汝之實。關于“爾汝之實”,趙岐注:“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22)可知“爾汝”是人們對元德之人的一種賤稱,其性質有點類似“呼爾”和“嗟來”,帶有蔑視和侮辱。不難想象,即使是一個無德之人,當他被别人如此輕賤地稱呼時,他也一定有羞惡之心,羞恥于自身德行不好,又厭惡于他人帶有蔑視和侮辱的稱呼。孟子之意,正在于引導人們“充無穿踰之心”和“充無受爾汝之實”,由不喜為顯而易見的不當行為發展到不喜為并不那麼顯而易見的不當行為。這就是孟子所說的“人皆有所不為,達之于其所為,義也”。“有所不為”,即指那些顯白的羞惡之心不喜為之事;“其所為”即指那些不那麼顯白的羞惡之心不喜為之事。所以,這句話的正确理解是:人們皆有羞惡之心不喜為之事,把此擴充到那些曾經昧着羞惡之心(或應當羞惡卻沒有羞惡意識)所為之事而能不肯再為,這就能形成完整而健全的義與不義的道德判斷或是非善惡标準。在“穿腧為盜”的例子中,我們也看到,羞惡感的産生不必以恻隐為前提或由恻隐而觸發,它就是對不正當行為的一種類似本能的情感反應。
實際上,儒家經常使用“穿踰”之譬。《論語·陽貨》載孔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17·12)邢昺《正義》雲:“言外自矜厲,而内柔佞,為人如此,譬之猶小人,外雖持正,内常有穿壁窬牆竊盜之心也與。”(22)色厲内荏之人就好像常懷有穿窬盜竊之心的小人一樣,這也可以反過來理解,常懷有穿窬盜竊之心的人,一定是色厲内荏。為何如此?因為羞恥于為盜(哪怕僅有為盜之心),所以在世人面前要故作色厲,然其羞惡之心不能自已,無法欺騙自己,故必内荏。這一心理現象似乎也可為孟子“人皆有羞惡之心”的命題做一注腳。此外,孟子還講述了婚姻中的“穿踰”行徑說:“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滕文公下》6·3)古代婚姻需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能成禮;隻有經由此種禮儀,婚姻才具有有效性或合法性。如果男女雙方不顧此等禮儀(在彼時實具有民法效力),像竊賊一樣偷偷摸摸戀愛,那麼父母國人都會輕賤之。對于一般男女而言,也羞于此等鑽穴踰牆的行徑。孟子此論,意在說明出仕之道:“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同上)既然羞惡于穿踰為盜和鑽踰戀愛,自然也應把此羞惡之心擴充到出仕事務上,堅守出仕之正道,拒絕枉道求仕。
由小見大,由顯而隐,擴充羞惡之心于事事物物上,主體就能養成健全的有關是非善惡的道德區别與道德判斷;若人人如此,則整個社會也就會形成一套健全的是非善惡标準,亦即義與不義的價值判斷和标準。孟子對此反複申論,除了前文論及的“充無受嗟來之食”“充無穿踰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外,相似的說法反複出現在孟文中:
(1)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離婁下》8·8)
(2)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盡心上》13·17)
這兩句沒有上下語境的話,往往被人所忽視,甚至不得其解。其實,聯系孟子的用語和整體思想來看,這兩句話顯然是在談論羞惡之心與義的關系。實際上,曆代注家也看到這一點。所以,孫奭《正義》疏解(1)雲:“此章指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為;不為非義,義乃可由也。孟子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義矣。又所謂‘人皆有所不為,達之于其所為,義也’,亦是意也。”(23)孫奭引用他處孟子說義之文解釋此章,以孟解孟,可謂深契孟子。朱子《集注》于(2)引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于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24)朱子明确用羞惡之心和義來解釋此章,亦可謂深契孟子。實際上,此兩章皆可視為“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和“擴而充之”的補充說明。
如果有所留意,不難發現,在孟子的談論中,羞惡之心總是與食物、職位、富貴等益品(goods)的取與相關,這表明孟子的義論思想主要關乎這些益品的取與。由于彼時社會環境和自身的處境,在孟子的論述中,他往往把羞惡之心特别地與出仕之道聯系在一起;而仕與不仕小則關系到個人之衣食溫飽,進而是個人之富貴,大則關系到兼濟天下。可見,在彼時,出仕之道既是觀察一個人是否有羞惡之心(義德)的重要途徑,亦是衡量一個社會是義或不義(義政)的重要标準。實際上,在當代社會,獲取職位尤其是進入公共職位的原則和方式,仍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正義的重要判準。
孟子曾講述齊之某良人餍足酒肉的故事。此良人(丈夫)有一妻一妾,他經常到人家墳墓祭祀處乞讨酒肉。如此餍足之後,返回家裡,告其妻妾,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并以此來驕其妻妾。其妻頗懷疑,一日遂暗中尾随,發現其龌龊行徑,返回乃與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孟子講述此故事後,如此評論:“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離婁下》8·33)這裡的“羞”,不是這一妻一妾恥己之不善,而是替其良人感到羞恥,當然,這種羞恥也含有對良人的厭惡(由“讪其良人”可證)。此良人可羞惡之處頗多,但根本處在于其餍足酒肉的方式幾無羞惡之心,謀生之道十分不正當。從孟子的評論可知,孟子正是意在借此來諷刺當時之人枉道以求富貴利達的行徑。值得一提的是,良人羞于向妻妾吐露實情,這似乎也表明良人實有羞惡之心,隻是他未能守住羞惡之心之不欲為的底線。所以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11·11),就是要人們通過反思,找回喪失的羞惡等本心,守住做人做事的底線。
孟子與弟子又有關于“羞”于“枉尺直尋”的讨論,在此值得好好分析。《滕文公下》載: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複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禦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6·1)
有諸侯招聘孟子(可以想見,是以不符合道義或禮義的方式招聘孟子),孟子不見,于是弟子陳代建議孟子委屈小節,應聘諸侯,可成就大功。陳代又引古人“枉尺而直尋”之諺語來勸谏。何謂“枉尺而直尋”,朱熹《孟子集注》:“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緻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尺小尋大,陳代建議孟子屈小伸大。孟子沒有直接回應,而是先講了兩個故事:一個是虞人因齊景公招聘不合禮(應當招以皮冠而齊景公招以旌)而甯死不就;一個是禦者王良不肯以不合禮法的手段獲禽,且羞與小人(趙簡子嬖臣)為伍。孟子之意,即使處低賤職位的虞人和禦者尚且羞于以詭道(不正當的方式)謀求職位或被任用,更何況作為士君子,焉能毫無羞惡之心,枉道以求仕?更為重要的是,在孟子看來:(1)枉尺直尋,屈小伸大,這是功利的算計。如若專以功利計,則“枉尺直尋”必将走向“枉尋直尺”,亦即由“屈小伸大”走向“屈大伸小”,最終走向為一己私利而犧牲天下公利。孟子反複強調,若未能守住羞惡之“端”,則必将走向物欲橫流。(2)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這是儒家對政治的基本理解和信念。孔子就曾說過:“政者,正也。”(《論語·顔淵》12·17)“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13·6)孟子無疑認同孔子的觀點:“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離婁上》7·20)孟子非常清楚,枉尺直尋,即便見用于諸侯,由于自身不正在先,焉能格君心之非?
如前所言,孟子談論羞惡之心,幾乎總是與食物、職位、富貴等益品的取與有關。實際上,這正是孟子對“義”的另外一個在筆者看來非常關鍵和重要卻為人所忽視的界定: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盡心上》13·33)
在此,孟子對“仁”“義”做了一般化的界定,雖然是以否定的方式——即何謂“非仁”“非義”——來界定。殺一無罪非仁也,表明仁主要與生命關懷或生命權為其實質内涵。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表明義主要與食物、職位、财富等益品的取與有關。所謂“非其有而取之”概有兩類:(1)私人關系中,屬于他人的财貨,你通過某種不正當的方式奪取;(2)依係于公共職位的富貴等益品,你通過某種不正當的手段或方式來獲取。我們這裡可以把“義”換成“羞恥之心”,則此命題為:“非其有而取之,無羞恥之心也。”這樣一來,羞恥之心與義的内在關聯,便一目了然。重要的是,仔細琢磨,這裡的“義”蘊含有正當、權利(right)的觀念。理雅各對“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的英譯就加進了right一詞:“How to take what one hasnot a rightto is contrary to righteousness。”(25)“正當”“權利”正是反複出現在西方各種正義論中的核心概念。就此而言,孟子義論與西方正義論的某些主題有實質性的交集。
正是基于這一界定,孟子說:“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系馬千驷,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萬章上》9·7)他人授予你天下,賜予你系馬千驷,如果不符合道義,你就不應當接受,甚至不該心存觊觎。面對大富貴如此,面對一介之微物亦如此:如果不符合道義,即便一介之微物也不應該與人或取之于人。孟子此說明确表達了權利界限觀念和權利的不可侵犯性原則,具有鮮明的道義論(deontologyr,或譯義務論)立場。這種立場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公孫醜上》3·2)的表述中,得到了更加凝練有力的表達。筆者曾在他文指出,孟子這一表述非常類似當代道義論的著名代表羅爾斯的表述:“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26)不難發現,兩者的基本立場若合符節,都明确反對功利主義,無論這種功利是天下大利還是社會整體利益,它都不能犧牲個體的正當權利。在此,筆者固然借助西方道義論來揭示孟子義論所蘊含的理論内涵,但卻不是借彼來證明此的絕對真理性;因為所有道德理論大體上都可劃入要麼道義論、要麼功利主義(或後果主義)的陣營(27),而此兩者到底孰優孰劣,誰更有說服力,這在西方學界,時至今日,仍在不斷争論和讨論。筆者僅就學理的角度,分析指出孟子義論所體現的基本思想傾向大體屬于道義論陣營。
以上是關于“義”的界定和由之而形成的一般原則。孟子對于此種不義,亦談及具體事例。《滕文公下》載: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6·8)
“攘雞”(即偷雞)顯然是通過一種不正當的方式獲取他人财物,其不義性顯而易見,人人皆知。同理,政府對人民橫征暴斂,同樣是不義,而且是更大的不義。這裡的不義主要表現在政府賦稅不合比例。政府賦稅過重,這無異于從黎民百姓手中竊取财物。而且,正如孟子反複強調,财物之取與的正當性(義)或不正當性(不義),并不會因為财物之小大多少、程度輕重而改變。日攘一雞為不義,則月攘一雞亦為不義。同理,政府嚴重超過賦稅合适比例是不義,則輕度超過此合适比例同為不義。在此,孟子再次娴熟地運用了“以小見大”和“由顯見隐”的方式,充分說明了政府橫征暴斂的不義性質。我們也再次看到,孟子之義論,不僅僅局限于主體德性的養成(義德),以及個人之權利訴求,它指向的是整個社會制度(義政),目的在于改良社會制度,以使其更加公正。
陳少明敏銳地注意到孟子羞惡之惡是研究儒家正義感的一條線索,并指出作為性善論奠基者的孟子,一開始就正視世界存在着邪惡,主張面對邪惡挺身而出,行俠仗義或替天行道。這很有見地,但筆者不敢苟同他對孟子正義觀的如下說法:“它不是利益主體自身的權利訴求”,“與當代思想中流行的合理利己主義正義觀比,孟子式的利他主義的正義觀,在處理常态的社會交換中,作用受限制是顯而易見的”(28)。确實,孟子雖然并不否定社會交換的必要性(詳孟子對“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的批評,見《滕文公上》5·4),但其義論不是直接讨論交換原則和分配原則(像亞裡士多德和羅爾斯等那樣),而是太多地聚焦在出仕(如辭受進退)原則方面,這有其自身曆史境域的局限。但是,如前所析,孟子的正義觀中無疑含有權利的觀念,包括自身權利訴求的合理利己主義觀念,實際上,孟子本人就曾多次為自己的合理權利辯護(29)。而且,筆者認為這是孟子義論所蘊含的比較重要的一項内涵。
一般而言,出于恻隐和仁愛而要求提供積極幫助的行動,是較高的道德義務,但卻不是不得不為的道德義務;而出于羞惡和義的行動,則近于底線的道德義務,不為不義的禁制性道德義務更是如此。孟子由羞惡談論義以及經常由不義來論說義,這本身就表明義所規定的義務更多是禁制性的。此外,我們常說“義不容辭”而不說“仁不容辭”,亦表明了這一點。其實,孟子本人已有類似說法:“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離婁下》8·11)孟子不說“惟仁所在”而說“惟義所在”,這與孔子不把“忠”道而把“恕”道視為“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論語·衛靈公》15·24)的道理相同,因為“恕”和“義”大都是底線的道德義務要求。進而言之,就人之常情而言,自身權利的合理訴求顯然較利他主義的義務為急切;就良好社會的形成而言,有一套明确的禁制性的道德義務和原則規範比高談利他主義的仁愛精神更為有效;就政府責任而言,“義政”要求政府不侵犯黎民權利,消除明顯的惡與不義;“仁政”要求政府愛民如子,視民如傷,顯然,前者之于政府的義務要求較後者更為迫切而不可寬貸。這是我們在當代社會更應重視孟子義論的緣由所在。孟子義論的特色是把它與羞惡之心聯系在一起,這也隐伏着其短處,即他對主體羞惡之心所激起的道德自律太過樂觀,而對個體權利的保障機制則缺乏充分的考量,雖然他已經實質性地涉及此問題。
【注釋】
①本文凡引《孟子》,皆據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②[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99頁。
③[美]約翰·羅爾斯著,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正義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1頁。
④[日]伊藤仁齋:《論孟字義》“《仁義禮智》”第九條,吉川幸次郎、清水茂校注:《伊藤仁齋、伊藤東涯》(日本思想大系33),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第131頁。
⑤孟子談論四心與四德的關系凡兩見,另見《告子上》11·6:“恻隐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彼雲“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此雲“羞惡之心,義也”。通觀《孟子》,羞惡之心隻能理解為義之端而不能徑直等同于義(詳後文)。
⑥[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297、1289、1289頁。
⑦[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37頁。
⑧⑨(12)陳少明:《仁義之間》,《哲學研究》2012年第11期,第35頁。
⑩(11)龐樸:《儒家辯證法研究》,劉贻群編:《龐樸文集》第1卷,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50,452頁。
(13)[宋]程颢、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下冊,第609頁。
(14)[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7冊,第2527頁。
(15)[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8頁。
(16)有關宋明儒者的仁義說,詳參陳喬見:《普遍之愛與特殊之愛的統一如何可能——以宋明儒者仁義說為中心的考察》,《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17)[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33頁。
(18)[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98頁。
(19)詳見[英]休谟著、曾曉平譯:《道德原則研究》附錄一《關于道德情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
(20)(21)[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778頁下欄。
(22)(23)[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下冊,第2525,2726頁下欄。
(24)[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53頁。
(25)理雅各(James Legge)譯.The Works of Mencius.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262頁。
(26)[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第1頁。詳參陳喬見:《公私辨:曆史衍化與現代诠釋》,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第201-202頁。
(27)我基本贊同牛津大學哲學教授羅傑·克裡斯普(Roger Crisp)的看法:“道德理論可以合理地被區分一方面是廣義的後果主義,另方面是非後果主義或者說道義論。”見Roger Crisp.Methods,Methodology,and Moral Judgement:Sidgwick on the Nature of Ethics.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2013/4。他也解釋了德性倫理學為什麼不是一種獨立的理論,而是非功利主義的道義論的一種形式。見Roger Crisp.A Third Method of Ethics?.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2015,Vol.90(2),pp.257-273.儒家具有鮮明的德性倫理學特征和道義論的立場傾向,這與克裡斯普的判斷也頗為吻合。
(28)陳少明:《仁義之間》,《哲學研究》2012年第11期,第40頁。
(29)詳見《滕文公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章(6·4)。
(原載《中山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