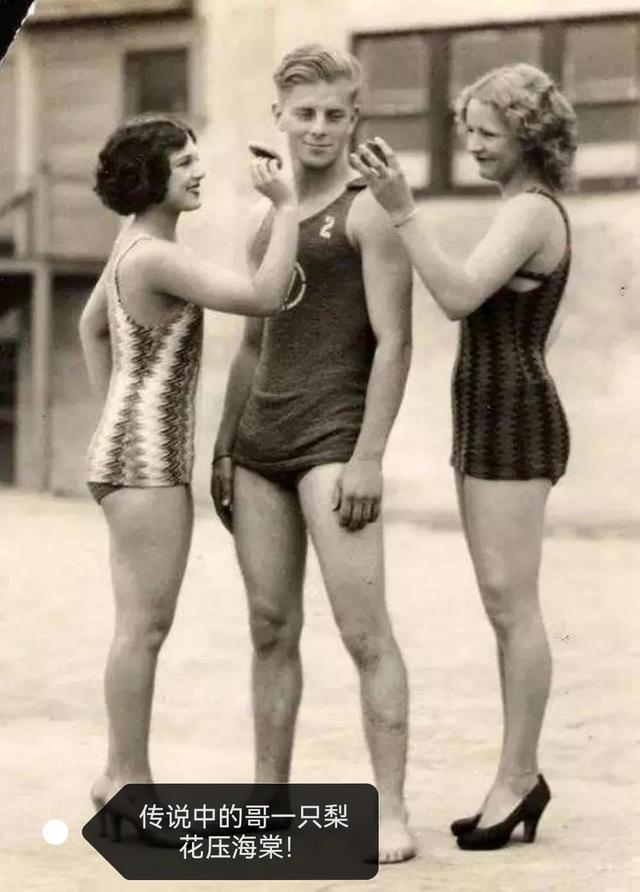疫情期間,高中班長在群裡發起網上聚會,号召身處全球各地的老同學們一起視頻見見。
看到消息的那一刻,我突然渾身燥熱,十多年前的羞恥感再次席卷而來。
說起來讓我羞恥的也不是什麼大事,但就是難以釋懷。
高中時的英語老師是個非常時髦又嚴苛的老太太,現在想來,她的教育理念非常先進,但當時對于我這個從農村進到大城市裡重點高中的小姑娘來說,她就像難以讨好的“皇太後”。她最喜歡做的事就是找一些課外閱讀材料,讓我們當衆朗讀并翻譯。我的高中時代就在兩個這樣的時刻中徹底陷入了地獄。
第一次是高一剛開始,為了了解大家的英文水平,每個人都要做自我介紹,我還沒說兩句,就聽到非常鄙夷的評價,大概意思就是發音不标準,還比不上小學生之類。那一刻,全班的靜默簡直是一種無聲的淩遲。
第二次是我在完全沒看懂課外材料的意思時,突然被點名起來翻譯,結果,果然招緻英語老師更加尖酸且無情的嘲笑,說我連基本的單詞意思都不懂。當時,不是“恨不得找個地縫鑽下去”,而是希望自己永遠消失,永遠忘記當下的一刻。
至今,教室裡隐隐傳來的嗤笑聲還回蕩在耳邊。
所以,想到高中,想到英語,那種羞恥感立即會卷土重來。
對于我的同學們來說,那兩個時刻,也許早就像高中時做完的無數張試卷一樣被遠遠抛棄和遺忘了。但對于我來說,那兩個時刻所體驗到的羞恥感,卻一直伴随我,并可能跟随我一生。這兩個時刻讓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愚蠢至極,哪怕我後來的高考英語135分,哪怕我的高考成績是全校前十,都無法挽救自己的自信心。
每當羞恥感來襲,我的情緒就會陷入失控,我的生活和人生也随之陷入一陣暫時的停頓。

TED五大最受歡迎的演講者之一布琳·布朗曾在她的演講中這樣解讀“羞恥”:
羞恥是一種讓我們相信自己有缺陷的,因此不值得被愛或獲得歸屬感的強烈的痛苦感受或經曆——我們所經曆的,做過的或沒有成功做到的事情,讓我們不配獲得他人的感情。
近年來,羞恥(shame)引起了越來越多心理學研究者的關注,甚至有人提出,最具破壞性的負面情緒,不是悲痛,不是憤怒,而是羞恥。因為羞恥從根本上動搖了我們的自我價值。
幾乎每個人都曾經曆過感到羞恥的時刻,很多羞恥隻是為了約束我們的行為不要越界,也有一些羞恥,會深刻影響我們的一生,這些羞恥的共同點是它們在一點一滴的積累中改變了我們對自我的認知。

《如何停止不開心:負面情緒整理手冊》(How To Stop Feeling Like Sh*t: 14 Habits that Are Holding You Back from Happiness) 一書的作者安德烈娅·歐文(Andrea Owen) 在書的前言中介紹了自己曾經經曆的人生低谷:
在她懷孕的時候,同時經曆了失業、被抛棄、無家可歸,在這種最需要幫助的情況下,她的感受是“深深的羞辱”,她根本無法忍受家人、朋友和同事的同情,她感覺自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女人,居然無法挽留自己的愛人。
後來,在參加了布琳·布朗博士的訓練營之後,她終于意識到,是羞恥将自己推入了“自我毀滅”的深淵之中。
安德烈亞·歐文在書中介紹了14種自我毀滅的行為模式:自責、孤立自己、麻痹自己、與他人比較、自毀、冒充者綜合症、取悅他人、完美主義、故作堅強、過度控制、災難性思維、歸咎于人、犬儒主義和過度追求成就。這些行為模式的背後,有着共同的根源,那便是過于在意他人對自己的看法,總會為羞恥感所淹沒。

為什麼羞恥感與我們如影随影?尤其是與女人密切相關?原因有三點:
其一,重視人際關系的價值觀和“恥感”文化從根源上造成深層次影響。
心理學上将東西方文化在大的層面上區分為集體文化和個人文化兩種價值觀取向。對于東方人來說,集體文化價值觀讓我們更加側重人際的關系,而非個性化的表達,因此,能否融入大的團體變成了非常重要的問題。集體也正是通過潛在的規範來約束其中每個個體的行為。
這就使得在集體文化中的個體更容易感受到羞恥所帶來的巨大影響。一旦個體的表現超過了集體的規範,就很容易招緻集體中其他個人的評價和社交壓力。
人際圈子越是緊密,羞恥帶給人的影響力就越是明顯。
其二,社會輿論不理性,網絡暴力橫行。
我們經常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吊詭的現象:在受到侵害之後,女人明明是受害者,卻還要承受社會的輿論壓力;網絡上的“鍵盤俠”放任侵害者不理,卻對受害者大肆議論和無端指責。
這種社會輿論的風氣讓女人很難勇敢地袒露自己的脆弱和無助,因為這種袒露反而會成為自己的軟肋而任人攻擊。
更可怕的是,社會輿論不僅無視了女人所受到的傷害,還從根本上打擊女人的自尊和自我價值,讓女人懷疑自己存在的意義。
網絡暴力,是名副其實的“羞恥放大器”。
其三,女人本身情感豐富,對外界評價更為敏感。
當發現愛人出軌的時候,錯的明明是對方,但那種羞恥的感覺還是會揮之不去。
是不是因為我做得不夠好才導緻他愛上别人?現在别人會怎麼看我?大家會不會覺得我是個失敗者?那個她一定比我聰明、漂亮還善解人意吧?鄰居最近看我的眼神好像都不太對了。不知道爸媽聽到這個消息會怎麼想……
人們都說,女人的心思千回百轉,情感異常充沛,也正因如此,女人對于别人無意間流露出的感情、态度都非常敏感,很容易捕捉到字裡行間的隐含意義,不自覺就會陷入猜測和擔憂之中。
所以羞恥感強的女人很難找别人咨詢意見,他們在傾訴的過程中會一直留意對方的反饋,一旦發現對方似乎不能理解自己,便會很快逃離,以防止自己被他人品頭論足。
越是敏感細膩,就越是受其所累。

總是被羞恥控制的人很難正常排解自己的情緒,他們經常會選擇以不健康的方式對内或對外發洩内心的怒火。
他們害怕别人的評價,擔心别人看到自己最脆弱的一面,恐懼别人同情或鄙夷的眼神,于是他們用厚厚的铠甲将自己包裹起來。
因為得不到他人的理解和安慰,他們很可能選擇自我麻痹,用購物、暴飲暴食、酗酒、沉迷網絡或遊戲、瘋狂加班等方式來麻醉自己,獲得片刻的欣悅或喘息,然後,陷入更深的惡性循環。
人前強裝歡笑,人後黯然神傷。
時間并不會療愈所有的傷口,時間隻會讓孤獨的受害者在黑暗的夜裡不斷自我懷疑,加深自責與自毀傾向。

難道就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救嗎?
在《理性情緒》一書中,著名心理學家阿爾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提出要用“無條件的自我接納(unconditional self-acceptance,USA)替代有條件的自尊(conditional self-esteem,CSE):
用自己的主要生活目标以及是否能助你達成目标來評價、判斷自己的信念、情感和行為。如果能達成目标,你則認為它是“好的”或“有用的”;反之,你則認為它是“不夠好的”或“沒用的”。但是,謹記不要讓這些影響了對自我的評價,無論你的表現好或不好,無論别人是否認同你和你的所作所為,你都需要接納并尊重自我、自己的人生和作為人存在的價值。
在這一觀點中,自我是中心,我們首先要認識到自我的價值是由自己決定的,而非其他任何人或任何事件。就像父母會無條件地愛自己的孩子一樣,我們也要無條件地愛自己。

而在《如何停止不開心:負面情緒整理手冊》中,作者又提出多種具體的操作方法,其中有兩個方法是從最根源來告别羞恥感的負面影響的,第一個方法是認清自己最看重的價值,第二個方法是認清真正可以影響我們的人。
如何才能認清自己最看重的價值?
我們可以列出很多有價值的事物,比如勇氣、自由、創造力、誠實、信任、公正、助人等等,在列出這些價值之後,我們需要做的是,描述這種價值對于自己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以“勇氣”為例,勇氣對我來說是什麼?
勇氣不是要一個人抗下全世界,不是用尖銳的刺武裝自己,而是願意将自己最脆弱的一面暴露在信任的人面前,讓他們為我療傷。

如何才能認清真正可以影響我們的人?
我們可以列一個最短的名單,例如在一個3×3厘米的格子裡寫下那些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人的名字,隻有這些人的意見才是值得我們聽取和在意的,隻有我們最信任的人才可以影響我們的人生。
在這個格子之外的人,無論他是達官顯貴,還是網紅明星,他們的話語和評價對我們的人生來說都是毫無意義的。我們根本不應該因為他們的一句話或一個眼神而羞愧難當、苛責自己,我們也完全不必要為了他們而改變自己。
真正可以影響我們的人,屈指可數。

終其一生,我們都在逃避羞恥帶來的痛苦,我們都在擺脫他人的目光,試圖自在地活出真我。
高中畢業已經十多年了,但十多年前的英語老師依然是我的夢魇。
也許我的夢魇并不真的是那位老師,而是她所代表的讓我羞恥的感覺,是她所給予的那些讓我誤以為自己無能、愚蠢、不可救藥的評價。
曾經,我的每一次情緒失控,都伴随着對自我價值的懷疑,都是一次羞恥的體驗;
現在,我在嘗試奪回屬于自己的勇氣,劃定我的重要他人,讓我的羞恥隻讓少數人看到,讓我的羞恥成為成長路上的墊腳石。
即使曾經紅過臉,依然可以笑開顔。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