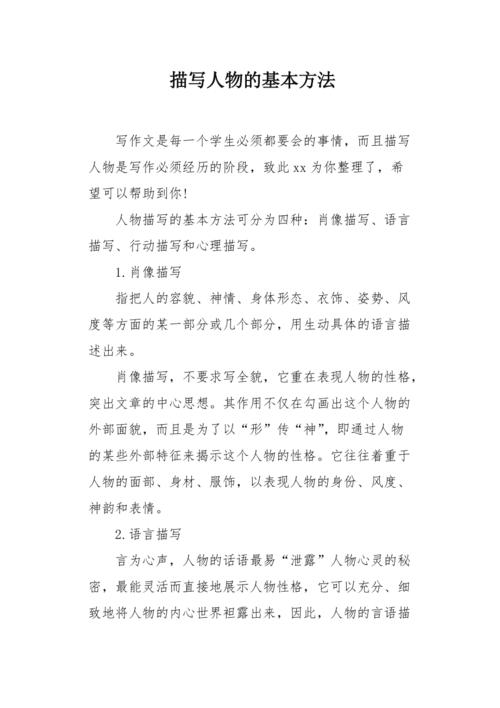一晃眼,很久沒在央視看見董卿了。
直到前些天她登上熱搜,憑借一手飄逸、娟秀的字迹。這是她給粉絲的手寫信:
卿城已經16歲了。我願意把它想像成一個女孩,碧玉年華,亭亭似月。
它一定是堅定的,坦然地經風雨,見世面,兀自長大。最後祝它是健康的。
從一月開始就在錄制《朗讀者》第三季,嘔心瀝血,傾盡全力。有快樂,有悲傷,有懷疑,有相信。
寥寥數語,真情與坦誠躍然紙上,還有一些細微的幸福和感動。
很久不見,董卿還是那樣的淡然溫婉,恬靜優雅。
幾乎看不出來她背地裡到底付出了什麼。
實際上,她一年錄制一百三十多場節目,累到尾椎骨第四節骨裂,仍咬着牙完成。累到生理期紊亂,臉上冒出無數痘痘,還是不放棄。
為了節目錄制,常年熬大夜,從機房走出來,外面天光正亮,背後是連續奮戰了十幾個小時的黑漆漆的夜,她仿佛覺得自己做了一夜的孤魂野鬼。
沒錯,董卿就是這樣一路從泥濘中,掙紮着站上了萬衆矚目的舞台。
苦味童年
出生于70年代的董卿,童年過得并不愉快。
父母畢業于複旦大學,但工作在安徽。董卿在上海出生後跟着外婆長到了7歲,該上小學時,才回到父母身邊。
父親對董卿管教嚴厲,規定她每天都要背古詩,抄古文。還要每天清早去外面的操場跑步,不管刮風下雨,一天都不能落下。
樓下就是某所中學的操場,她一個人在400米的操場上跑着,那些晨練的學生們已經整理好隊伍了,隻有她孤零零的一個人跑着,感覺特傻。
(董卿和父母)
就這樣不情願又默默地跑完兩圈半,回家給父親交差。有時實在覺得難受,她也會偷偷躲在樓梯口,等時間到了再裝着氣喘籲籲的樣子跑回去。
回到家,一家人坐在桌上開始吃飯,自然又是少不了的批評和嚴厲,幾乎每一頓飯,父親總要說許許多多看不慣她的事。
“你那裡又做錯了,這裡沒有做好。”大多數情況下,董卿很少跟父親争辯,就算感到委屈,也隻是一邊含着淚,一邊扒飯。
更讓她覺得難過的是,連多照一下鏡子也不行。隻要看見她在照鏡子,那句“馬鈴薯再打扮也是土豆”一定會在耳邊響起。有時母親想給她買塊布做新衣服,父親也不同意,竟然把母親的衣服改改就行。
這讓從小就熱愛文藝,喜歡唱跳的董卿一度非常讨厭父親,最開心的日子就是父親出差了,可以高高興興地過幾天。
在父親的信條裡,勤儉吃苦、克己嚴厲是本分,他希望董卿也是這樣。
所以從高中開始,在報社當副總編的父親就會給認識的朋友打電話,“放暑假了,我女兒來給你免費幹活,行不行?”
對方覺得不給錢很不好意思,最後就約定每天一塊錢,兩個月給60塊。
高一那年暑假,在一家三星級賓館,15歲的董卿開始了清潔員生涯,她分到了10個房間的任務。
擡起床墊、鋪床單、四個角認真地包規整,套好被子,一套流程下來,她已經累得汗水大顆大顆地落下來。
幹完這些,還要擦馬桶,擦浴缸,她就跪在地上洗。一轉頭旁邊還有指導的老師,特意說,你爸剛才打電話來讓對你嚴厲一點。
一個上午過去,别人都幹完活兒在吃飯了,董卿才做完兩間房。她有些手足無措,想哭,卻又隻能拼命忍着。
後來到了下午,父親來看她幹得怎樣,董卿看見父親哇地一聲就哭起來,
我幹不了,太累了。
父親難得地摸了摸她的頭,“再堅持一下。”然後又走了。董卿看着父親的背影,心裡有種說不出來的難過。
在那些幹售貨員、服務員、播音員等活兒的時候,她一度懷疑父親是不愛自己的。
這種不夠被疼惜,和極度高壓的童年,注定了董卿内心是缺乏安全感的。
多年後,她回憶這一段日子,給了一個“苦”的标簽。
又辣又澀
高中畢業,董卿考上了浙江藝術學校的表演大專班,強硬的父親也拗不過。
畢業後,董卿被分配到浙江話劇團工作,僅僅過了半年,她就發現自己并不喜歡這裡,剛好浙江電視台招聘主持人,她很幸運地被錄取了。
這帶給董卿前所未有的滿足感,每天上班走上電視台的四層樓,幾乎就是蹦蹦跳跳的,她覺得很興奮,做電視是多麼時髦又高級的一件事。
錄制的第一個節目叫《人世風情》,原本什麼都不會的董卿學寫文字,做編導,後期錄像和制作等等,什麼都幹。
兩年的青澀時光,讓董卿從學生慢慢轉變為真正的主持人,她出乎意料地表現得很不錯。
此後,又在父親的建議下考到上海衛視當主持人。
那段時間,對董卿來說是難得的緩慢平實,她把大部分的光陰都用在了學習上,先後在上海戲劇學院攻讀電視編導的本科,和藝術專業的碩士。
不喜歡空閑,也從來不敢自己停。董卿從一開始就對自己有要求。
她沒想過自己能做成什麼樣,但首先一定要做,還要做到最好。
離家近了,長大後的董卿跟父親的相處也慢慢變了。
曾經很強勢的父親一反常态地溫和起來,把她叫到飯館去吃飯,斟滿一杯酒,對她說,“現在想來以前有很多不對的地方,希望你不要怨恨。”
董卿一下子就紅了眼眶,她開始理解父親的用心良苦,隻是那些深紮于心的刺,那種被揮鞭子的感覺好像一直在。
所以,當央視的邀請到來時,她幾乎沒怎麼猶豫就同意了,雖然内心實在很忐忑。
我隻知道我放棄了什麼,但我根本不知道,我将會得到什麼。
29歲已近而立,要放棄現有的安穩和優渥,到一個新的地方從零開始。
董卿不是怕,而是覺得這種落差有點酸。
特别是當她進不去心心念念的央視大樓,隻是在大興一個很偏遠的地方錄制節目,身邊也沒有一個幫手。
每天要自己扛着大包小包的東西去,在演播室連續奮戰十幾個小時後,走在深夜的北京街頭,空氣很涼,她默默地裹緊了單薄的衣服,低着頭,匆匆往住處趕。
有時真的很想拎着箱子立刻就回去,但隻能逼自己不要想太多。
空蕩蕩地租來的房子,蒙着灰塵的家具和箱子,想回家的沖動,想堅持下去的毅力,一直在董卿心裡糾纏着。
為了更快站穩腳跟,她拼命地做節目,一年錄制130場。忙到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生理期紊亂,臉上長出無數痘痘。
但這種苦和累,董卿并不覺得難,她曾說,“我的一切都圍繞着工作。”
她喜歡被掌控的生活,喜歡不斷向前,持續成長的痛感。
一步一進
慢慢地,董卿在央視的西部頻道站穩了腳跟。
她主持的《魅力12》風格清新,簡潔明麗。
有一天她坐出租車,司機笑着問,“你就是西部頻道《魅力12》的那個主持人嗎,那個節目挺好的。”董卿瞬間感動莫名。
再後來,她被調到央視3台擔任娛樂節目的主持人。《歡樂中國行》和那一年的青歌賽上,
董卿都表現不錯。
記憶最深刻的是,2007年的《歡樂中國行》元旦特别節目,董卿的端莊大氣,和沉穩優雅讓人難以忘懷。
當天活動接近零點,突然出現了兩分半鐘的空檔,隻見主持人董卿款款走上舞台,淺金色禮服光彩奪目,全場人目光緊緊跟随她。
在萬衆的熱情期待下,董卿用不疾不徐的語言一邊感謝,一邊回顧。
突然耳麥裡導播說,時間誤判,隻有一分半鐘。董卿依然面帶微笑,立即調整語序。但馬上得知,時間還是兩分半。
導播語氣急切慌亂,而台上的董卿對觀衆微微一笑,走到舞台中央,彎下腰深深鞠了兩躬。最後跟随着她的節奏,大家準時迎來了新年。
這一幕被稱為“金色三分鐘”,也是董卿第一次展現出極緻的主持功底。
這時距離她來到央視不過短短5年,剛好主持了2次春晚。從一個外鄉人,慢慢成了台柱子。
實際上這一路有多困難,董卿鮮少提及。
她說得更多的都是自己面對榮譽時的喜悅。
2005年第一次接到春晚邀請的那個深夜,董卿剛搬新家,正在灰頭土臉地打掃衛生,突然接到了春晚總導演郎昆的電話。她高興莫名,拿着掃帚就在那裡瘋狂地轉圈。
她沒想到春晚這麼大型的晚會,自己剛來3年就能有機會上去。
但她同時也明白,這個舞台不會永遠屬于她自己。
她一直記得前輩倪萍對她說的:
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站上這個萬衆矚目的舞台,你一定要做到最好。
所以,她不喜歡隻做一個沒有思想的主持人。每一次節目的台本,她會認認真真全背下來,哪怕有十頁紙,也要一字不差地背完。
一旦上台後,她不會完全按照台本來說。她喜歡觀察,喜歡用自己的思維去判斷什麼東西是台本沒有預見的内容,那這就她需要表達出來。
“我會把隻按照台本說,看成是我的一種失職。”說這話時,董卿特别認真。
剛到央視的時候,她更關注自己穿哪件衣服好看,怎麼才能把頭發弄更好一些,一定要比别人更瘦,更白才好。
但後來,她慢慢明白在中央台,一舉一動都會被無限放大,隻要是用心準備的東西,就會得到超乎想象的成績。
不管交給我什麼,我都能夠百分之百地超出導演的想象去完成。我并不覺得有比别人更強的地方,但是你隻要把這個事情交給我,我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
這種渴望被認可,被看見的背後,是“像阿甘那樣的傻勁”。
困與掙紮
2012年,來到央視十年的董卿有些乏了。
那會她連續主持了十幾場《我要上春晚》,雖然一切看起來很平靜,沒有絲毫破綻。但董卿自己非常清楚,明明還可以做到更好,很多采訪都不夠入心。
她敏銳地感到,自己失去了最初的激情, 就隻是按部就班地幹着,像一台機器那樣。
這種感覺是她很不喜歡。
從節目裡下來,她一個人坐在家裡沙發旁邊的地上,回味反思着,哪一句話說錯了,如果換一個種方式問應該會更好,還有當時為什麼沒有這樣接話……
做錯了、做得不好,對自己懊惱和不滿,一遍遍在她心裡揪着。
此後兩年,這種獨自救贖,在董卿的生命裡多次發生。
雖然得了很多獎項,是全國的知名主持人,但她想要的絕不僅僅是這些。
工作沒填滿的時候,她很孤獨,可一旦被填得太滿,像個陀螺式地轉動了十年後,那種内心的恐慌和無助更讓她害怕。
擔心做不好失去現有的一切,但實際上有無數個聲音在告訴她,該停下來了。
後來,她去看了話劇《如夢之夢》,長達8個小時的表演,中間她獨自出去吃了一頓飯,回來又認真看完。
這種停頓讓她找到了一種别樣的感覺。
2014年,董卿終于下定決心放下一切外出求學。
隻身在異國他鄉,她幾乎不化妝,穿着最簡單的牛仔褲和白襯衣,手機裡隻有菜譜和英漢詞典兩個界面,每天拎一個書包就去上課。
那種平靜孤單的日子,幫助董卿重新吸取營養,一點點填滿曾經的空乏。
她不參加聚會,不論在哪裡,董卿最不喜歡交際。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采訪過央視跟董卿密切接觸的人,他們都共同表示,很少看到董卿有放松的一面,比如跟大家一起唱歌、吃飯、聚會這樣的事幾乎找不到。
白岩松想了很久認真地回答,沒有。
倪萍很直接地給出答案,“董卿這個人,從不浪費時間說閑事。”
看起來永遠“精準高效、超長待機”的董卿沒有壓力嗎?不是的。她隻是習慣了奔跑,習慣了永遠要做到最好。
《朗讀者》有一期片花,需要一個董卿爬長城的畫面。
鏡頭離得很遠,也很小。團隊建議完全可以用替身,或是走很小一段就行。
但董卿不肯,她不斷地爬,哪怕頭頂烈日,也堅持用一個小時爬完了整一段長城,下山之後,她沒顧得上弄汗濕的衣服,幾乎立即開始了工作。
董卿後來對記者講了一個故事,張藝謀有一天偶遇同學在雪地裡瘋狂地走,他很奇怪問對方是不是有病。同學淡淡地告訴他,這是在磨練自己的意志。
從台前到台後的華麗轉身,實際上是董卿内心世界與現實的抗衡。
就像她說的,人生有六個字,前面三個是“不害怕”,後面還有三個“不後悔”。
外強内弱
2015年,董卿正在異國學習,很意外接到了導演哈文的電話,邀請她回來主持春晚。
這一刻,她是高興的。
能再次被需要,她覺得這是一種幸福。回到久違的舞台,璀璨的燈光點燃了她久違的激情。
隻要我一走進演播室,當燈光亮起來,一霎那間我就投入進去了,我喜歡站在台上的感覺。
就這樣《朗讀者》從多年的醞釀中,慢慢浮現出來,董卿也下定決心做制作人。
真正要操作,才發現内心是極沒有底氣的,不僅審核流程複雜,拉贊助和投資商更是困難。幾個月前早已跟嘉賓約好,但前期的各項工作一直沒法落實。
錄制第一期,留給董卿和團隊的時間隻有2個多月。要搭建攝影棚,要敲定各項方案細節,又也馬上快過年了。
團隊直接說,我們不可能一個月搭出來一個攝影棚,因為物品沒法齊備。
那你們需要什麼?我能怎麼做?跟你一起去建材市場也可以。
後來,采購團隊拿來一整間房子的物品,董卿跪在地上,一個個地挑選。
其實這些都不算什麼,最難的是,她在後期制作上的高要求。
為了選一張落日餘晖的圖片,她盯着圖庫一直選一直看,用了将近一個小時,隻為挑選最符合意境的圖片。
隻要董卿走進機房,團隊都知道,十幾個小時的工作開始了。她偶爾看看手表,哦,深夜十二點,該吃飯了。吃完又埋頭幹,直到所有工作完成。
有一期節目,在兩天一夜的不斷修改下,“完美版本”幾乎已經定稿。所有人都長舒了一口氣,準備收攤。
董卿突然停止不動,叫了暫停,又反複觀看,最後決定有個4秒的鏡頭不好,要重做。這意味着又要在龐大的數據裡找資料,讨論,修改。
導演劉欣說,“習慣了,在那個時候,人都麻木了,懵了。”
相比較董卿的完美主義情結,她的強勢似乎更讓團隊害怕。
(董卿在工作中)
有一次采訪數學家丘成桐,因某些技術問題一直做不到提詞器和語音同時出現,隻能不斷嘗試,董卿看見後,一下子就火了,她覺得這樣做很耽誤嘉賓的時間,團隊就不應該犯這樣的錯。
一個跟了她多年的夥伴覺得,董卿就是硬币的兩面。
工作時候像“機器”一樣,固執而堅硬,似乎永遠不會累。
上到台上,面對嘉賓,她卻超級敏感細膩,不僅端莊優雅,任何一句情感濃烈的話都能讓她瞬間淚流滿面。
“我是一個愛哭的人”董卿自己承認過。
這是她的一個“缺口”,也仿佛是她跟觀衆、跟團隊更親近的原因。
有人說“董卿在節目裡如果掉眼淚,特别打動人,時候把握得特别好,你也想跟着哭。”
對董卿來說,現在的她很少落淚。
哪怕工作再高壓,她也可以做到冷靜而克制,好像多年前,她剛到北京時,在會議上當着衆人面掉淚的事,早已換了一個人。
我永遠都沒有長大,但我永遠都沒有停止生長。
這句話來自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董卿一直拿來當座右銘。
行在心中
最近,《朗讀者》第三季正在錄制。
最有意義的是“一平方米” 朗讀亭吸引了很多普通人,隻要你願意,任何人都可以走進去讀。在裡面暢所欲言,說出自己的故事,表達你的困惑與迷茫,隻要是獨一無二的就好。
另一個項目“一萬公裡”則聚焦更廣袤的大地,探聽更多的聲音。
而董卿一直在忙碌,從北京、武漢、廈門到成都。4月23日,她在合肥發起了一場朗讀接力直播活動。
依然是翩跹的身影,利落的短發,優雅自信的笑容。
如果她不說,沒有誰能想到,如此精緻美麗、知性從容的董卿有過那樣的困苦與掙紮。
也沒有誰知道,一幕幕經典完美的畫面,是她一幀一幀摳出來的。
更沒有誰知道,她曾無數次獨自面對台上的璀璨,下台後的落寞與冷清。
那些巨大的反差,或許就是一個人最真實的樣子。
也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樣,有拼盡全力的敢,有咬牙落淚的痛,還有自我成全。
一切恰如董卿的那句話,
但即便不能擁有完美的生活,所幸依然在追求完整的自我。
-end-
作者:梁小小
參考資料:
1.南方人物周刊《董卿 我特别舍得把自己給出去 | 封面人物》
2.人物《董卿 慣性奔跑》
3.十點人物志《董卿 | 45歲怎麼了?》
4.人民文學出版社《董卿:沒有主持春晚,其實挺意外的》
5.央視《面對面專訪董卿》
6.BTV專訪董卿
7.南方周末《董卿:不想這樣來博取關注》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