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10月号的《人民文學》打破了創刊近60年的記錄,刊載了麥家的長篇小說《風聲》。
這是一次破天荒的文學事件。首刊後不久,《風聲》推出單行本,麥家憑借這部小說榮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二零零七年度小說家”稱号——這一年,或可稱為“《風聲》元年”。
2009年3月,小說改編而成的話劇《風聲》上演,同名電影(由高群書、陳國富聯合執導)于建國60周年前夕上映,與當年的國慶“獻禮片”《建國大業》一道彙入了“國家主義叙事”的大流。
迄今為止,《風聲》仍是觀衆津津樂道的諜戰片“神作”。麥家“中國諜戰文學之父”的名号由此坐實,無人可撼動。

《風聲》電影

《風聲》原著
如果把《人生海海》(2019年)視為麥家的文學轉型,那麼2007年橫空出世的《風聲》無疑是一座不可繞過的高峰。
然而長期以來,影視劇過盛的名氣遮蔽了小說原有的光芒,以至于人們常常忘了,電影是小說《風聲》的伴生物,沒有小說打底,電影的風行幾無可能。
01 “誰是老鬼”?
麥家曾言:“如果說《解密》和《暗算》側重的是‘人的命運’,《風聲》則側重于‘事的命運’。”
如何理解這句話?作為“解密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風聲》延續了麥家一貫的小說做法——将人置于嚴酷的極端環境中,以此考驗人性、拷問曆史。
以小說作試金石,對善與惡、真與假、忠誠與背叛等主題加以追問和辨認,是麥家小說的旨趣。
從這一層面來講,《風聲》與《解密》《暗算》一樣,都與“解密”、情報有關,屬于不折不扣的“特情”小說(或如其他評論者所言,是“新智力小說”)。
不過在前兩部小說裡,麥家寫了孤獨的天才,塑造了諸如容金珍、黃依依等個性鮮明的“經典”形象。
但在《風聲》中,人物雖置于聚光燈下,卻顯然退居一隅,坍縮為曆史深處的影子,人身處在“事”的漩渦内無力轉圜,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此為“事的命運”。

那麼,《風聲》講了什麼樣的“事”?怎樣的“事”擁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值得一再講述,進而被無數讀者所癡迷和傳頌?
自2007年首次面世以來,《風聲》有過多個版本(譯本也于2020年3月由素有“英國最佳獨立出版社”之稱的“宙斯之首”(Head of Zeus)推出)。
2013年,《風聲》二次修訂,2020年,麥家又作了第三次修訂——足見作家對小說的喜愛。《人民文學》版分為“上部”“下部”和“外部”,每一部都有“前言”;
直到“讀客版”,“上部”的“前言”已移到結尾變成“後記”。盡管内容不變——交代《風聲》的故事來源,用麥家的話說,“講的就是‘風聲’是怎麼‘吹’來的。
但這一調整非同小可,按照時間順序、最大限度還原故事,使得讀者甫一打開小說就紮進了風聲鶴唳的1941年。而叙述者則藏身其後,等到“上部”結束,他才開口說話,露出臉來。小說積蓄的叙事力量借此迸發,力拔千鈞,攝人心魄。

如此叙事魔力,顯然得益于小說所講述的那個無法被耗費和磨損的“原型故事”。讀過原著或看過電影《風聲》的人,應該很熟悉“誰是老鬼”這句話。
這是《風聲》的題眼和懸念,也是小說叙事賴以運轉的樞紐,它如同黑洞,将讀者注意力吞沒其中:
1941年的日僞時期,春夏之交,西子湖畔一座名為裘莊的别墅裡,囚禁着五位汪僞政府的軍事要員(吳志國、金生火、李甯玉、白小年、顧小夢),他們之中潛伏者共産黨的卧底(代号“老鬼”)。
由于一封共産黨聯合行動的密電被南京僞政府方面截取,困于裘莊的“老鬼”必須将情報送出,小說在此形成了多方力量的博弈和角逐:
老鬼要在密不透風且遭到監控的裘莊裡突破防線,以肥原龍川(日軍特務二課機關長)為首的敵人要在早已成為甕中之鼈的“嫌疑人”(“吳金李顧”四人)裡揪出老鬼,破壞共産黨的聯合行動。
于是,一出疑窦叢生的“羅生門”上演了。

“誰是老鬼”成了斯芬克斯之謎,也成為懸在“吳金李顧”四人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旦謎底揭開,是生是死便昭然天下。
為了顧大局、保自我,所有人對所有人懷疑,所有人與所有人博弈,明與暗、敵和我、強與弱,鬥智鬥勇,機關算盡。李甯玉為了自證清白,最後服毒自殺,送了性命。
上述即是上部《東風》的内容。到此為止,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浮出水面。這樣的故事,僅僅掀開一角就足夠吊人胃口,更何況《東風》不過是故事的“陽面”之一。
《東風》既定,下部《西風》襲來,最後止于外部《靜風》。可以說,經由三個獨立而環環相扣的聲部,《風聲》完成了一組瘋狂、精巧的“重複”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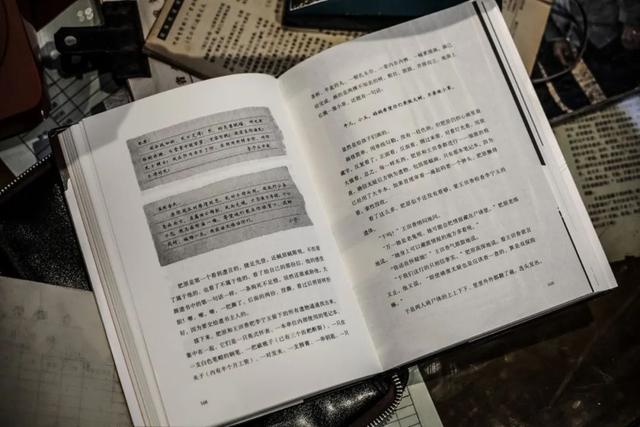
但此處的重複并非換種方式将故事重講一遍那麼簡單,它遵循一種“否定的辯證法”——“下部”颠覆“上部”的真相,又通過“外部”解構前兩部确立起來的叙事權威,從而将真相與虛構、曆史和小說的邊界徹底攪動。
麥家為什麼非得這般苦心孤詣,不老老實實地講故事呢?
聰明的讀者大概猜到了。這般講故事的好處是,它讓原本塵封的“事”随叙事的推進發生突轉,讀者的心理預期在被滿足的同時即遭瓦解。
因此,讀《風聲》的過程如同剝洋蔥,一層又一層——或者換種說法,《風聲》調用了“俄羅斯套娃”式的小說結構法,将秘密裹在最裡層。不讀到最後,休想知道故事的真相。
02 《風聲》的“密室逃脫”術
對讀者而言,打開《風聲》不僅是解讀“謎題”,同時還意味着投身一場叙事冒險。閱讀《風聲》的過程,如同“行走在地獄的屋頂”(語出日本俳句詩人小林一茶)。
繁花在側,但你無暇顧及,哪怕凝視一眼,都足以失足墜落,得不償失。
為了制造這樣的叙事效果,麥家像魔術師那樣“偷天換日”,将空間(裘莊)内發生的故事,轉化為一場與時間賽跑的追逐之旅。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這是典型的“密室逃脫”模式:在規定時限内破解謎題,找到出路;否則遊戲終結,等待你的唯有失敗。
營造密室、密閉空間是麥家寫小說的拿手好戲。
從《解密》到《暗算》的“701”,到《風聲》的裘莊,無不如此,但裘莊顯然承載着迥異于“701”(國家安全部門)的意義,
前者是單一空間,是我方活動的場所,小說所叙述的故事也大多發生于此。

然而裘莊不同,它曆經軍閥混戰和抗戰、國共兩黨對峙的時期,成為曆史的見證者。裘莊築有東樓與西樓,更是敵我雙方明争暗鬥的所在。
肥原在囚禁“老鬼”的西樓裡安裝了竊聽器,将一高一低兩座樓貫通起來。這樣的設置,無疑将讀者的神經末梢送至故事内部。
“竊聽”搖身一變,成為一種經濟有效的叙事手段(這從文本多次“轉錄”西樓裡人物的對話可以看出來)。
由于涉及國共日僞四方的利益沖突,裘莊裡發生的一切關系着民族抗戰的大曆史——這樣的寫法,在老舍的《四世同堂》裡也曾有過。
隻不過同樣是表現抗戰,《四世同堂》的“小羊圈胡同”對應的是北平的日常生活(小說充滿了大量的飲食起居的細節),而在《風聲》中,我們感受到的隻有恐怖、猜忌和死亡的威脅,私人的日常生活幾乎消匿不見。
這也是《風聲》有别于1940年代抗戰題材小說之處。在這裡,裘莊被建構為一個高度壓縮的“人性劇場”,其中上演的一切,無不叫人想起薩特存在主義的“境遇劇”,以及那句著名的“他人即地獄”。

因此,裘莊也是“囚莊”,人囚困其中,面對的是民族大義和善惡對壘,人心難測,真假混淆,小說因此生出了極大的叙事張力。
換言之,通過小叙事(小說)和大叙事(曆史)的同構,《風聲》營造出遠較故事的懸念更為深刻的心理懸念、曆史懸念。
靜态空間中的“事”(找出“老鬼”),在規定的時間(四天後)裡壓縮成一個博爾赫斯式的迷宮,讀者邁入其中,除了一再迷路,别無他法。
《風聲》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小說家對人物心理的精準揣摩,以及對人行為動機的合理鋪排。在《東風》裡,肥原為了揪出“老鬼”,先是用驗筆迹的方式,使出離間計。
西樓裡被懷疑的對象,依次是吳志國、李甯玉、白秘書和顧小夢。吳志國拒不承認自己是“老鬼”,最後被動了刑,而李甯玉也一口咬定吳志國才是老鬼;顧小夢為了洗脫嫌疑,又将矛頭指向白小年。

這無疑是“羅生門”的翻版。《東風》呈現給讀者的便是這樣一個人與人相互懷疑、指正又互相駁斥的對弈過程。
到了第八章,小說篇幅過半,但故事裡才過了三天。這場高密度的叙事試驗,以極快的叙述節奏容納極大的叙事能量。可以說,保持這種“既快又密”的叙事節奏殊為不易。
肥原為了揪出老鬼,先是讓吳志國假死,以其血書引蛇出洞,眼見這一手段失效,又将“死去”的吳志國“複活”。
如此一來,打破的平衡再次恢複了——五個人始終還是五個人,一個也沒有少,然而在人物沒有變動的情況下,他們各自的心理狀态已經悄然發生了轉換。這種轉換如此劇烈,以至于讀者必須稍作停歇,才能适應這樣的“翻轉”。
03 故事的第三重真相
到了上部《東風》的第十章裡,叙述人、故事的記錄人“我”正式登場。我們由此進入故事的第二重真相:李甯玉與哥哥為了打入敵人内部,假扮夫妻掩人耳目。
李甯玉死後多年,其兄長“潘老”向“我”袒露真相,李甯玉就是老鬼,情報是她以性命送出去的——她在自殺前了一幅畫,畫作上的小草藏了一副莫爾斯密碼。
莫爾斯密碼對故事的推動起到關鍵作用,莫爾斯密碼是一套符号轉換系統,實際上,麥家的小說也是對曆史和民族記憶的一次虛構和轉換。李甯玉為了發送這份電報,付出了年輕寶貴的生命。

“誰是老鬼”在《東風》的結尾得到了确鑿無疑的解答。然而,這不過是這部小說的冰山一角。因為故事還有第三重真相,這一真相藏在《西風》裡:
裘莊事件之後,顧小夢和特務處長王田香回歸部隊,張司令、金生水、白秘書、張參謀(胖參謀)等人均下落不明。
時隔半個世紀,顧小夢陰差陽錯地看了“我”的小說手稿,為了澄清事實,年邁的“顧老”(顧小夢)與“我”進行了一場漫長的對話,訴說起那段被掩蓋的曆史真相。
借顧老之口,小說在這一部分被重講了一遍,曆史與小說、真實與虛構的邊界再次打破。

如果說上部《東風》是“立”,那麼下部《西風》是“破”,“外部”則為“補”,
“立”的意義在于打撈曆史(盡管隻是表層故事),
“破”旨在将被記錄在案的曆史假面戳破,正本清源,為淹沒在時間中的個體發聲;
“補”的意圖在于把故事從曆史深處拉到現實層面,一方面交代作者的寫作緣由,也借此補叙所有與裘莊有關的人物的命運。
這已經超出了“故事”部分,而具有鮮明的元小說特征了。
正如麥家所言:“我寫《風聲》小說,從故事層面上說設計的就是一個驚險的逃逸魔術,但從意義上說,我想通過‘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個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個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種驚心動魄的心智較量中,為人性那無法度量的邊界下一個‘我’的注腳。”
《西風》出現了兩個叙述人,一個是那段慘烈曆史的見證者顧老,一個是傾聽者、記錄者和轉述者“我”,二人構成“聽—說”的關系,帶領讀者再次穿越時間的迷霧,走進曆史深處。
此外,小說中的“老鬼”在這部小說中一直是以“隐身”的方式呈現的。
也就是說,上部《東風》在叙及老鬼時,用的是不辨性别的“Ta”,小說以第三人稱的限制性視角,為讀者将自我替換到老鬼的角色中提供了便利,也令讀者對身處絕境中的老鬼産生共情。
即便在後來人的講述中,李甯玉也是一個傳奇、一個幽靈般的人物,然而正是這個早已殒命的“老鬼”,引發了《風聲》。
某種程度上說,《風聲》是以虛構的方式為李甯玉招魂,替無數為革命灑熱血、抛頭顱的能人志士立傳。
如果說麥家《風聲》在叙事結構上借鑒了博爾赫斯的迷宮,那麼這個迷宮早已舊貌換新顔,因為在《風聲》中,迷宮是立體的、翻轉的,甚至可以拆解拼接、重新組裝的。
麥家當然無意于叙事遊戲,他将“個人”的聲音置入曆史深處,借此将叙事變作對曆史發問的載體,小說也因此被賦予了深厚的意涵,獲得了遠超故事之外的文學價值。
文丨林培源

本文為單讀友情互推,内容由賣書狂魔熊貓君提供。

,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