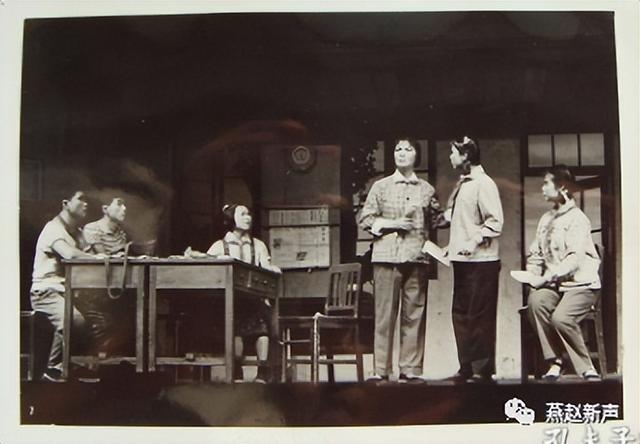衆所周知,電視劇《西遊記》裡的唐僧一角,有三位扮演者:汪粵、徐少華和遲重瑞。
年輕時,三位都是翩翩美少年;歲月流逝後,三位“唐僧”的命運卻迥然不同。

從氣質看,汪粵更有英氣,徐少華更有貴氣,遲重瑞最有靜氣。
汪粵似乎是存在感最低的那位,可他又是最早被确定的三藏扮演者。

觀衆後來看到的《西遊記》,當年是一邊播放一邊拍攝的。現在電視上跟觀衆見面的是徐少華,但汪粵确實是楊潔導演第一眼相中的“唐僧”,并率先拍攝了《禍起觀音院》、《偷吃人參果》、《三打白骨精》這三集。
上世紀80、90年代的小觀衆,有很多是被《三打白骨精》裡那個決絕的唐僧給氣哭的。悟空苦求無效,長老憤然貶徒。現在想來,唐長老曆經九九八十一難才取到真經,其性格中不能缺少堅毅和勇敢,絕不可能僅靠綿軟完成這宏偉的使命。
三打白骨精是唐僧師徒遇到的最大誤會和分裂,也隻有汪粵這樣的唐僧,才讓人相信玄奘那超乎常人的決心,以及堅決捍衛原則的強硬。這樣的氣質,是對佛法中“無畏”的最好闡釋。

用現在的話說,徐少華顔值最高,氣質最為高貴。也唯有這樣的雍容之氣,能讓人相信,唐太宗會欣然賜其“禦弟”之榮耀,讓其在漫漫取經路上,成為大唐王朝的“文化大使”。

錦斓袈裟、金檀缽盂、通關文牒,無不彰顯着唐僧這一角色的尊貴,也隻有徐少華這樣的唐僧,能與唐太宗共框而毫不違和,無論行走在魔域還是皇宮都泰然自若,并為俗世承擔至為莊重的使命。

也難怪,見到這樣的“禦弟”,女兒國國王願意以身相許,“你為國王我為王後”,電視劇《西遊記》最令人動情的“趣經女兒國”,有此唐三藏,才讓人唏噓。王權富貴與戒律清規的抉擇,在這樣的唐僧身上才最動人。

當然,最終到達靈山并取得真經的還是遲重瑞。三位唐僧扮演者中,最有佛相的就是他,氣質最脫俗的也是他。西天愈近,唐僧就越靜,整個取經路,仿佛讓一位堅毅的少僧承擔着尊貴的使命,最終修行為一個大師。

仔細想來,若電視劇裡各集裡唐僧的扮演者有些錯進錯出,仿佛都會略差一點意思。
電視劇已成為永恒的經典,但演員終究活在俗世中,那靈魂裡存在着的英氣、貴氣和靜氣,都需要再被生活洗禮一遍。
結合各種綜藝訪談,汪粵的命運似乎最為波折。據傳,他在西遊劇組拍戲的同時,接到了電影的片約,在當時電視劇拍攝節奏緩慢,讓汪粵希望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他向劇組申請兩個片約同時進行,“唐僧”分身分神,讓劇組覺得不妥。
汪粵自己的理解是,他是在兩個劇組裡拍戲,兩個都不耽誤。不過在楊潔的理解中,你這麼做的話,就等于是想要離開了。
汪粵最終失去了繼續拍攝西遊記的機會,那時的他還不能理解他到底失去了什麼。
當年一直想追逐更好的機會,卻不知不覺間錯過了最好的機會。這也像俗世中的大多數人的命運,總想目光如炬地尋找更多功成名就的機遇,卻常常迷失在萬變的世界中。
讓一個富含活力與勇氣的年輕人放棄對功名的追逐,是悖逆人性的。然而,很多無用功也從此而來,甚至離當初的目标越來越遠。諸行無常,也許是佛教對人最好的警醒。
說到徐少華,目前關于他最多的新聞就剩了“商場走秀”。


徐少華一直就職于山東省話劇院。因為工作原因,我曾經接觸過北方大省文化圈裡的很多事,跟很多人“就想考公務員”的第一印象一緻,迷戀權力始終是這裡的主流。有的文化領導每天午飯都要有人陪着吃,說好聽得下飯;有的領導堅持leader helps leader,卻忽悠有點才學的年輕人透支青春;很多學曆突出的人,初入宦海,遇到最多的批評就是“不看事”。我也見過,很多曾經意氣風發的少年,進入這個圈子幾十年,無不在其浸染中變得面目全非。在一輪又一輪的服從性測試、關系搭建、看不見的手的操盤以及兩面話術的洗禮下,持守者不得清淨、高傲者終将碰壁、迎合者人格矛盾。專業退化、人格同化、創造鈍化,是毫無疑問已經且正在發生的事情。
當身邊的女兒國國王變成縣城街頭的大媽,當《西遊記》片頭的仙歌被聒噪的音樂取代,禦弟哥哥失去的不僅是唐僧的形,還有其神。發腮、長皺隻是表象,即便是玄奘本人老去之後,也不會是這般煙火氣。

沒辦法,不隻是唐僧,很多英俊儒雅的小哥哥,進入這種生态系統一段時間,都會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發生形神之巨變,你的高貴氣質是這個生态不能容忍的。油膩者或許混得還不錯,焦躁者可能還在被打擊的路上。唯有領導才有擁有彰顯自己氣質的權力。
目前,遲重瑞出現在媒體上時,一定是站在陳麗華身邊的。

酒席上,王健林這樣的大佬對陳麗華畢恭畢敬,卻懶得跟遲重瑞說一句話。“唐僧”唯有笑臉相迎。

有人說,他的錢花不完,也有人說,那不是他的錢。
從一定程度上說,他可以觸摸到這個世界很多昂貴的物質,可以接觸到很多位高權重的大佬,但是,從電視劇《西遊記》之後,他屬于自己的社會角色幾乎消失了。
說起來很玄妙。三位“唐僧”中以氣質論,最無欲無求的那一位,好像一直活在“榮華富貴”這個氛圍中。不為稻粱謀,不為生計走。
男人在沒錢的時候,大多是很想成為他的;在男人稍稍獲得了一點财務上的自由的時候,很多人一琢磨,其實并不想成為他。
當然,這一切也可能有另一種解釋,那就是他獲得了真正的“大隐”與平靜。俗世中的俗務,他已徹底不再染指,甚至鮮對媒體發聲,他甚至不再需要與塵世互動。
在“俗物”包圍下徹底脫離“俗務”,也許是另一種人生境界。隻不過這一切我們都無從得知。現在還在為什麼是“西遊文化”而辯論不休的,為了大家不忘記電視劇《西遊記》而鬥戰不止的,還是他當年的徒弟孫悟空。

其實,原著《西遊記》中唐僧這一角色,比電視劇中要複雜得多。吳承恩筆下的唐僧,是一個見過最高權力的人,是一個飽嘗最多苦難的人,是一個被最多肮髒浸染的人,是一個參與驚天大交易的棋子,卻是一個無權做自己的,無力反抗的人。
英氣、貴氣和靜氣,都不足以支撐唐僧走完漫長的取經路。他需要修行到什麼程度,我們根本想象不到。三種氣質的“唐僧”,在命運跌宕之後,面目越發接近,也越發模糊,都像一個微胖老大叔了。殊途同歸,也許才是人生的本質。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