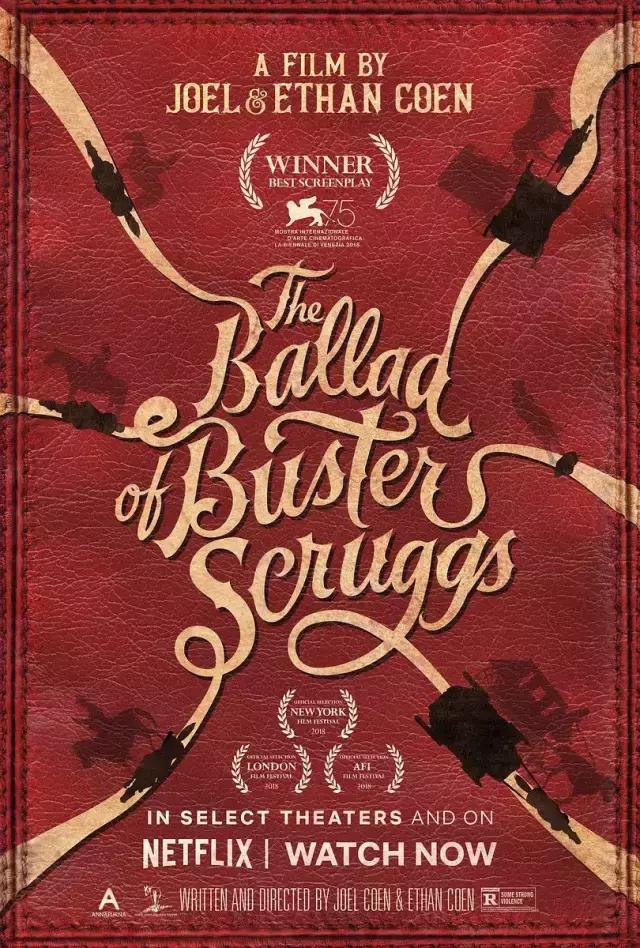山中少年今何在
閻世德

粘一個野字,總是貶多褒少。山中少年,野就野吧,野的時候,原本也沒指望别人的誇獎,山裡的孩子,不但不奢求别人的誇獎,最大的願望,僅僅是能免除了父親的皮鞭,母親的責罵足以喜笑顔開了。
少年,隻要生長在大山,隻要能走動,大山總是敞開了胸懷等着你。土蒼蒼的山,似乎比媽媽更有吸引力,孩子們撲進山裡,一點也不遜于撲進媽媽的懷裡。唯一的區别,在家是個乖寶寶,一進山裡,就是一群野孩子了。
往往的情景是:姐姐或者哥哥,帶了弟弟或者妹妹,背個小背篼,拿把小鏟子,手把手,呼朋喚友,成群結隊,嘻嘻哈哈鑽進山裡,像逃出牢籠的一群小獸。
草芽在地下蟄伏,殘雪在背陰處睡覺,但春天已在孩子們的心裡開放。看似一片片荒涼死寂的土地,下面已經千變萬化了。這種變化逃不過野孩子們的眼睛,生來就是山的孩子,自然感覺得到山野的變化。指頭粗細的野蘿蔔已經在地下瘋長,性急的,撐開地面,從裂縫中呼吸春天的氣息。孩子的鐵鏟毫不客氣插入裂縫,一撬,一根一乍長的野蘿蔔閃爍白生生的光澤,很不情願地躺在背篼或者筐筐裡。
當然,報複的任務隻能交個大人了。野孩子一回到家,乖的像綿羊。得勝的一方,不知道大難當頭。煤油燈下,父親的巴掌掄了過來,任你如何狡辯,隻有一個理由:打人不對,欺負歲數小的更不對。失敗的一方,仗着父母,幸災樂禍看着挨打的小夥伴挨打,總算找回了公道。正在得意時,父母的巴掌也落了下來:碎籽籽厲害的不行,你就不會讓着哥哥姐姐?又滿臉堆了笑,擋住扇下來的手掌:算了算了,教訓一下就行了,不是不能打仗,娃們手下沒個輕重,萬一一個把一個打壞了,可咋辦?于是大人們開始說說笑笑,仿佛因為小孩的糾紛,給了他們叙舊的機會。
第二天,野孩子們卻又手把手撲進山裡。也會發生類似的情況,但大的總會讓給小的,輕易不再出手。做人的道理,就此放在了心上。
野孩子隻快樂自己的快樂。挖來的野蘿蔔,被大人洗幹淨下鍋,下鍋後再倒進一些幹面粉,文火慢炖,差不多了,拿擀杖用勁攪拌,野蘿蔔已經稀爛,和面粉在攪拌下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有條件的,淋幾滴菜籽油,濃郁的香氣在屋裡翻滾,一種叫穹穹子的吃食就好了。野蘿蔔甜滋滋的味道,讓這道美食不僅可以果腹,又節省了糧食。
野蘿蔔的芽子一旦冒出地面,根須就老了,野孩子的眼睛卻亮了。一種叫辣辣的植物,頂了星星點點的綠,對着野孩子們擠眉弄眼。野孩子們一陣歡喜,舞了小鏟子撲過來,挖出一根根辣辣,弄幹淨土,放在嘴裡嚼得津津有味。辣辣有油筆芯般粗細,色白,微辣,脆爽,量大。一群野孩子,很像山野覓食的嘎哒雞,一坐就是大半天。
季節的腳步在邁動,轉眼間,到了響雷的季節,一響雷,辣辣就吃不成了,這時的辣辣不再叫辣辣了,而是成了聾辣辣,吃了,耳朵會聾的。也有膽大的,偏就不信,偷偷挖了吃,吃完耳朵也沒什麼異樣,才知道大人們的很多話都是哄人的。
知道也就知道了,成了大人的野孩子,對又一代的野孩子還是會照說不誤。說了也就說了,至于如何理解,全在野孩子的心裡。
天氣轉暖,土地像一床棉被,踩上去軟軟的,挖過野蘿蔔的地方,留下星星點點的印記,而孩子們背着背篼又瞄準了就要出土的苦苦菜,紅花郎。見風的芽子已經被風吹綠,一鏟子下去,一大把白生生的苦苦菜芽到了手裡,抖抖土,安心躺在背篼了,眼疾手快的,不多的功夫就能挖上很多。雖然苦苦菜長了葉子也能吃,但遠沒有芽子好吃。拿開水锊锊,切上幾刀,撒了細鹽,澆了醋,再用油炝一下,即便是沒有主食,一盤足矣果腹了。

也不僅僅是果腹。總有長大的野孩子會對後人說:不是像你們這樣吃個新鮮,那會,想法設法填飽肚子,是為了活命。
腦袋瓜靈光的後人會開個故作驚訝的玩笑:這命的質量高了去,全是純天然綠色無污染呀。
被開玩笑的長輩也憨憨地笑:靠山吃山,隻要有山在,總有人的活路。也說心裡的實話:這野味,怎麼吃都饞,到不同的時令,就想不同的野物。
一種食物,不同的烹制會有不同的味道,但總有一種味道,任你吃上千萬次,也難覺其一。野孩子吃苦苦菜也就是苦苦菜,已經老了的野孩子吃苦苦菜,卻在咀嚼苦苦菜之外的味道。
也是,一年四季依時更叠,一代代人各有各的生存。挖苦菜的野孩子不僅僅滿足于挖野菜,溝坂、向陽處,嫩黃的毛刺花開了,一串串,像豆角,所以不叫毛刺花而叫毛個個(角角)花,捋下一串,嚼的滿嘴生香,鮮甜得難以割舍。
當然了,也就是個野味兒,當不成主食來吃的,連着幾頓,或者吃多了,都不好受。不好受是不好受,但能活命。當然了,如今再去吃,可是真正的野味兒,嘗鮮,養生,但這個味兒已經不是原來那個味了。
出土的麥苗見風瘋長,很快揚穗吐花,一場雨水淋過,麥仁有了雛形。灌漿需要一個過程,野孩子們卻先下手了。找穗大實硬的麥穗揪了,回家大人們自有炮制的辦法。去了麥殼,從石磨眼裡進去,轉眼間索索條條的麥索子如水般流下來。盛碗裡,撒鹽到醋拌蒜泥,不由得小嘴巴不吧唧。
麥索子的味道似乎還挂在嘴邊,麥穗已經變得充實了,青糧食,家裡可以做,野孩子們自己也可以。放牛牧馬乃或者打豬草,抽空拾來幹柴枯草,點着了,将拔來的麥穗在火苗上緊着翻騰,一個個麥穗掉進灰燼,一股清香已經彌漫。撿了麥穗放手心,兩手搓幾把,用嘴吹去麥殼,一粒粒飽滿的麥粒閃着綠瑩瑩的光,迫不及待鑽進嘴裡,嚼出滿嘴的清香。這叫手心裡打場,嘴裡揚場。自己動手,吃飽肚子。
青黃不接,似乎是一個很遙遠的詞語,但以前的野孩子并不陌生。小時候對這個詞語的理解是大人臉上的愁雲,是見底的糧倉。再沒有人比他們更渴望春天的到來。長大了,才知道這個詞意味着生死關口。也是,隻要春天到來,就沒有活不下去的道理。難怪老人吃着野菜,唏噓不已:這是當年救了很多命的東西呀。
隻有經曆了才有的感歎,無礙野孩子們的快樂。隻要填飽了肚子,一切都充滿生機。轉眼到了夏末秋初,野孩子滿眼裡都是幸福。土豆撐開了地面,小手伸進去,長足的土豆随之離開土地,一趟走過去,背簍已經過半。早有其他夥伴找好土坎處,挖成竈的模樣,撿石塊的夥伴已經撿來許多不大不小的石塊,拾柴的把柴禾堆成個山。壘石塊、燒火是個技術活,操作者緊抿了小嘴,一臉的嚴肅認真。等燒紅了石塊,倒進土豆,一腳踏塌石壘子,任憑土豆在高溫下冒氣,緊着拿土密密封了,隻等着熟的時辰到來。
還有一種燒土豆的做法:挖一塊塊土疙瘩,壘起來燒紅了也能烤熟土豆,但野孩子們更青睐石塊。石塊溫度高,能給土豆包一層焦黃的外殼——土塊也能,但外殼沒有石塊的金黃、幹脆。不論怎樣,最終的結果是一個土豆有了兩種味道,兩種吃法:黃的嘎嘣脆,白的幹爽綿軟,似乎更有土豆的原味。
這個味,滲入了骨髓。
要老去的野孩子,留戀人世的最後一口氣落不下去,眼巴巴等着:能不給我燒個土豆?在外安家了的,彌留之際的願望竟然是:要是能喝上口山泉水就好了。
這個味,這個念想,走進了生命。一種吃食有一種吃食的味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記憶,但共有的永遠是這個味,永遠是無法忘記的鄉情。不管你走多遠,相同的記憶,相同的味道,總會在心底留下深深地印痕。
山中少年今何在,心願隻在此味中。

2017年4月29日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