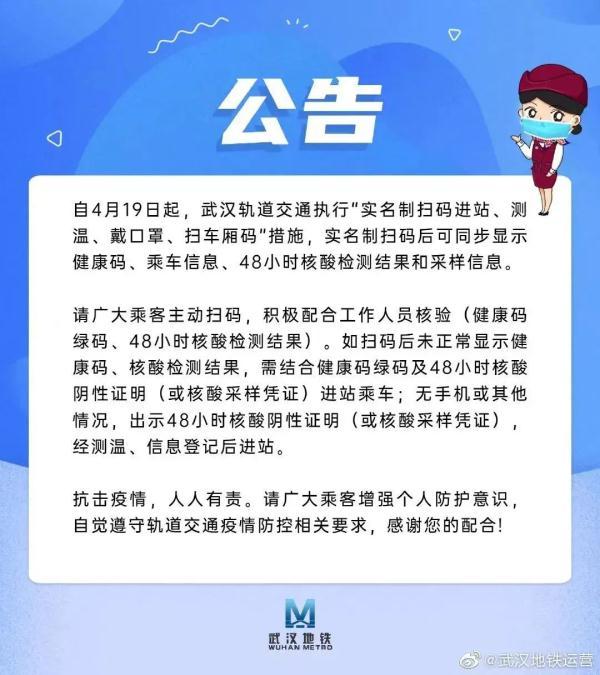門閥貴族的自律性和社會性,來源于鄉裡社會輿論即"鄉論"的支持。随着政治和社會形勢的變化,不同時期的"清議"或"鄉論"有不同的特質,當我們把目光聚焦在西晉元康(291-299年)時期的社會時,《抱樸子·刺驕》展示了這樣一幅畫面:
世人聞戴叔鸾(良)、阮嗣宗(籍)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濯腳於稠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為,非諸夏之快事也。
葛洪所描繪的,正是元康時期的"放達"之風。這種社會風氣的背後,無疑有強大的社會輿論也就是"鄉論"作為支撐。
竹林七賢
李濟滄先生對元康"放達"之風及其與"鄉論"的關系作了較為精細的讨論,指出"放達"之風所具有的反禮教的實質與漢末至竹林名士的思潮一脈相承,不同之處在于前者形成了覆蓋社會各個階層的社會風潮,并受到了廣泛的稱譽。由此,我們可以将支持"放達"之風作為元康時期的"鄉論"的特質,這是其與漢魏以來的"鄉裡清議"或"清議"及東晉南朝的"清議"或"鄉論"的本質區别。
居喪之情元康"鄉論"的這一特質,對理解魏晉南朝"清議"或"鄉論"的變遷大有幫助。進而,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這種特質是如何産生的?其實"放達"之風反禮教的實質展示了這種風氣與國家權力相對立的一面,因而其背後的"鄉論"也就和國家權力明顯地對立起來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鄉論"與國家權力間的對立不可能在朝夕之間形成,而是伴随着漢末反禮教的社會思潮向"放達"之風發展逐步彰顯的。這就是說,對立性之外,"鄉論"和國家權力間還具有某種微妙的一緻性。《世說新語·德行》中有一條耐人尋味的材料:
王戎、和峤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床,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峤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峤,而應憂戎。"
王戎是"竹林七賢"中的著名人物,其居喪一事亦見《晉書》本傳。在這裡,我們看到以晉武帝和劉毅為代表的國家權力對王戎、和峤的孝行均表示認可,而前者更傾向于和峤,後者更傾向于王戎;二人"俱以孝稱",表明他們同時也得到了社會輿論的認可。值得注意的是,和峤"哭泣備禮",居喪期間的言行舉止完全符合儒家禮制,受到稱贊固然屬于情理之中,但王戎的行為并不符合禮制,用裴頠的話說,就是"不免滅性之譏"。所謂"滅性"就是因喪廢事、以死傷生。因而,王、和二人之"孝"最根本的區别,在于王重"情"而和重"禮"。
當然,考慮到王戎其人素以吝啬聞名,因而他的"雞骨支床"也有故作姿态的可能。暫且不論王戎主觀上是否有沽名釣譽的嫌疑,其"哀毀骨立"的孝行的确得到了國家權力和社會輿論的認可。換言之,重"情"的孝道觀在這一時期是受到廣泛認可和稱贊的。這種重"情"的孝道觀實際上是儒學語境下"情"價值的凸顯。
衆所周知,魏晉是"人的自覺"或"人間的發現"的時期。因此,"情"價值的凸顯并不限于儒學語境,在玄學的浸染下,"情"得到了極大的張揚。王戎的行為,可以說正是玄風浸染的例子。
西晉
綜合上述例子,可以說魏晉南朝重"情"的社會觀念是儒學與玄風兩股思潮自覺或不自覺融合的結果。"情"價值的凸顯也就具有了雙重性的意義:從"玄"的一面看,"情"的凸顯具有反禮教的性質;從"儒"的一面看,"情"的凸顯相對于兩漢繁瑣嚴密的經學,具有儒學自我革新的意義,使得儒學價值從僵化的經學形态中解放,獲得了新的發展。因而,王戎等名士遭喪時的"任誕"行為,就不僅是儒學外部的受玄學影響而産生的反禮教行為,同時也具有"從儒學之外為儒家價值尋求根基"的意義。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情"的凸顯對元康"鄉論"的形成有何意義呢?對此《後漢書·逸民列傳》有言:
良少誕節,母憙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鸾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緻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
戴良居母喪中食肉飲酒,與禮制不符。他以"情苟不佚,何禮之論"為自己辯護,就是說,隻要自己對母親的孝心發自内心、出自天性,即使言行在表面上不符合禮,但卻沒有違背禮的内在精神,所以"論者不能奪之"。
戴良的言行,實則已開魏晉南朝重"情"之風的先河。需要注意的是,他的言行雖然産生了社會影響,"多駭流俗",但同時也就表明其還沒有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隻能說是"暗流"。這股"暗流"有兩個思想特質,一是強調儒學語境下的"情"的價值,并明顯地表現出對繁文缛節化的"禮"及其背後繁瑣僵化的經學的不滿;由此便衍生出第二個特質即與政府的不合作傾向,或者說,相對于國家權力的獨立性與社會性。
這樣的兩個思想特質,經由魏晉之際的玄學的浸染,在西晉時期門閥貴族勢力見長的社會背景下,成為了元康"鄉論"形成的思想基礎。
也就是說,不管是從儒學還是玄學的角度看,"情"價值的凸顯都和國家權力明顯對立。以重"情"為思想基礎的元康"鄉論",當然也就表現出了相對于國家權力的強烈對立性。這種強烈的對立性通過"鄉論"所支持的"放達"之風表現出來,與"放達"之風相映成趣。
君臣忠孝至此又浮現出了一個新問題:既然"情"的凸顯使得"鄉論"表現出相對于國家權力的強烈的對立性,以晉武帝和劉毅為代表的國家權力為何對王戎的"死孝"予以肯定,而二者的态度又有着微妙的差别呢?這就不能不把目光投向時人推重的"孝"或"孝道"上了。對于此時的孝道觀念,唐長孺先生有一個很精辟的論斷:
司馬氏是河内的儒學大族,其奪取政權卻與儒家的傳統道德不符,在"忠"的方面已無從談起,隻能提倡孝道以掩飾己身的行為,而孝道的提倡也正是所有的大族為了維護本身利益所必需的。
司馬氏作為西晉王朝的建立者,為了鞏固其統治而大力提倡孝道,而門閥貴族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标榜孝道。既然雙方基于利益需要都重視孝道,即"孝道"成為了雙方共同的話語框架。那麼此時,以皇權為中心的國家權力和以元康"貴遊子弟"也就是門閥貴族為主體的社會輿論即"鄉論"在這個共同話語框架之下,如何能達成某種微妙的一緻呢?
司馬懿和曹操
從王戎的例子可知,這種一緻确實存在。我們知道,這一時期對"孝道"的重視使得《孝經》地位崇高,因此有必要看看是否能在《孝經》中尋找到這種一緻性的根據。質言之,《孝經》是否提供了理論依據,使得皇權和門閥貴族在政治上能各自滿足利益需求而又保持平衡,從而為雙方共同推重呢?答案是肯定的。《孝經·聖治章》雲: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一部不長的《孝經》,可資利用之處甚多,這一句尤其值得注意。"父子之道"建立在以血緣為紐帶形成的父母子女間的人倫關系之上,故曰"天性";"父以尊嚴臨子,子以親愛事父,尊卑既陳,貴賤斯位,則子之事父,如臣之事君",便又将這種家庭内的人倫關系和尊卑貴賤的社會關系相結合,從而使"父子"間的"孝"這樣一種親情和宗法關系擴展為君臣之間的上下關系,就是所謂的"君臣之義"。也就是說,《孝經》所主張的"孝道"實際上包含了"忠"與"孝"兩項内容,這正是傳統儒家對"忠"和"孝"的關系的基本觀點,也是漢代統治者"移孝作忠"的理論根據所在。
三國鼎立
司馬氏建國,"在'忠'的方面已無從談起",隻能大力提倡"孝道",司馬氏大力提倡"孝道",其目的自然是維護"君臣之義";而門閥貴族标榜"孝道",自然不是為了強調"君臣之義"。這樣一來,"忠"和"孝"間的矛盾就被内在化于"孝"這一共同話語框架中。而對于門閥貴族的這種心态,南朝著名貴族、蕭齊宗室蕭子顯看得很清楚。他說:
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為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為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緻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
在蕭子顯筆下,門閥貴族和皇帝間沒有什麼"君臣之節"可言,即使江山改姓,他們依舊享有榮華富貴。和"殉國之感"對舉的"保家之念",實際上就是門閥貴族所标榜的"孝道"。可見,他們所謂的"孝道",實際上是強調其"天性"的一面,仍然是将家庭内的人倫關系和尊卑貴賤的社會關系相結合,但其指向不是君主或國家而是家族。這也就能說明,何以漢末魏晉的士人不少都有"至孝"的名聲了。
南齊短短23年換了7個皇帝
天性與孝道
門閥貴族标榜"孝道"是強調其"天性"的一面而降低了"君臣之義"在其中的價值,西晉以皇權為代表的國家權力提倡"孝道"目的在于強調"君臣之義",但在當時的情形下,皇權無法也不可能反對"天性"在"孝道"中的地位。《晉書·何曾傳》說:
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于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于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污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
文帝即司馬昭。其時雖仍在曹魏,但大權已落入司馬氏手中,因而此時的司馬氏就是皇權的代表。何曾以阮籍"居喪無禮"違背孝道為由,鼓動司馬昭懲罰阮籍。何曾其人,本傳說他"性至孝",前述漢末魏晉士人多有"至孝"的名聲,何曾便是絕佳的例子。
其所謂"至孝"自然是維護了家族利益,而在司馬昭面前極言"公方以孝治天下"固然是阿谀奉承,但也再次證明了"孝"确實成為國家權力和大族間共同的話語框架。司馬昭拒絕了何曾的建議,此處的"為吾忍"很值得玩味:"為吾忍"表明司馬昭實際上也對阮籍甚為不滿。
阮籍居喪期間雖然行為"放誕",但他"因吐血,廢頓良久"的表現被認為是合于"天性"的而受到贊揚,這也與"孝"地位擡升的趨勢相吻合。這麼一來,司馬昭倘若懲罰阮籍,便否定了"天性",實際也就是否定了"孝道"。這無異于自打耳光,也會觸犯門閥貴族的利益,是司馬昭無論如何都不願看到的,所以他隻能以阮籍"羸病若此"搪塞了事。
由此,我們看到,在西晉皇權與門閥貴族間的角力中,兩者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共同将"孝道"作為話語框架,各自表達的話語,側重點卻有所不同,前者重在"君臣之義",後者重在"天性"。同時,雙方都無法忽視的内容是"天性"。如此便解釋了以晉武帝和劉毅為代表的國家權力何以在對王戎與和峤二人的孝行的評價上與社會輿論達成一緻,在這種"一緻"中,可以看到"天性"的張揚。而晉武帝傾向于和峤,其意在于重"禮";劉毅傾向于王戎則反映了重"情"的思潮對國家權力的影響。"情"與"禮"間無疑存在着矛盾,但它和"忠"與"孝"間的矛盾一樣,被内在化于作為共同話語框架的"孝"中。
孔子說:"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 "三年之愛"實際上反映了人類共同的情感,"三年之喪"盡管在漢代有反複,但最終成為受到普遍承認的喪期。那麼,在服喪期間表現出的"情"就不僅僅是個人情感,而是承載着家庭内的基本倫理,并由此将家庭與社會聯結在一起。
在強調對"父母之喪"的真情流露上,"情"得到了"天性"的強力支持,得以貫通個人、家庭和社會,上至達官顯貴,下至販夫走卒,皆沉浸其中。這樣就說明了元康"鄉論"形成的強大社會基礎,也正是元康"放達"之風得以覆蓋社會各個階層的内在動力。
餘論綜上,我們在兩個層面上探讨了"鄉論"形成的原因:第一個層面又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儒學的内部變遷即在從"移孝作忠"到"先孝後忠"的曆史轉變中"情"的價值得到凸顯,二是儒學受到的外部影響即玄學的熏陶。第二個層面則是皇權與門閥貴族間的角力,兩者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共同将"孝道"作為話語框架,各自表達的話語,側重點卻有所不同,前者重在"君臣之義",後者重在"天性",二者于對立中又有統一性,關系微妙。這兩個層面的關聯點和最終的落腳點就在"天性"。
東晉
這樣一來,儒學與玄學和皇權與門閥貴族間對立統一的關系及這種關系下各自的自覺或不自覺的推動,共同促使了元康年間支持"放達"之風的覆蓋整個社會的社會輿論即"鄉論"的形成。東晉南朝"禮玄雙修"的局面使"禮"在漢末喪亂後重新樹立了對"情"的規範作用,使其身上的"禮法豈為我輩而設"的色彩減弱,并以合于儒家倫理的形式表現出來。在東晉南朝人的實際生活中,"緣情制禮"常常表現為為了突出"情"而極盡"禮"之要求,甚至達到比較極端的地步。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