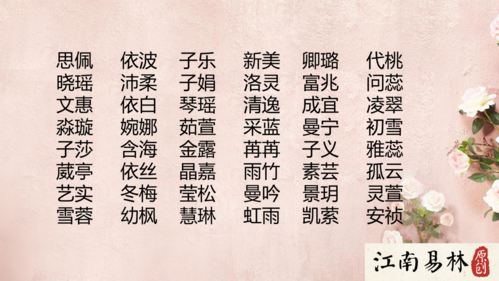07快男
來到這裡,沒有人後悔。
在過去20年裡,“07快男”毫無疑問是令人記憶深刻同時也讓人感受到複雜況味的一屆選秀。
在新舊娛樂工業交替的時代,在消費社會和粉絲文化剛開始萌芽的12年前,“07快男”以蕪雜、粗糙的形态入場,但從今天這個愈發完備精緻的選秀時代回看,卻顯得生動、蓬勃和多元。
12年裡,每一個人都在體驗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無法體驗和想象到的巨大名利飓風,也無一例外地接受“叢林法則”堅硬的揀選和命運的無常試煉。
昨天,冠軍陳楚生和13強中最早被淘汰的陸虎講述了他們的12年,今天,吉傑、蘇醒、張遠、王栎鑫将分享他們的私人記憶。
這12年中,吉傑用前幾年高度配合的工作換來解約後的創作自由,2013年發行的第二張創作專輯《自深深處》以最高得票率入選當年“華語傳媒音樂大獎年度十大專輯”之首以及“蝦米”年度十大專輯,他也被評價為“少有的以自身另類氣質音樂審美很快擺脫選秀光環影響的創作藝人”;
蘇醒也沒有停止過創作和自我表達,盡管這些自我表達的一部分在新的娛樂意識形态中常常被視為“癫狂”;
張遠則穿過初代快男和初代男團的起伏,在2018年又一次出現在新世代的選秀比賽中;
而王栎鑫的大部分工作已經變成演戲和參加綜藝,但他仍試圖實踐一種随時能拔腿就走的生活。
回望12年,在一個始終伴随濃縮性戲劇化生存體驗的行業中,他們努力學習着與名利場的無常共處,接受際遇的錯落起伏,聲名的來去。王栎鑫覺得07快男遭遇的一切,“像是一場華麗的悲劇”。12年後,吉傑發現,他們是一幫受了最多苦痛的選秀參與者。曾經他以為這是偶然的集合。現在他明白了,那是“偶像的命運”。
“因為選秀的初衷是要制造偶像,偶像它一定會有爆發和隕落的時候,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偶像越來越像快銷品一樣更叠。在“一切都是看運氣”“偶然性”和“命”組成的生态群落,他們也都漸漸找到了錨定自己的那塊礁石。
以下,是他們的講述——
文|安小慶
編輯|金石
圖|網絡(除署名外)
吉傑:我們都是鋪路石

尹夕遠 攝
1
小時候,我站在老家甘洛的山上,山下是鐵軌,我看到鐵軌就想哭,我在想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讀高中時,我開始喜歡一些西洋音樂,就特别特别想出去。考上大學,我第一次離開家。在壓抑的家庭環境裡長大,現在想來,音樂帶給我的是一種現實的逃避,是自己的一塊淨土。
所以,後來兜兜轉轉參加“快男”海選,也有一種命中注定的感覺。
2007年4月15日,好像是個周五。 我和當時的秘書還有幾個同事,逃了下午半天班,從上海開了三個小時車,到了南京。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逃班。說實話,那個時候我還挺看不上所謂的電視選秀的。你想啊,我當時在上海一個跨國企業裡做高管。那時候MTV音樂台、摩登天空都是來我辦公室提案要錢的。
我去參加完全是去玩,當時我有帶着一種就是我來教你們怎麼唱歌的很得意的心态去玩,根本沒有想到以後要當歌手。好像要去搞事,就這麼過去了。
第一個晉級賽區50強,後來又拿了南京賽區冠軍,進入全國13強。本來覺得是玩玩,嘗到點甜頭後,就像被卷到一個漩渦裡去無法自拔。
比賽中,我最享受的部分,聽起來好俗氣,但真的就是粉絲舉着牌子在那兒喊我名字,我到今天也希望有一天,我做成功一件事之後,我還能再好好唱歌,你要去機場接我,我超高興,我會在機場跟你聊天。現在沒有接機,已經五六年沒有了。
那時候的節目組,我覺得更真誠。
他們沒有講,啊楚生你就是一個流浪歌手人設,吉傑你就是老大哥。現在我們錄節目,大家都是為了結果設計腳本,但那時候完全沒有。比賽中唯一需要做心理建設的是,我收到的信和禮物永遠沒有别人的多。我記得那時候禮物最多的是灏明。禮物會送到城堡,我每次就告訴自己,喜歡我的人都是有檔次的人,有品位的成熟的人,他們不會搞這種,然後到機場人家都是一百多個人接機,我的隻有幾十個,我就會心理建設,沒事,我的人都是在忙着上班,哈哈哈哈哈。
第一次發現自己紅了,是比賽中途回涼山做了一場見面會,據說來了十多萬人,山上都站滿了。超開心,覺得自己是明星了,特别特别開心。
之後就到了決賽,我隻記得那天晚上的氣味了。那個時候,還是靠燃燒固體煙彈來産生煙霧。特别刺鼻,舞台燈光要出線條,必須要有薄薄的煙。現在都是做霧的機器了,我就再沒聞到過那個刺鼻的味道了。
我們穿的是銀灰銀灰的衣服,楚生和蘇醒他們倆穿的是金色的,我就特别“羨慕嫉妒恨”。但是我現在去看那比賽,我覺得我得第五名都多了,太難聽了,我那些歌,瞎搞,我就像在唱KTV一樣。
巡演結束那天,慶功宴的間隙,我和蘇醒發現張傑坐着沒說話,右邊的眼睛還有一點點紅。問他為什麼,他打趣的說:我看着大家那麼開心,有一點點感動,巡演就要結束了。。。。。。
是的,那個夏天結束了。

快樂男聲五強
2
藝人的工作适應起來挺快的。那時候火呀,每天都在飛,每天都在車上。做了三四年,給公司掙了不少錢,我那時候是掙錢第三還是第四多的。但一直沒給發唱片。我沒有鬧。有藝人是到公司找龍丹妮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有些女藝人的媽媽也在那裡要死要活的。
我好像有兩邊大腦。一邊大腦就是藝人,覺得公司太過分了,也想去鬧,可是另外一邊大腦,我是一個職業經理人,我就在想如果我是這個公司的CEO,我會把有限的資源放在何潔身上,放在張傑身上,因為他們的粉絲轉換消費是最快的。
我還記得,當年剛簽約的時候,我說,我要做一個世界級的爵士靈魂樂歌手。後來,除了沒發歌以外,其實挺快樂的。快樂來自能夠上台唱歌。
就在這種個人的調整中,懵懵懂懂的過了三四年。但因為大家同在一個行業,是朋友,同時也是競争對手,誰又出歌了,誰今天有什麼機會了,心裡慢慢地也會去關注和比較。
我記得那幾年跨年演唱會,我們在那兒候場,一會兒張傑就上去了,獨唱,一會兒魏晨上去了,獨唱。我們就是那種合唱,而且唱的是影視歌曲,那種感覺特别難受。慢慢的你會發現,啊,楚生可能有他候場的休息室,楚生不在了,張傑又有了。這種時候,難受,但是臉上不會表現出來,就裝傻。這是演藝圈一個必備的生存技能,我覺得我還是表現得很好的,表現最差的應該是栎鑫。
隻有一次,我們十幾個人在跨年晚會舞台上,拿着大剪刀在後面給楚生伴舞那次,消化起來是困難的。我并不是不願意給楚生伴舞,我很喜歡他的音樂,在音樂上也很尊重他,但我心理上是很難接受的。
我現在都還記得那個畫面,我拿着那個特别大的剪刀,楚生在前面彈着吉他,張傑、我、譚維維,十幾個人在後面伴舞。就因為他是冠軍嗎?我覺得這不公平,這是對藝術的不尊重。下台來就很難過。
慢慢地,從一些小事件開始了解這個行業了,原來它是這樣的,很多時候是運氣加資源,還要臉皮厚。
臉皮厚,我有的時候也挺擅長的。
就像我當時解約的時候,我找龍丹妮,找楊柳,她們就不接我電話,不回信息。我就一直發一直發一直發,她也不回我。過幾天我就去公司堵,堵了幾天之後就堵到了,我就直接跟丹妮說,我了解公司是一個什麼狀況,我放棄之前的生活進入這個圈其實就是想做歌,現在我不要你給我做歌了,因為我知道你不會給我做的,我現在就要出去,你讓我自己出去想辦法做音樂。
我說得特别真誠。她聽完說,下午給你辦。我應該是有史以來天娛第一個一分錢沒賠就走掉的。雖然龍丹妮當時也是個商人,但是她還是挺講道理的。
其實開始那幾年我寫了好多企劃,我甚至自己還做過一張唱片,讓公司幫着去發給媒體。但是我發現我每次去公司,那三箱唱片都還堆在那兒。解約的時候我就把它們全部搬回家了。
一般去談解約的時候,下家都已經找好了,但我不是那種性格的人。解約後有大半年的時間,我都是一個人。我有個高中同學是國企的,我說你來當我經紀人吧,我們兩個就皮包公司似的到處演出走穴。
那時候,我去商演,最受不了的一個介紹詞就是,“下面有請2007年快樂男聲五強吉傑”。我的頭發和造型弄得很時尚,也準備了新作品,然後走到那個台口,聽到“下面有請2007”,我就覺得自己越來越矮,越來越矮,到“快樂男聲”,我就不想上去了。因為經曆了這麼多,自己開始出專輯了,我覺得我的東西不是這個頭銜能夠涵蓋的,有種不服氣的感覺。
2011年第一張專輯做了之後,我曾經想去找之前的公司同事,找他們拉一些贊助做一場全國的小型巡演,預算什麼都做好了。以前我的一個下屬負責一個大洋酒的公關,他說他們是跟碧昂絲這種等級和華語樂壇最頂級的藝人合作,他沒辦法幫我,我馬上就說OK。又去找了另外一個人,然後約她們在KTV裡見面,給她們唱了很多歌,但就是開心完了之後就沒消息了,都說我們會去幫你聯系,然後第二天就沒消息了。
中間确實看了很多世相,也學到了很多生存技能。就像前段時間我去參加《流浪地球》的首映。其實那天去了好多好多大明星,但我被叫上去說話,那些台下的粉絲肯定是對我最不感興趣的,但是我就有辦法在現場讓大家笑起來,我覺得自己被動地習得了一些技能。
這些習得,也有可能會讓你異化。
就像每當上面那種情況出現的時候,其實我都會靈魂出竅,就是有一個“我”會浮在半空看着下面的“我”,說,“吉傑你現在真的好醜,你變成了一個小醜”。
經常會有這種時刻。就是隻要涉及到自己的自尊、自信、自傲,和不認同的時候,第二個自我就會出現。

吉傑在新專輯首唱會上
3
這些年,我最難受的其實是《歌手》裡面歌手上台,而我站在台側的那一刻。
我覺得是一種上刑一樣的難受。 你們看我在鏡頭裡站着陶醉,其實我的靈魂正在出竅——“你就别裝了,你是不是覺得他沒有你唱的好”,然後再回去。我會告訴自己,隻要還能靈魂出竅,隻要還有這個概念支撐着,生存下去就好了。所以,我每次還是會去。因為首先有錢,第二它有曝光。
那時候,《歌手》節目一些工作人員來北京。大家會一起約去KTV,唱唱歌,陪他們玩一玩,聽到消息的人一般都會去,大家都卯着勁兒地呈現自己唱得多好,有這種機會大家都會拼命展示。我心裡就是,别努力了,上不了的。他們不了解,唱歌隻是其中一個方面,你要通過唱歌上也可以,你得像迪瑪希那樣驚為天人,那是一條通道。另外一條通道,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社會代表性,要有一定的關注度,第三條通道就是,你功成名就,你有自己的代表作。
但我其實很清楚,我三條通道都不屬于。最早我也認真地推薦過自己。我自己花10多萬錄過一張翻唱的demo寄到節目組。有試唱我一定會去,但是一直上不了,我也特别理解,也不會糾結了。
我曾經對Jessis.J說過,我說,如果我有機會站在舞台上,我不會比你差的。她說我相信。很多人說,吉傑就是合夥人而已,但我覺得我的才華是無法否定的,隻是沒有機會。我覺得我可能有一種超乎常人的自信。一個藝人要在娛樂圈打拼你一定要有種誰都摧毀不了的自信。
錄《歌手》的時候,有一次騰格爾老師一進來,直接指我,他說,這個人是我最喜歡的歌手,然後有一次Jessis.J沒來,汪峰老師就說吉傑上,吉傑絕對沒問題。但這些在真人秀中都被剪掉了,因為它不符合節目的主軸。
還有一次,我記得去年那一季錄包餃子的時候,所有人,包括劉歡,他們全部都在喊,“吉傑唱一個”,我就沒唱。楊坤把我的《花兒》都放着了。我就不唱。
因為,首先我知道這個會剪掉的,因為,它不符合這個節目的主線。所以最後他們都覺得我瘋了,編導也在說你唱啊,我就不唱,我把電扯了,扯了之後,楊坤又插上,來回搞了好久,很尴尬,但我就沒唱。
一點猶豫都沒有。我就是去做合夥人的,節目組需要吉傑是一個特别懂音樂,然後能夠把很難搞的藝人搞定,能夠讓這個藝人在真人秀的部分很自然地表達的人。
把合夥人做到最好,其他别瞎想了,該是你的就是你的。
這個行業,就是18線小明星有18線的煩惱,一線的煩惱也不少。我特别喜歡接觸圈外的人,比如說現在跟我們做直播的這些同事,很多從杭州來,我覺得他們比一個一線明星有意思多了。他們的工作,他們怎麼開始做直播,他們經曆了哪些奇葩事,我覺得比跟藝人聊天有意思多了。

《歌手》中吉傑擔任Jessis.J經紀人
4
從2007年到現在,12年了。
就像我曾經在博客裡寫過的,“我從一個默默無聞卻倍受業界尊重的外企經理,變成了萬衆茶餘飯後的話題,變成了平台上争光添彩的新星,變成了奔忙于綜藝通告的小小藝人,變成了東西南北遊走跑場的賺錢機器,一年一年過去,我從為娛樂公司賺錢名列前茅的話題人物逐漸過渡成為依靠07年餘熱苦苦支撐的過時符号”。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2012年。我說,“選秀和歌唱比賽,乃至是整個行業,從頭到尾可能隻能給你一樣東西,那就是讓你知道大起大落是個什麼東西”。
現在再看,其實不準确,因為事實上我就沒有“大起”過。我覺得比賽完的那一天,就是低谷的開始,我到現在也在低谷裡,我幾乎就沒有走出過低谷。但是我自己已經算是比較好的。
我們07快男裡很多人的經曆,都讓我非常難過和惋惜。我們是一幫受了最多苦痛的選秀出道的兄弟。這是一種宿命吧。我現在明白了,我覺得這是偶像的命運。因為選秀的初衷是要制造偶像,偶像它一定會有爆發和隕落的時候,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我們就真的像一批樣本一樣。所以說龍丹妮牛,就是她打造了13人13面,這13人代表了社會上各種各樣的人和各種各樣的音樂風格,後來的選秀風格太趨同化,其實都沒有做到這點。
今天我自己再看,我覺得“快男”其實是一個新舊時代交替時期的試驗品,也是一個偶像制造的節點。 為什麼到今天我們都還是家喻戶曉的人,我覺得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它是老百姓自己選的,每個人都參與。第二,它是真笑真哭真感動,現在綜藝都有台本,那時候是沒有的,哭了就是哭了,忘詞了就是忘詞了,我們連耳返都沒有,但是我是覺得那三年選秀最厲害的地方就是這兒,它處在一種懵懂期,懵懂期最本質的一些東西特别感人。那種粗糙其實也挺有生機的。
到後面的選秀,就更加有工業化的感覺了。我們也聽說有的女孩,本來是很女孩子氣的,但她覺得扮成男孩子氣可能會受人歡迎,所以她進入這個比賽的第一天,就剪短頭發。這在我們那屆是聞所未聞的。
處在曆史的節點,我覺得還有一個需要承認的,那就是我們都是“鋪路石”。
“鋪路石”的命運,也是曆史的必然。新鮮事物出來之後,主流人會覺得受到威脅了,品牌會覺得他們是草根,各個方面都戴着有色眼鏡。但是通過早期選秀,通過老一代選秀人的努力,之後好聲音也好,嘻哈也好,樂隊也好,他們一出來商業價值就好了。
我們當時電視通告都是幾千幾千的,現在的電視通告都是幾十萬幾十萬的,甚至有上百萬的。我覺得這是早期選秀人心裡永遠的一個糾結吧。那個時候的藝人,除了挺下來的春春啊靓穎啊維維啊她們,其實大部分人在最好的時候是沒有掙到錢的,真的沒有掙到錢。
很多人好奇0713之間的向心力怎麼産生的。因為大家都在低谷。如果大家都發展得像張傑那麼好的話,可能早就已經沒時間聯系了。我覺得這幫快男兄弟為什麼這麼好,說句不好聽的話,就是大家都沒有發展到能夠去互相嫉妒和競争,去搶這些資源的能力。
這12年,我做了幾百項努力,各種各樣的事,失敗了幾百次。出專輯做演出這些不用說了,還研發過英語口語課程,學過脫口秀,考過主持人證,辦過雜志。最近我開始做直播賣貨。
因為我有十多年的跨國企業和五百強企業的品牌經驗,我自己給自己的定位是我想做成淘寶第一明星主播,我對這個特别有信心。我曾經以為做直播賣貨的時候,那個分裂的自己又會站在旁邊一直斜眼,結果居然沒有,所以我現在特别開心。
這12年,最高的,我去格萊美采訪過,去跟很大的明星聊天過,然後最差的,去幾個人的夜店演過,從國際到國内你有一個很完整的畫面感,人變得更踏實了。我覺得這些經曆都特别特别好。不管最高,還是最低的。
我也沒有後悔12年前選擇成為藝人。這個職業給人的最大樂趣我覺得是三個字——“可能性”。
娛樂圈不是一個努力和得到成正比的地方。但因為大家認識你,你有無限的可能性,去做任何的東西。我們社會上的很多人是沒有這個可能性的。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是很奢侈的。它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
蘇醒:我們沒有被詛咒,相反還很幸運

受訪者供圖
這12年裡,我的落差感也沒有那麼的大。
可能是因為我太過理性。比賽的過程中,看到那麼多的人聚集在一起為某個人狂歡的時候,我覺得我不是特别能去享受這個事情。在表演的時候,我很enjoy和觀衆的互動,但我不是特别能夠完全地癡迷或者是迷戀上那種萬人簇擁的感覺。
當我看着他們為我歡呼,為我尖叫,聲嘶力竭、聲情并茂的時候,我能夠想象到,OK,這隻是Just this moment,可能并不一定是永恒的,可能會轉瞬即逝。我也能想到這是因為我們出現在一個全國播出的平台,所以忽然一下受到了上億人的關注。這些人聚集、瘋狂是正常的,但是這個夏天過去了呢?慢慢慢慢這些東西都會淡化。
比賽期間,當發現大家開始對你有所保護,甚至很多人希望從你身上得到一些什麼的時候,我開始發現自己成為了商品。
我覺得我是個快樂的商品。很多人說商品,你就是個商品,有一種先入為主的看法,好像這個人沒有了靈魂,好像他是被人利用和榨取的價值。come on,我覺得每個人都是有價的,我們都是商品啊,在這一點上我接受起來一點障礙沒有,甚至還會覺得挺好,我挺有成就感、滿足感的,I get value,我有價值了。
比賽之後簽了公司,資源蛋糕就那麼大,每個人有自己的方式去獲取。有時候,因為一個晚會的位置,大家都會不太開心,不太愉快。甚至晚會上能不能唱自己的solo,還是得跟别人合唱,為什麼給你兩首歌,而我隻能跟别人合唱半首歌……
那一兩年其實挺痛苦的。時間久了,我沒有感受到獲得應有的扶持,或者可能公司有更要捧的人,同時我又不希望去跟别人争破臉的時候,我做了最符合我性格的決定,轉約,撤退。
這個過程非常痛苦。期間跟朋友和家人一共借了50多萬,自己出了一張專輯叫《三十未滿》,裡面有《北京city》的那張。《北京city》和《分裂》都是我對這個行業的觀察。
我從小就對觀察人非常有樂趣,而且這似乎是種本能。娛樂圈就是名利場,這個圈子很妙,人際關系往往呈現彈性搖擺狀,陌生和熟識可以在頃刻間變化,見人位勢高,則各種裝熟,不認識也說認識。看人身份低,便各種裝傻,認識都說不認識。
至于什麼要維護關系,什麼要察言觀色要會做人……我最讨厭就是在這個圈兒裡“你要會做人”這句話。這句話賊惡心。
你讓一個藝人會做人,這是最大的謬論,那得多平庸啊,你要會做人,才拿得到機會。國外的藝術家,哪個不是脾氣特别怪,哪個不是經常一身毛病,會做人是靠他經紀團隊幫他去做人,他維持他藝術家的這種扭曲,甚至是一些癫狂,但他在業務上他是個天才,我們要保護這樣的人。
這個圈兒所有一切其實都是看運氣的,都是偶然性,都是命。你點兒在了,不用你會做人。
我現在很讨厭一些年輕藝人進來就制式化了。“前輩你好”,趕緊低頭,握手,你好你好你好,我不是說不應該這樣,我也不懷疑人家是有禮貌,但是一看就是被教的,會做人,微笑,跟每個人都微笑。但是我看不到人,我看到一個個漂亮的皮囊,你人呢?比如說你在台上給我甩個臉,或者有時候你覺得不爽,我還覺得哥們兒有意思,可以多接觸接觸。
我們當年不是這樣的呀,我們當年是老百姓看電視,我們沒有粉絲去把我們養起來,所以我覺得從這點講,我們是挺幸運的,我們不能說為所欲為吧,但起碼可以做相對比較真實的自由的自己。
我都想過,我要是在當今這個環境下去參加選秀,第一輪被淘汰了,絕對的,我看誰不爽我直接說,估計一半的選手都受不了我。所以我很佩服張遠,他能在那裡撐幾個月,我撐不了。
這個圈子的名利來得特别快,消失得也特别偶然。這方面我還好,每次聊這種話題,我到最後都是誇我爸媽,我真覺得我最幸運的就是我受過很好的教育,我有特别好的父母。我好就好在我可能家庭經濟條件還OK,我從一開始就把這當做一個工作,我的匮乏感沒有那麼強。當然你給我名和利,太好了,但是沒有的話絕不至于那麼的失落、彷徨和痛苦。
選秀比賽當時是很新鮮的,那時身在其中,我沒有覺得它會改變什麼時代,後來才證明它确實是改變了娛樂行業的劃時代分水嶺。
2017年,出道十年的時候,我寫了那首歌,《stand up again》,歌詞寫的是,“這十年是夢是幻,是痛是斷”。那整個比賽就挺夢幻的,現在想想都覺得那是個挺扯的小概率事件,真的是很偶然的機遇。
我感覺2007快男是一個實驗品,是一個多家受益的試驗品,行業得到了巨大的改變跟推動,當時的公司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益,包括我們之後很多年都因為當年的這個起點高,而有所受益。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試驗失敗的産品,07快男再失敗的話,中國沒有成功的選秀了。
這麼多年,很多人說在我們身上看到強烈的命運感。我覺得我會有自己的命運感,但這跟集體沒關,隻是這個集體裡,我出這個事,他出那個事,會顯得這個集體命運多舛,我覺得純屬巧合,我其實特别反對這樣的一些論調,這其實就是個概率學,放到任何一個集體裡,裡面的人也都會有各自出的事。并不是我們這個集體好像被詛咒了一樣,我們現在過得比很多人好啊,現在的團體,平均半年、一年就沒了,我們現在還有呢,人還在呢,詛咒啥呢?
如果非要用這個詞的話,我告訴你們,什麼是被詛咒的一代:我們之後那兩三屆、三四屆選秀,他們才是被詛咒的一代,連看都看不到,才是被詛咒的。
至于我們之間的友情,我們經常聚的,栎鑫來北京都不住酒店的,住我客房,在我家吃了三天,這自然而然的。虎子來吃個飯,去楚生那兒練個歌,打球的時候姚政也去,很自然——當年我們這夥人一起參加了一個比賽,今天我們留下了幾個朋友,就這麼簡單,當年我通過比賽收獲了名利,今天,我通過12年收獲了幾個朋友。
張遠:出來串個門兒,用了12年

尹夕遠 攝
2007年,我在南京财經大學讀三年級。按照原本的打算,大學畢業後是要去澳洲留學。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出現了《快樂男聲》,也都是命運。
那幾個月,學校隻有兩個時間是最興奮的,一個是看世界杯,一個就是看我比賽。總決賽那段時間,我媽媽為了給我拉票,瘦了20多斤。
比賽完就是巡演。站在台上,幾萬人在下面盯着你唱歌跳舞,當時會有這樣一種感覺——我是誰,我何德何能,我就這樣子了?
巡演結束後,公司想做一個男子組合,剛開始肯定是不想去的,誰想做組合啊。過了幾個月,發現發專輯沒什麼希望了,想法才變了,因為你是第九名,(資源)排不到你啊,誰會去做一個第九名?
後來 “至上勵合”一出來,哇,爆了,那時候“紅”到就是簽售簽到差點中毒。
“快男”和“至上勵合”的開始,都爆了一下。但過去十幾年,事業整體的發展情況就是每況愈下。我輾轉了很多個團隊和公司,試過拍戲,綜藝,給模特做音樂老師,甚至兼過棚,開過酒吧。
對2013年左右往後的生活,我有點類似于斷片的感覺,都不想再去回憶了。因為我不喜歡那個時間段的自己。那幾年我自己看自己,我都覺得好讨厭。我對自己太不好了。就覺得自己是個廢物。在北京,隻是苟活而已。到底這些年我在幹什麼?我在堅持什麼?真的有一種堕入無邊黑暗的感覺,我覺得我是廢物,我這十年什麼都沒有做。
那時候,什麼都不想吃,吃個黃瓜吃個雞腿都沒有味道。有一點能量,我會看書,硬看書,忍着痛看書,硬去健身,哪怕不吃東西,逼自己出門健身。但更多時間是窩在沙發上一整夜,一整天,拿着ipad玩玩《三國殺》,玩了幾千把。我不敢睡大床,因為我覺得我配不起那樣的大床,隻敢睡沙發,在沙發上不那麼容易翻來覆去,最後沙發被我睡塌了。還有很生氣的時候,很不甘心的時候,會打枕頭,不過瘾,然後去打牆,手腫了,放到冰箱裡冷凍。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去看《我是歌手》的彩排,因為我很喜歡那個舞台,太愛那個舞台了。等我坐車到門口下來的時候,同時下來是一個經紀人,他一下車那個反應就是,“诶,他怎麼來了”。他的表情就是我怎麼配上《我是歌手》?
做藝人以來,我的銀行卡在前七八年,存款沒有多于過十萬塊錢。最少的應該就是卡裡可能就是幾千塊錢了吧,如果再沒有收入,房租就給不了的狀态,但還好,總是在關鍵的時候會頂上來一些活動,收入一小筆,從來沒有大筆。
在“至上勵合”的時候,有段時間,公司給我們訂頭等艙,我們自己會把它換成經濟艙,拿那個中間差價補貼一下。反正就想,忍一忍吧,忍一會兒兩千塊錢可以拿,挺好的。

至上勵合
為什麼我跟蘇醒那麼長時間的朋友,因為他永遠沒有嫌棄我。就像他買奔馳的時候我買克魯茲,我倆一塊出去玩,他有些朋友開着賓利來,我開着個克魯茲,大家覺得Why?我無所謂啊,我覺得又怎樣呢,你又比我高貴到哪兒去呢。
可能也是因為我上的财經類大學,不是從小戲劇院校或者是其他藝術類院校畢業的,所以我也知道所謂的真實的生活。說實話,我的收入作為藝人來說是挺心酸的,但是比起一般的上班族和普通人來說,我也不錯了。
我也不覺得自己有多苦情。很多時候,我會有一種觀察的視角,也看到更多的人和人性。
2019年,在2007快男和“至上勵合”之外,我又多了一個新的身份,“創造營2019”選手。

“創造營2019”中的張遠
這兩年整個娛樂行業進入寒冬。很多人選擇淡出或者蟄伏。去年看了“創造101”和“偶像練習生”後,我反而突然有了一個突發奇想,想去參加。因為我這個人一直以來都太溫吞了,太穩了。很多人說,在張遠身上看不到任何出格的事情。
這世界其實很簡單,不管你遇到什麼問題,一個真心話,一個大冒險——你想不想去,想,去了會不會後悔,不會,那你就去吧,你就去冒險吧。
12年的時光也告訴我,保守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就去了。這也是我從快男出道開始的12年裡,我自己做出的最大的決定。
說實話,在決定參加節目後,我充滿了巨大的恐懼和壓力。從理性來說,我知道這件事有好有壞,好是重新被更多人看到,壞的方面第一場就淘汰,成為炮灰,晚節不保這種感覺。
從2013年起,我就幾乎沒有跳過舞了。參加比賽,沒有退路,我選擇去海外封閉訓練了一個月。
我租了一個房子。完全與之前的世界隔絕。天天健身、跳舞、唱歌,和聲樂老師練習,重新開始,就像一個學生一樣。不停地練,不停地唱。一個多月,過年也沒有回家。像運動員重新找競技狀态那種感覺。
我前後經曆了四輪面試。過程大概就是一次一次地被打擊。幾乎每一個選手和節目組的工作人員都告訴我,遠哥,我們是聽你的歌長大的。我記得有一次面試,節目總導演曾經非常嚴厲地告訴我,我進不了他心中的前20。
幾個月後,我重新站上舞台。結果做的還不錯,我自己也很滿意。
身在這個行業,快樂的時間其實很少。
經曆了12年的起伏,我并沒有覺得自己有多特别。因為我非常清楚,誰沒吃過苦。而且我覺得有這樣的經曆,反倒不應該是做藝人更好的一個經曆嗎?
特别像我們這個行業,痛苦就是養分,痛苦也是能量,當你把自己的痛苦變成了工作,就像梅姨拿金球獎終身成就獎時的獲獎感言說的:
——把你的心碎變成藝術。Take your broken heart, make it into art。
曾經有記者問我,如果當初沒有參加“快男”,會不會我和07快男的生活都不會那麼動蕩。可是人生不就是這樣嘛,我覺得挺好的。你覺得這個劇情非常跌宕起伏,甚至不堪承受什麼,但其實我覺得自己已經很幸運了。
那幾年真的是選秀的巅峰時代,我們是第一屆“快樂男聲”。細數13個人,幾乎10個人都還在線,這個量絕對是曆屆選秀當中最強的一屆。我們是一個時代的印記,沒有人不記得我們那個時代的人。在我心裡也覺得,我們是最經典、最特别、最唯一的一屆。因為我們就是“0713”,沒别的解釋。
說實話,當時比賽的時候大家之間也會議論來議論去,有小團體什麼的,這都很正常。但比賽之後,我們所有的巡演都在一起,之後很多晚會大家都會再聚,甚至後來有一些也不在天娛了,大家漸漸地互相了解,彼此支持,慢慢形成了一種兄弟情誼,而且越到後面就越真誠,越真實,蘇醒從本來大家最讨厭的人反倒變成了大家都還挺喜歡的那個人。
為什麼能做那麼多年好兄弟,就像蘇醒置頂微博裡我的留言一樣。我說,這些年我們都各自成長跌宕輾轉,好在互相陪伴,我們接受人性和世界明暗,幸好也都品性良善,真誠坦然。
我不後悔進娛樂圈,我多精彩啊。
蘇醒真的看得透,關于藝人,他說過一句我非常欣賞的話——我一人,我藝人,我異人,我亦人。
我的微博名字裡面有一個單詞,bird。如果演藝圈是一片大森林,我希望自己是鳥。張開翅膀想飛到哪兒飛到哪兒。
我想過,比如說如果真的财務自由了,我也不用完成音樂夢想了,我會去雲遊一年,把自己吃成個胖子。對,胖子,我挺想試一試的,我好奇自己到那個程度可以醜成什麼樣,油膩成什麼樣。
在這個圈子裡,我時常感覺自己像是一個來串門兒的。隻是串得時間久了一些。以後肯定要走,但目前我還覺得沒串夠。
王栎鑫:我是幸運的,隻是沒有在做最熱愛的事

尹夕遠 攝
2007年,我17歲。
那一年,我媽其實準備安排我去當兵,父母輩會覺得當兵、考公務員都是特别靠譜的選擇。但我從小是一個特别叛逆的小孩。比如我15歲談戀愛的,不顧老師、校長、家裡的反對,跟初戀談了五年多,一直談到出道之後。
我從高中就幻想可以當歌手,所以,那一年,我去參加了“快樂男聲”長沙賽區的海選,但第二輪見評委時被淘汰了。淘汰之後,母親覺得每個賽區一兩萬人,不可能選中我,就不想讓我繼續下去了。但是我自己很堅持,我說還有兩個賽區可以比,一個是廣州,一個西安。母親極力反對,我說,那你借我一千塊錢吧,将來會還你,我說我必須去。我坐了十幾個小時的綠皮火車到了廣州,我媽送都沒送我。
那時候每個賽區有三條通關紅領巾。在廣州賽區,我運氣也很好,拿到了其中一條,直接進入到全國五十強。 比賽過程中不能使用手機和上網,第一次覺得自己紅了,是我們13強一起去北京拍MV的時候。我記得那是在北京T1航站樓,大概來了上千人接機,特别誇張,人走不出去。機場也沒有這種經驗,大家措手不及,沒辦法,隻能一個一個出,出一個,走一家粉絲,出一個。然後是比完賽後全國巡演,粉絲們會造勢、争地盤、碼方陣,每個人應援的顔色都不一樣,比誰的人氣高。你家把這條街包了做廣告,他家就做一百個空調氣球,我家就是大巴。
12年過去,選秀比賽也不太一樣了。感覺那個時候的比賽更純粹一點,大家接觸到的東西不多,也沒有太多的準備。現在很多選手或多或少都披上了一層保護殼上來。以前完全沒有什麼人設的分配,你自己想怎麼表達怎麼都可以。
我記得有在廣州賽區的時候,有一場是俞灏明跟劉洲成pk,讓晉級的人來投票。我覺得這個票沒法投,他倆都是跟我一個賽區的,我就當着全國觀衆的面直接把票給扔掉了,場面一度尴尬。過後想真是有一點不顧全大局,當時也沒有這方面的情商。
還有就是吉傑拿了南京區冠軍後棄賽又回來的那場,他說自己不參加了,又回來,有一個畫面是他過來跟每個人擊掌,擊到我這兒的時候,我手沒伸出來。當時就是不爽他。
還有就是“四進三”那一場,蘇醒跟魏晨PK,九個兄弟來投票決定了他們倆誰進前三。當時我不太爽蘇醒,不太喜歡這個人。在台下的時候,我就跟兄弟們說,不要投蘇醒,大家一起投魏晨,把魏晨直接投進了全國前三。最後變成蘇醒跟張傑PK,把張傑PK掉了。

蘇醒PK魏晨
那個時期,我們算是重新定義了選秀比賽,觀衆的參與感比較高,我覺得有很多東西都是非常珍貴的,所有表現出來的稚嫩也好,所有能看得到的性格缺陷也好,全部都展露無遺。
決賽那天的夜晚,台上,楚生拿冠軍後一臉懵,而在台下,我已經在幻想自己在各種萬人體育場開演唱會的樣子,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經先簽唱片公司了。其他人大都對未來有些迷茫。
但現在想來,我覺得他們那時的迷茫還更好一些。
因為像我,一開始對自己未來的期望太高了,後來的失落感反而更強。失落感最早出現是在2008年發了第一張唱片以後。銷量挺好,但因為一些原因沒能持續頂上去。另外,我出道前覺得歌手就是發唱片、開演唱會,但真的出道後,每天就是參加通告,錄節目,演出的舞台都特别爛,所以内心期待值就下滑特别快。
我記得有一次錄一個綜藝節目,節目組安排我唱歌,讓我去試麥。調音師遞給我一個特别破的話筒,那話筒感覺都癟了。我說那邊不是有好的話筒嗎,他說那個是給後面大腕兒用的。
我覺得進這個圈子給我上的最好一課就是這種落差和不被人重視的感覺。當你不被人重視的時候,那你就隻能靠自己了。它讓你在面對最差的那個狀态時,内心不會有太多波瀾。
2007年我們出道的時候,傳統唱片工業已經沒落了,我們要被迫地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來“曲線救國”,像一個跳闆一樣去輔助自己的歌手夢想。 比如最早錄很多綜藝節目,我真的很煩耍寶啊,演小品什麼的。幹什麼?我不是幹這個的,我是唱歌的。拍戲,拍什麼戲?我不愛拍戲。可是後來漸漸地,就把所有的這些事情,變成了自己的職業。而且做着做着,你發現改變也沒有那麼難——當你把自己變成一個十八般武藝樣樣都不精通的人,你确實可以好好地活着,隻是你沒有在做你最熱愛的事。
有一點沒有變的是,在出道12年的任何階段,我不會戴墨鏡、戴口罩、戴帽子,把自己遮得特别嚴實,怕人認出來什麼的。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平凡的人。
這可能和我天天看宇宙的視頻有關系。藝人這個行業天天面對無常和名利的來去,有的人靠宗教,有的人靠跑步,而這是我的自我療愈方式。 我從小就喜歡擡頭望着天空,對宇宙這個東西特别特别有興趣。後來就看和宇宙、天文相關的書和節目。你要知道宇宙有多大,你就知道自己多渺小了,你自己曾經自以為是的那些東西,你高看自己的那些東西,那些浮躁的、浮誇的所謂名利,全都不重要。隻有愛是很重要的。
對這個行業,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陷得太深。我希望自己一隻腳在裡面,一隻腳在外面,我可以随時跨出來。
就像我結婚。 男藝人25歲結婚?我說沒多大事,跟年齡沒關系,跟錢也沒關系,我當下想做這個事情,我想愛這個女人,我想跟她一起去冒險,去嘗試婚姻這件事情,我去了,我生了兩個非常可愛的寶寶。我想去另外一個城市生活,我就去了,好多朋友好像離不開北京,我不是那種人。

王栎鑫結婚
我是一個可以拔腿走掉的人。當時我在北京待了八年,我也愛這個城市,但是那個當下,結完婚之後,我想回老家體驗一下長沙的生活,我就回到長沙生活了兩年。我覺得安逸啊,很舒服,每天可以去對面菜市場買菜,可以遛彎,體會不一樣的人生。在長沙住了兩年之後,我覺得孩子要上學了,長沙可能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去上海吧,OK,那我就去上海,我在上海生活了一年。
我自認為生在一個特别好的時代。
當時大家能看的節目就那幾個,我們07快男的國民認知度挺高的,哪怕以後都沒有那麼紅,但是大家都認識我們,看着我們一路成長。
我們這批快男确實挺不容易的,像一場特别華麗的悲劇。
真的,比賽時大家都是年紀輕輕的花樣少年,出道後光鮮亮麗,但後來每一個人都經曆過了各自苦痛的歲月,俞灏明啊、阿穆隆啊、蘇醒、陳楚生,各有各的起伏,包括已經退出的郭彪和姚政,還有現在在網上樂呵賣貨的吉傑……
隻有少數人是幸運的,我覺得我是幸運的,我覺得張傑是幸運的。 我沒有經曆過大災大難,也沒有經曆過什麼痛苦的人生,我就像那個真的是被老天眷顧的人。我們聚會也會聊這個話題。姚政每次見我就說,你丫真是運氣太好了,你太幸運了,真的,好好珍惜吧。
大家之間的情感聯結,我覺得真的是從各個兄弟經曆苦難之後,開始變得更加完整和越來越堅固。因為他們的事情,我哭了多少回,天哪,灏明那次(我)都哭成啥樣了都。接受不了,真的接受不了,覺得太可惜了。最可怕的是灏明受傷之後,我們身邊還有人在讨論賠償這個事情,有人說,至少還能賠點錢什麼的,這是什麼人啊,在他們眼裡錢還是蠻重要的。
我還是希望所有那些不好的事情都不要發生。不是說每個苦難都是鍛煉自己、豐富自己人生的,我覺得人生不需要這些東西。比如灏明的災難也好,阿穆隆的災難也好,蘇醒和楚生的解約也好,都是特别痛苦的事情,都是永遠抹不去的。
但我真不後悔進入這個行業。 我覺得這個行業讓我這個普通人體會到了不一樣的精彩人生。你在這裡獲得了關注、支持,掌聲和名利,也看到了形形色色各種缺陷的人。
如果這個行業是一片叢林的話,我應該是河流裡面的一個鵝卵石吧。一直靜靜地在邊緣的地方看着鳥飛,蟲爬,看這個茂密的森林,葉子掉落,重新生長。我在水裡躺着,一直被沖刷,會被磨平,有可能發大水的時候也會把我沖走,沖走就會去到另外一個地方,那個地方也可能是我另外一個家。
12年過去了,我的面相也變了。眼角越來越往下,沒有以前那麼鋒利了,好像更加從容,更加友善,怎麼說,好像變得太會跟所有事情和解了。其實隻有我自己知道,我還是一直在跟自己過不去。
我曾經是田徑運動員,我喜歡競技,我内心對榮譽、對第一名的追求一直都在。現在,我人生裡面唯一的還可以去追求排名和title的,是撲克。
我已經打了十年撲克,也拿過一些小比賽的冠軍。這是我最好的平衡藝人工作的另一個愛好和運動。
當我坐在一個桌上,我一直在做腦力運動,在競技,在下注,我是靠每一次下注去和其他人交流的。我不再需要跟人溝通了,我可以把自己關在一個小的世界裡面,我可以戴帽子,戴面具,穿成一個卡通人物都可以,不需要跟人交流。
競技體育它是有世界冠軍的。但娛樂圈沒有這種。就像吉傑說過的一句話,娛樂圈不是一個努力和得到成正比的地方。但是撲克世界可以。
我内心還有自己想堅持的東西,可是另一方面我又好像很幸福地過着自己的生活。 就好比我常常跟我老婆講,有一天,我會離開你。 一開始女人哪能接受到這種。突然消失,意外,離開。我自己背上行囊,自己去過自己一個人的人生。比如說我孩子18歲的時候,我可能就離開了。你總會有你自己這一輩子想追求的一種生活方式,或者是,哪怕你愛一個人,想去一座城市,過另一種人生。
你沒有實現過,你從來沒有實現過。但你不想一輩子都無法實現。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