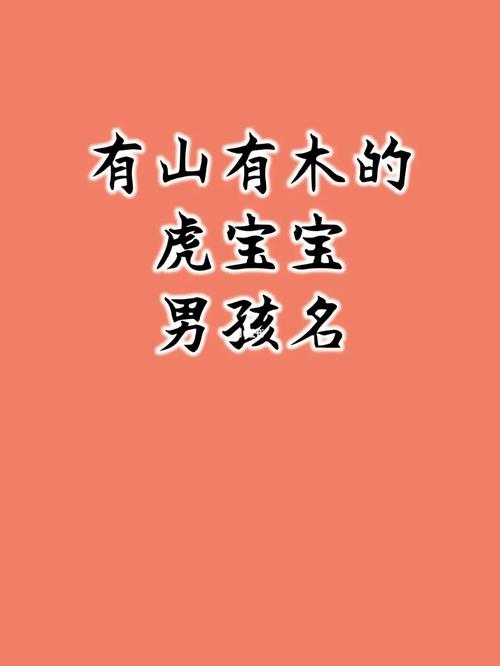2018年8月,位于黃河岸邊河灘潮濕沙地上的柽柳林,洪水時節,黃河水經常漫上河灘,浸泡林地。

2018年8月,羊曲水電站已經修建完部分基礎工程。

12月16日,然果村柽柳林中的一棵柽柳樹。

12月16日,工人駕駛卡車、吊車、挖掘機正在移植柽柳。
位于水電站水庫淹沒區内;樹木遷移工作已再度開始;有專家認為強行移植會緻古樹“全軍覆沒”
最近兩個多月,青海省同德縣然果村護林員田紮西發現,自己守護多年的一片古柽柳林熱鬧了起來。
從10月中旬開始,大型卡車、塔吊、挖掘機等駛入古柽柳林,将一些小樹連根拔起,“大樹是一棵一車運走,小樹是兩棵一車運走。”據田紮西統計,施工方目前已移植了20多棵中小口徑的樹,還未開始移植年齡更大的古樹。
柽柳,多分布于甘肅、内蒙古、青海、甯夏等地,因此又稱甘蒙柽柳。2010年,田紮西守護的這片古柽柳林被前來青海考察的生物學專家發現,并被多位研究者認為是世界範圍内迄今為止發現的樹齡最老、樹幹最高、樹徑最粗、分布海拔最高的野生柽柳林,具備巨大的生物多樣性價值,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景觀”。
然而,2002年,青海省立項了“黃河羊曲水電站”建設工程,選址就在同德縣然果村附近,由青海省政府委托黃河上遊水電開發有限公司建設。按最初規劃,水電站庫區大壩将于2018年底落成,屆時這片古柽柳林将全部被淹沒。
随之而來的是持續多年的争議。青海省提出将古柽柳林整體進行移植,并提出了由多位業内專家調研完成的保護方案,但亦有多位專家對方案提出質疑,稱方案存在多處“錯漏”,移植可能對古柽柳樹造成毀滅性破壞。
争議聲中,水電站在環評報告未通過的情況下已開始建設。
四個“世界之最”
2010年,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吳玉虎來到青海進行植物區系調查時,經當地林場負責人指引,發現了這片柽柳原始野生林地。
林地屬同德縣然果村村委會管轄,位于黃河岸邊海拔2660多米的河灘潮濕沙地上,洪水時節,黃河水經常漫上河灘,浸泡林地。
據《中國周刊》報道,吳玉虎在深秋時節來到這裡,“從黃土高坡上下來,燦爛的晚霞照耀着西邊的天空,這片古柽柳就矗立在天地間的一片金黃中……高原的寒風折斷了樹枝、剝開了樹皮,可是柽柳樹幹遒勁,呈現出一種剛勁和蒼涼,顯示着頑強倔強的生命力。”
吳玉虎粗略測量後發現,林中的野生柽柳樹高6-8米,樹幹粗壯,有數百株的直徑在20-100厘米以上,其中幾十株的直徑在100厘米左右,最粗的一棵樹的胸高莖圍逾370厘米,堪稱“樹王”。當地年長居民告訴他,附近村莊1949年後才搬遷至此,村民遷來時這些樹就已經是這麼大了。
這讓吳玉虎感到十分驚異。“因為柽柳一般都是灌木,最多是小喬木,樹徑頂多20厘米,而這片柽柳林裡很多都是幾個人抱不過來的大樹。”吳玉虎說。
環保組織提供的一張照片顯示,兩個成年人在一棵大柽柳樹下拉手圍抱,也僅能圍住樹徑的約二分之一。
由于當時并不能确定該柽柳林的價值,吳玉虎随即聯系了中科院新疆生态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國内著名柽柳專家劉明廷。
劉明廷現場考察後告訴他,自己畢生研究柽柳,從未見過此等規模的柽柳林,并感歎“這是個奇迹”。
“這些野生古柽柳大樹成就了4個‘世界之最’——樹齡最長(100-300年左右);胸高莖圍最粗(376厘米);高度最大(16.8米);野生分布區中海拔最高(2740米以上)。”吳玉虎表示,這片古柽柳林還為國家森林生态系統增加了一個天然的野生柽柳喬木林,柽柳的基因以及它們所記錄的當時的氣候狀況、環境變遷等方面的信息,為了解青藏高原氣候與環境變化提供了最好的科研材料和最直接的證據,“是中國生物多樣性的驕傲和世界自然遺産的标本。”
據《光明日報》此前報道,據悉,直徑在100厘米以上的野生柽柳,單株已屬罕見,何況連片成林,這在世界範圍内也從未有過報道。
吳玉虎分析,或許正是由于當地高海拔、低氣壓、日照強烈、晝夜溫差大等環境特點,還有地處偏僻、交通不便等,為這些野生古柽柳樹提供了避難所,才造就了其成為世界範圍内的“柽柳之王”并幸存至今。
未批先建的水電站
發現古柽柳林後不久,吳玉虎就得知,附近正在規劃建設一座水電站,而這片林子正處在水電站水庫的淹沒區内,屆時古柽柳林将會遭遇“滅頂之災”。
根據水電站環評編制機構、中國電建集團西北勘測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公布的水電站環境影響評價報告草案,同德縣然果村附近的水電站名為“黃河羊曲水電站”,青海省2002年開始立項,由青海省政府委托黃河上遊水電開發有限公司建設。
據上述草案,這座水電站裝機容量為1200MW,工程規模為一等大型工程。其建設是為了“合理開發和有效利用黃河水能資源”、“增加西北電網電力供應,滿足電網用電需求”、“促進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
據環評草案,水電站淹沒區有甘蒙柽柳林51.3公頃,樹徑大于30厘米的柽柳共計666株,“羊曲水電站淹沒區柽柳資源的淹沒,對甘蒙柽柳種群,柽柳屬植物生境、生态系統與景觀多樣性以及對當地野生動植物資源有一定影響。”
這份環評報告并未通過環保部門審批,然而,2010年,羊曲水電站已經開工建設。
2017年,青海省紀委通報了6起生态環境保護領域執紀問責典型案例,第一起即為“羊曲水電站項目未批先建監管不力問題”。通報顯示,2010年6月,該項目在未取得電站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和項目核準相關文件的情況下,在建前施工的同時進行了部分主體工程建設,未批先建長達7年之久。
據黃河上遊水電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下簡稱“黃河公司”)官網信息,2013年11月19日,公司副總經理楊存龍到羊曲水電站建設工地進行了檢查指導,并在導流洞、引水系統和廠房開挖、砂石拌和系統等工程施工現場,聽取相關負責人彙報。
2016年底,有媒體去當地探訪,看到水電站的導流洞已經完工,洩洪洞也幾近完工,而水電站壩肩正在澆築施工中。
當年,這種“未批先建”的行為遭到了青海省生态環境廳的處罰。
青海省生态環境廳2016年公布的一份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針對黃河公司所屬羊曲水電站項目“三通一平”(指水電站前期工程:通水通路通電、平整土地)工程環境影響評價文件未經批準,擅自開工建設,依據《環境保護法》和《環境影響評價法》,對黃河公司罰款20萬元。
截至目前,該水電站的環評依然未通過環保部門的審批。11月29日,青海省生态環境廳辦公室負責人向新京報記者表示,羊曲水電站的環評審批工作由生态環境部負責,省廳不知情。然而,據一位接近生态環境部環評司的權威人士透露,“環評司至今沒有收到該項目的環評報告。”
“沒有通過(審批)。”11月30日,黃河公司一位負責水電站環評公示工作的工作人員亦向新京報記者證實。
移植争議
水電站的建設考慮到了古柽柳林的保護問題。
上述環評草案顯示,由于該區域柽柳林地不僅具有極高的觀賞價值,而且在生物學特征、植物學特征和本身特有的遺傳基因方面具有較高的科學研究價值,因此,“有必要對其采取一定的保護措施。”
保護措施指的是“移植”。《黃河羊曲水電站庫區甘蒙柽柳移植擴大試驗實施項目招标公告》顯示,這片古柽柳将于2016年11月15日開始施工,移植工期為半年,至2018年7月前完成移植及後期養護工作。
為了移植成功,青海省先在小範圍内做了試驗。
青海省政府2016年11月在官網發布的《青海省政府新聞發言人就柽柳保護有關問題答記者問》稱,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黃河上遊水電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先後投入600餘萬元專項資金,委托國家林業局西北林業調查規劃設計院組織實施了黃河羊曲水電站控制流域内柽柳移植先導試驗研究項目,先期在氣候、地貌、立地類型一緻的控制流域外保護移植柽柳25株,“目前全部存活,取得了良好的移植效果和階段性成果。”
此後,原青海省林業廳、國家林業局又組織中國林業科學院、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有關專家,對然果村及周邊甘蒙柽柳林進行了調研,并出具了《青海省同德縣然果村及周邊甘蒙柽柳調查研究報告》。省政府則據此制定了《青海省羊曲水電站拟淹沒區甘蒙柽柳保護方案》(下稱“保護方案”),并于2018年8月對外公布,方案依然是對淹沒區柽柳林進行“遷地保護”。
研究報告認為,“甘蒙柽柳喬木林……在其他适宜的生境條件下,仍然可以長成類似的柽柳喬木林。”
關于移植科學性問題,保護方案編制組成員、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張齊兵在去年8月的發布會上表示,在2015年通過先導移植試驗,對移植的25株第二年之後生長狀況調查,移植的甘蒙柽柳全部成活,且具有根系再生和新枝萌生能力。
這一結論引發不少專家質疑。原國家林業局科技發展中心主任黎雲昆多年來一直關注然果村野生柽柳林的保護進展。11月27日,黎雲昆告訴新京報記者,2016年的移植試驗中,被移植的柽柳裡最大的樹徑長僅為93厘米。
黎雲昆說,移植能否成功,關鍵在大樹、古樹的移植。他去過柽柳被移植後的現場考察,發現越大的樹體,生長情況越差,“直徑93厘米的樹移植後能夠長出新根,不能說明直徑150厘米古樹移植後也能成功,更不能說明可以移植徑長超過200厘米的樹。”
據澎湃新聞報道,北京植物園副總工程師郭翎在實地考察後亦明确反對古柽柳移植,“大樹如果活不了,單算活下來的小樹成活率有什麼意義?”郭翎表示,“當地的土壤特性與移植工期不存在古樹移植施工的可行性,強行移植很可能使這批古樹全軍覆沒。”
吳玉虎則表示,即使移植大樹能夠成活,整片野生柽柳林作為一個森林生态系統的完整性也會被破壞。“生态系統是不可移植的,即使樹木全部移活,也是人工林。”
11月27日,新京報記者緻電負責編制遷地保護方案的中國林科院林業研究所研究員褚建民了解上述争議,褚建民表示自己“正在國外出差”,不方便進一步解釋。
中國工程院院士、林學及生态學專家沈國舫告訴新京報記者,自己并沒有親自考察過然果村的柽柳林,但根據相關資料,從保護生物基因多樣性的角度,他認為這片柽柳林有其“珍貴性”,“比如将來如果要培育更加耐鹽或抗某種病蟲害的柽柳,這片林子裡可能就保存着這些基因。”
至于是否應遷地保護,沈國舫表示自己“不好判斷”,但他認為,一旦移植,肯定會部分損壞“古樹”的完整性,能否移植成活也“是個問題”。
“現在評審通過保護方案的機構,既是方案的編制者,又是評審者,這是有問題的。”黎雲昆表示,“國家林業局已經認可了這個方案,而參與方案編制的西北林業調查規劃設計院是它的下屬機構,這種情況很難保證方案的客觀性。”黎雲昆認為,如果要出具一個經得住曆史檢驗的保護方案,應該由國家環保部門組織意見不同的專家共同調研、編制方案,而非由國家林業局或青海省政府組織。
不僅是科學問題
除了移植方案,業内專家還對古柽柳林的諸多科學問題存在争議。
比如樹齡問題。保護方案認為,經過抽樣調查,柽柳林中樹齡為20-40年的樹木最多,超過100年的樹木為極少數,目前隻發現兩棵,其中一株已經倒伏,另一株樹心已腐爛,沒有發現超過百年健康生長的樹木。這意味着,在官方看來,這片柽柳林的保護價值已經“大打折扣”。
“保護方案關于樹齡的認定壓根站不住腳。”11月23日,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态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潘伯榮告訴新京報記者,方案編制者的樹齡測定方法并不科學,所測樹齡也不準确。
潘伯榮曾在2010年8月25日-31日率隊到然果村柽柳林實地調查,發現了1株樹徑約1.45米、已經被人砍伐的柽柳古樹,測算其樹齡為102年,因此,他将标記的365株甘蒙柽柳中樹徑大于1.4米的植株定為“百年古樹”。在他考察中,共有203株柽柳達到這一标準。
根據相關認定标準,樹齡達到一百年的樹可稱為“古樹”。2009年國家林業局發布的《關于禁止大樹古樹移植進城的通知》規定,對古樹名木、列入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名錄的樹木、自然保護區或森林公園的樹木、天然林木……其他生态環境脆弱地區的樹木等,禁止移植。
青海省林業局認定的“古樹”隻有兩棵,黎雲昆認為,保護方案是在回避古樹保護的政策問題。
黎雲昆曾在一次環保沙龍上表示,保護方案的重點是古樹的遷移,拟淹沒區到底有多少古樹,這是決定保護方案是否可行的重要依據,“你要遷移必須把底數摸清楚,底數不清楚就說可以遷就太随便了。”
就上述質疑,新京報記者緻電保護方案編制組負責樹齡檢測的專家、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張齊兵。張齊兵表示,在去年青海省政府組織的一次交流會上,反對“遷地保護”的專家已經和他“充分交流”了相關問題,他在會上已做出回應。至于具體看法,他需要征得所在單位同意才能對外回應。
黎雲昆回憶,在那次座談會上,他曾當面就保護方案中關于古樹樹齡的認定提出質疑,但張齊兵表示,檢測結果沒有問題,是“零誤差”的。
多年的争議下,水電站建設曾在2016年暫停過。當年11月,青海省政府宣布,在保護方案确定前水電站不得蓄水,暫停古柽柳林移植。但2018年8月,上述保護方案公布後,這一工程再次啟動。
田紮西告訴新京報記者,由于修建水電站,然果村已經進行了移民搬遷,大部分村民都去了周邊縣城居住,政府也發放了相應的補償款,但仍有部分關心柽柳林的村民不同意移植,其中就包括他自己。
田紮西表示,自己不同意移植與補償款無關,而是由于自己已經守護柽柳林長達13年,在他看來,林子裡的樹們屬于“古董”,讓他難以割舍。
采訪期間,多位專家告訴新京報記者,青海柽柳林保護問題争議至今,已非單純的科學問題。
吳玉虎回憶,去年,青海省生态環境廳等部門曾組織意見不同的專家和黃河上遊水電開發公司召開過一個讨論會,會上,他提議是否可以想一個兩全辦法,既讓水電站建設,也不用對柽柳林進行破壞性移植。
“比如是否可以把大壩降低20米,這樣柽柳林就不會被淹。”吳玉虎提議說,但水電站負責人告訴他,即使隻降低兩米,水電站也會損失大部分發電量,建水電站将沒有意義。而水電站目前的投資已超過60億,項目一旦擱淺,誰來承擔損失會是另一個問題。
近日,就移植方案、未批先建、保護方案編制評審機構公立性等争議,新京報記者多次緻電、發函至青海省林草局詢問看法,截至發稿,未獲回複。
A特06-A特07版圖片/受訪者提供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