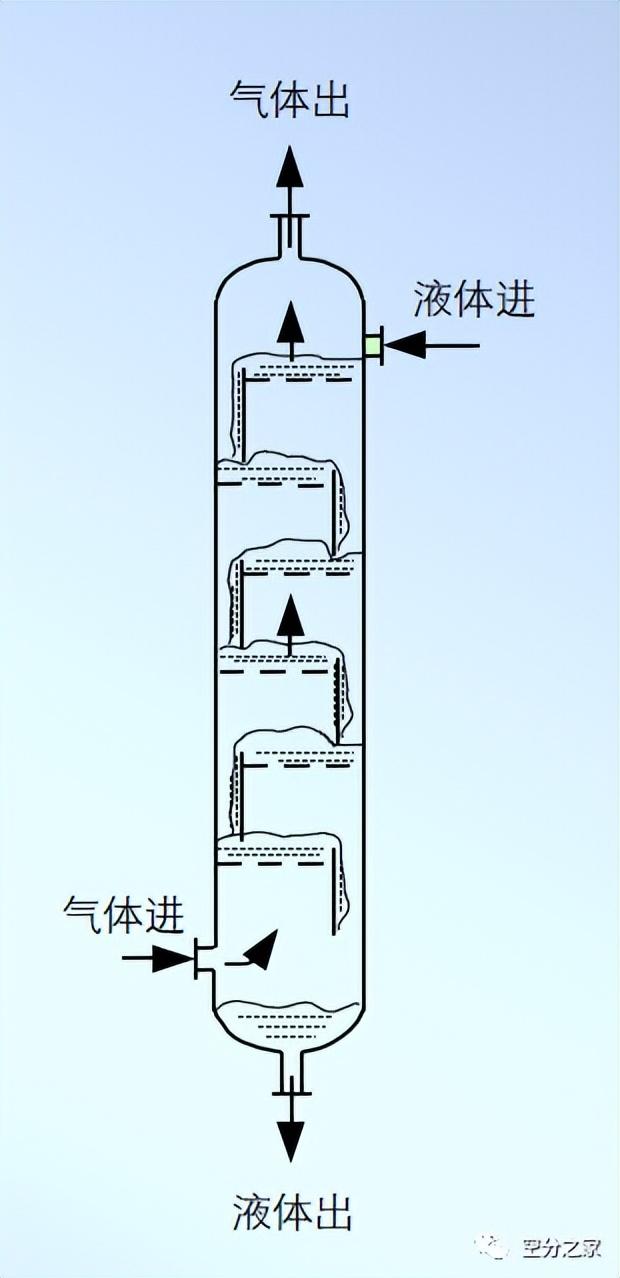口述:阿威(廣西柳州人)
撰文:胖爺
我從未想過,會進入一家内衣廠。當然,光從工廠的名字,實在看不出來,這是一家生産女性内衣内褲的企業。工廠的後綴名,是制衣廠,這給了我迷惑。
我在老家學過車縫,這算是一門技術活。有了一技傍身,我想我能在深圳安身立命。所以,南下之初,我是抱着進制衣廠,或者與車縫相關的工廠的。然而,事不湊巧,或者,說這是命運使然,反正,我來到了公明。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并不知道公明有着内衣生産基地之稱。我來公明,無非是因為小妹也在這裡。
小妹在上村一家電子廠,管理公司的财務。原本,我也可以進電子廠,但一來,我不想沾小妹的光,我總覺得憑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在深圳立足。二來,小妹所在的電子廠,規模不大,是小廠,工資不高。更何況,我是有技術的,不能荒廢。
于是,找了幾天,進了合水口一家内衣廠。當然,我講過,進廠前,我并不知道,廠裡的主打産品是内衣。若知曉,我怕心裡多少有些害羞,應該會另謀他職。但我這人呢,又有點奇怪,一旦辦理了入職手續,知曉了這一事實,又不願再更換。

我相信命運,我覺得這是我的命運。不過,在内衣廠上班,對于我這麼内向的男子來說,實在是無法輕易說出口的。
因此,每每與同鄉聚會,問起彼此之間的工作,我總左右而言他。實在避開不了,便以制衣廠搪塞之。但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我在内衣廠上班的事,不知怎麼,到底傳了出去。傳出去便傳出去罷,我不偷不搶,沒什麼好丢臉的,何況,我技術好,活兒精,在廠裡得到了主管的充分肯定。
内衣廠,其實包括所有的制衣廠,幾乎全是計件算工資的,幹得快,不良品少,工資就高。我一步一個腳印,前幾年,最高的工資曾經突破過一萬元。
我知道,這點工錢在深圳,根本不算什麼。但我出身農村,沒什麼學曆,隻有這門技術,這工資全是我的打拼所得,用汗水換成的成績,我很知足。
我剛進廠裡,内衣廠幾乎全是女工,男生很少。現在,情況不同了,男女比例變成了五五開。甚至,個别部門,女工沒有幾個。
最開始那幾年,因為男工少,我們幾個有限的男孩子,有種抱團取暖的感覺。畢竟,在内衣廠上班,天天接觸這些東西,女生又大膽開放,講出來的許多言辭,讓你覺得實在過于熱情了。加之,那時,我還算年輕,未經世事,尤其剛進廠那一段時間,每每見到那些女工,對她們的調侃,常常臉紅。
我們幾個男工友,住在一個宿舍的七八個人,成了很好的兄弟。他們每個人的故事,都可以寫成一篇文章,都有許多令人回味無窮的意味。
其中,睡在我下鋪的,來自江西,我喊他遊哥。遊哥比我大五歲,在内衣廠的崗位,是定型工。内衣廠有原材料,到産品成型,總共有十幾道工序。包括撚線、針織、繡花、染整、加工成品、附件到輔料等等。
遊哥所做的定型工,其實相當于塑料廠的沖壓工。他的工作說簡單也簡單,就是将超高溫度的内衣布料放進模具中沖壓成型。遊哥比我早兩年入職内衣廠,談了個四川的女朋友。他這個女友,在西鄉上班,我還見過一面。

有一回,她來公明找遊哥。遊哥把我也喊了出去,我們仨一起吃了一頓飯,其間,他們談了一些話,具體什麼我忘了,因為那天喝了一點酒。我不善飲酒,一杯啤酒都感覺吃力。
那時,遊哥和女友已經一個月沒見面了,按理講,他們應該小别勝新婚才對。結果,吃完那餐飯,遊哥便以我醉了為由,要送我回廠,然後把女友哄了回西鄉。為此,我一直心存愧疚,覺得是我破壞了他的好事。
直到有一天,遊哥才對我坦白。原來,他在廠裡天天與内衣打交流,工作中,每天要“摸”内衣,摸了無數次,慢慢地對女友産生了免疫心理,沒有感覺了。我記得我當時聽了覺得蠻搞笑,不過事後想想,又覺得悲痛。
現在回頭再反思這件事,我更多地從産業,從整個制造業,從人性關懷的角度來思考。也許,錯的人不是遊哥。不過,就好像村裡人對我的态度一樣,遊哥的女友也無法理解他。不久之後,他倆正式分手。從此,各奔東西。
也是在那一年底,遊哥離職了。離職前,他請我吃飯。那時,經曆了一些曆練,我已經稍稍能喝一點酒。但我隻是陪酒,慢慢飲,遊哥則是狂飲,他是抱着必醉的心态去的。結果,當然大醉而歸。而他的醉言中,一個勁地勸我離開内衣廠。講着講着,他的臉上,慢慢流了一臉眼淚。
遊哥離開後,我原本動搖了,正在舉棋不定時,我被調了崗。實際上,相當于升遷了。因為我辦事踏實認真,南下前曾學過一段時間的繪畫,有些功底,車間主管找了談話,升我為畫圖師傅。
畫圖師傅工作更輕松,實際上,還有點相當于設計師的角色,參與産品研發了。工資漲了,條件輕松了,我自然留了下來。誰曾想,那年春節回家過年,我身上多了一個标簽:内衣畫師。

這個稱呼多少帶着調笑的意味,以至于妹妹私下裡,寫了一張紙條,讓我回深圳後,趕緊離職,換新工作。到了深圳,她真的行動了,請人事主管幫忙,幫我在電子廠物色了一個倉管員的職務。
人事主管是個中年男人,幾次三番約小妹看電影,她一直拒絕了。但為了我,或者說,村裡人的背後指點,讓她也不堪重負,于是她想法子,讓我離開。為此,她甯願作些犧牲。我感謝小妹的付出,但我沒有同意她的建議。
我留在了内衣廠,别人怎麼說,與我無關。我是在那件中秋節之後離開的,但我的離開,與小妹無關,而關乎一個女子。
女孩叫阿麗,也在内衣廠,負責成員檢測。之前,遊哥說他每天“撫摸”廠裡的各式内衣,對女友沒有念想。阿麗則每天經手的内衣更不可計算,她在這行當四五年了。
她也是四川人,為人體貼大方,尤其心善,這樣一個好女子,竟然沒有談過男友。實在因為内衣廠男女比例不匹配,換成别的工廠,她這樣的女子,早就名花有主了。我們在一起後,她曾開玩笑地說,她之所以沒談朋友,因為她知道我會來找她。
她是個鬼怪精靈的女生,我承認我是幸運的。不過,即使是這樣溫柔懂事的女生,也在勸我離開内衣廠。也許,她覺得内衣廠女生多,也許,她覺得天天對着女性内衣,我也會變成下一個遊吧。
麗是在紅花山公園對我講這番話時,那天晚上,廠裡不加班,我倆乘着夜色在微風中漫步,手牽着手,走到公園的一處僻靜處,她主動拉我停步,偷偷地給了我一個吻。那是我至今想來仍無比甜蜜的吻。
後來,很多次的親吻,再也沒有了第一次的被觸電的感覺。然而,也隻是一個吻罷了。因為,我是膽小的,而且在公園那樣的地方,人來人往,我實在害怕被人看到。當然,那時也毫無經驗,不知如何下手。

正是我的舉止,讓她認定,我是值得托付終生的人。因此,她鄭重其事地對我提出,我倆一起離開内衣廠。我問她為什麼,她沉默了許久,才說,我不願意你每天面對不同的内衣,我隻想讓你看到我。
我問,看到什麼?她說,看到我的……一切。
我答應仔細考慮。但我還未作出決斷時,她卻突然回了一趟老家。那時,通訊遠不如現在發達,我們都沒有手機。我在内衣廠一直等她,可等了許久,再未等到她的到來。
我被相思折磨,熬到年底,辭了工,回家過年。過完元宵,我再度返回深圳,但我沒去内衣廠,在小妹的幫助下,盤下了她工廠外面的一家小店。從此,再未進過工廠。
而我與阿麗的交往,除了那個吻,什麼都沒有留下。
每個人的故事,都值得記錄。每個人的經曆,都是時代的一部分。三驚胖爺專注于非虛構紀實,歡迎提供采訪線索。如果您想分享自己的經曆,歡迎聯系胖爺,我們一起記錄曆史。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