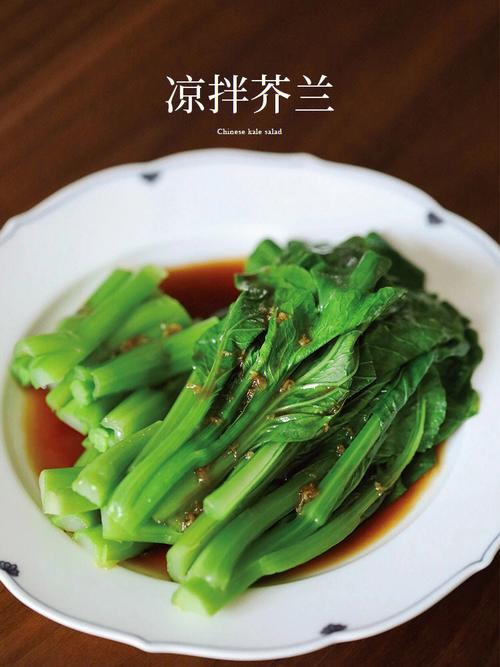印象派這詞,最初是用來罵人的。
如今所說的印象派,最初核心小圈子,由莫奈、雷諾阿、西斯萊與巴齊耶四人組成:莫奈與雷諾阿是兩個窮小子,1860年代初二十出頭,在巴黎一度靠蹭飯為生。雷諾阿多年之後老了,還說多虧莫奈年輕時喜歡穿得花裡胡哨,他倆就靠一身衣服撐門面,跑别人家去蹭飯,吃雞、喝香貝坦紅酒,快活似神仙……
莫奈與雷諾阿二位當時的創新,一反學院派新古典作風的素描作風,也懶得塑造所謂理想美,而熱衷于戶外繪畫:
把握光影空氣情景,用迅速的筆觸描繪。
他們都被法國上頭的組織——也就是沙龍——相中過,但他倆還是過着離經叛道的人生,所以後來又被沙龍排斥了。
印象派的其他名家如畢沙羅、塞尚與德加們,則是後來加入的:本來,他們與莫奈、雷諾阿不是一個世界的人。隻是年紀相仿,又都挺有叛逆精神。
這裡埃德加·德加很有意思:他大莫奈六歲,有錢家庭出身,早年科班裡學過,不像莫奈與雷諾阿,初到巴黎時,還是野路子。
德加很推崇莫奈式的迅疾筆觸,但對莫奈與雷諾阿的絢麗光影,興趣就小了。
當莫奈與雷諾阿兩個窮孩子跑出門,到處描繪花園野地、浴場河流這些不要錢的風景時,德加卻請得起芭蕾舞演員來給他當模特。能跑去美國,住在新奧爾良,舒舒服服地畫畫。

1873年,莫奈公開呼籲:應建立一個新的藝術家團體,獨立于學院派之外——當然沒人聽啦。
于是,莫奈們決定自己動手了。
也就在這年,雷諾阿的兄弟愛德蒙負責整理展覽目錄,跑去跟莫奈念叨:
“你這都什麼畫名?《村裡》、《出村》、《勒阿弗爾的風景》?你不能起個好聽的名字嗎?”
莫奈:
“那,最後這幅,改叫《印象》怎樣?”
愛德蒙:
“還是叫《印象·日出》吧!你們畫家呀,真不會起名字!”

1874年春天,在巴黎市卡皮西納大街35号——那裡曾是攝影家納達爾的工作室——第一次印象派畫展開始。當時自然引來了各色争議。
一種流行的說法是:
“這批人就是把幾管顔料裝進槍膛,轟兩發上畫布,簽個名——這玩意也叫做畫!”
前輩評論家路易斯·勒魯瓦先生舉着莫奈的《印象·日出》,嘲諷說這批人也算個派,就叫“印象派”吧。
從此才有印象派這個詞,罵人用的,不小心就此命名了一個時代。
當然,後來印象派成了,于是也就留名曆史了。現在說起印象派,大家就想起莫奈的睡蓮和麥垛、雷諾阿的浴女、畢沙羅的風景畫,等等等等。
但您也看到了,印象派這名字,最初是罵人用的;泛指的是這麼一個小團體。
哪怕這個小團體中,并不是每個人都按一種畫風來。
1874年之後十二年,類似展覽陸續開了七次,到20世紀,莫奈與雷諾阿活着看到自己成為傳說,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國家收藏。多年後聽來,這是藝術史上最傳奇的故事:一群外來青年,以民間印象派對抗學院派,從此永久改變了世界對藝術的欣賞眼光。
但其實又有不同。
比如畢沙羅将年輕的修拉和西涅克引入了這個團體,修拉挺崇拜莫奈,但莫奈并不算喜歡修拉:
修拉研習過安格爾的畫,曾分析過德拉克洛瓦的筆觸,佩服莫奈對光與色彩的理解;人研究了謝弗雷的光學著作,決定“更理性、更科學地描繪光”,不用線條,不用塊和面,而用色點來創造畫作。
而莫奈覺得修拉太理性太科學了,莫奈自己喜歡的,可是“畫親眼看到的東西”呢。

至于同為印象派代表的德加,後來也終于走了另一條路。1876年,有位評論家認為,德加和莫奈看似處于一個畫派,其實各執一端。他将德加比作學院派大師素描之王安格爾,而将莫奈比作德拉克洛瓦。
後來羅伯特·戈登先生更說:
“德加似乎在刻意将自己與莫奈分開,而且會嘲諷莫奈那種在戶外繪畫的作風。”
1882年,大城市人德加去到海邊的埃特雷塔:那裡有天然生成、鬼斧神工的白垩懸崖,最有名的莫過于水流制造的的三個拱孔。
然而德加沒在那裡作畫,卻留下了這麼句話:
“我眼睛可受不了這個,這種光線更适合莫奈。”
所以咯,雖然同是印象派的,其實都不一樣。
甚至繪畫史上公認為所謂“後印象派”三傑的塞尚、高更和梵高,其實也大不相同。
保羅·塞尚生在普羅旺斯的埃克斯,并在那裡長大。普羅旺斯啊,陽光、大蒜、牡蛎、甜酒、薰衣草的世界,埃克斯更是時時沐浴在陽光中:那地方不大,你在哪裡,都看得見1011米高的聖維克多山。
塞尚去巴黎闖蕩了幾年後,回到了普羅旺斯埃克斯,繼續畫他的聖維克多山。印象派熱愛的是光線,可是塞尚公開說“線是不存在的,明暗也不存在,隻存在色彩之間的對比。物象的體積是從色調準确的相互關系中表現出來”——他當然有資格這麼說,因為在普羅旺斯的陽光下,一切都明亮而濃豔。在他的窗口,塞尚不停地畫聖維克多山,直到花甲之年依然不停。
很多年後,畢加索代表他那代人說:“塞尚是我們所有人的父親。”

高更則去了塔希提,抛棄了歐洲已有的一切技巧,畫他的塔希提。他的故事如此傳奇,毛姆還以他為原型,寫了那著名的《月亮與六便士》。

梵高在1886年到巴黎接觸了浮世繪後,熱愛上了日本大師歌川廣重的《東海道五十三次》,于是跑去阿爾勒,用華麗的筆觸表達奔放的情感。1888年2月19日他給高更寫信:
“我永遠不會忘記初到阿爾勒之日的情感。對我來說,這裡就是日本。”他念叨“你隻該學會描繪草,然後是所有植物,然後是所有風景、所有的動物、最後是人物形象。你就做着這一切,度過一生。要做這一切,一生都還太短。你應當像畫中人一樣,生活在自然裡,像花朵一樣。”

您一定發現了,這大概就是标簽的荒誕:
明明風格完全不同,隻因為某一段時刻聚在過一起,便會被貼上個标簽,一起挨罵。
久而久之,隻要闖出來了,罵人的标簽也就成了曆史名詞,然後稀裡糊塗歸了包堆,就擱一起了。
類似的荒誕,海明威也遇到過。
現在文學史說海明威是所謂迷惘一代lost generation的代表。
這詞怎麼來的呢?
1920年代,海明威在巴黎。比海明威年長的女作家格特魯德·斯泰因,也住在巴黎,算海明威的前輩。這位博學的女士一度是海明威的好朋友。
某天,她跟一位修車青年鬧點不愉快,就倚老賣老地對海明威說:
“别跟我争辯,你們就是迷惘的一代。”
身為剛經曆了一戰,一向自覺嚴以律己的海明威,自然覺得這話不能接受:說着修車的人呢,怎麼就忽然給我栽上了?
他想:明明每一代人自有其迷惘啊。
所以,憑什麼我們就迷惘的一代?
憑什麼上一代人,就給一代人下結論了?
“那些輕率的标簽,還是都見鬼去吧!”
諷刺的是,後來海明威出版《太陽照常升起》時,扉頁提了斯泰因這句“迷惘的一代”。本來他覺得“迷惘的一代”這詞太扯了,所以要“太陽照常升起”——他本來預想的書名叫《嘉年華》。
結果這本書大紅,連帶“迷惘的一代”也成了曆史名詞。于是文學史就說海明威是迷惘一代了。
本來海明威反感這标簽,結果自己還被安上了!

要到三十多年後,海明威在《流動的盛宴》裡,才一字一句前因後果解釋清楚:
我本來就不喜歡這詞,覺得這就是個輕率的标簽!——但那時已經晚了。
XX一代或者XX派,雖然粗暴,但至少還有點特色。
最簡單粗暴的标簽,自然是按年齡劃分。七零八零,九零零零。
我十幾年前跟人開過玩笑:大仲馬和雨果1802年生,所以算1802一代?波德萊爾和福樓拜1821年生,所以算1821一代?巴爾紮克1799年生,好嘛,這就沒法當1800一代來吹了……
您一定明白這玩意有多荒誕了。
貼标簽這事最殘忍的是,經常是單方面的打壓,很論資排輩。
上一輩可以對下一輩随意指點江山,下一輩隻能先受着;又趕上上一輩往往比下一輩偏保守又正好占據主流,所以往往要認定下一輩不夠持重。
我還記得90後當年,被貼過“肥豬流(非主流)”的标簽,細想來這說法相當有惡意,但人誰沒年輕過呢?年紀輕輕就一本正經的又有幾個呢?那樣真的好嗎?
所以咯,上一輩給下一輩定義的标簽,多半是不成熟的,簡單粗暴的提前判決。
動不動就一句話否定一代人,本質上,是居高臨下的規訓與服從。
而下一輩要過許多年,得到話語權,才能回頭反抗。
雖然多少能扭轉一些話頭,甚至讓一些最初的貶低詞彙改變其意味完成大逆轉,但總歸還是有點不爽的,對吧?
哦對了,順手推一下我翻譯的《流動的盛宴》。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