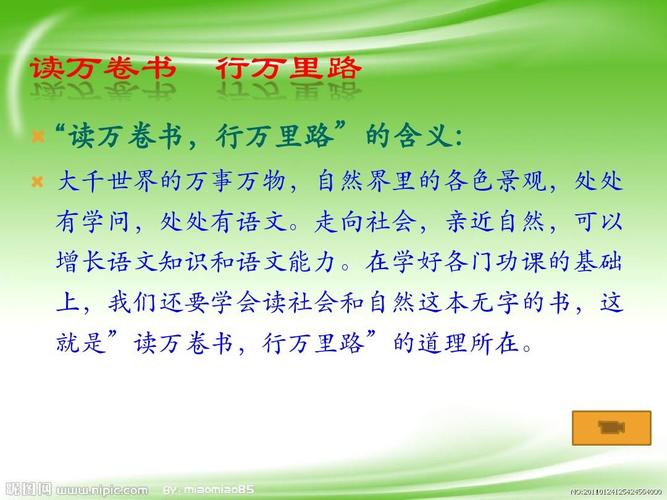2020年的夏天,
五條人陡然走紅,
如同一場沒有Action的電影,
突如其來,如夢如幻。
但阿茂肯定,那不是一場夢。

(仁科)漸變真絲襯衫、紅色西裝、紫色西裝長褲
均為BERLUTI
暗紅色皮鞋 TOD'S
(阿茂)藍色提花羊毛連體衣、暗紋西裝長褲、綠色皮鞋
均為PRADA

這支著名樂隊在現實中受萬人追捧,但在阿茂的夢裡卻前所未有地遭人嫌棄。沒有人在乎他們是誰,樂手們被罵得灰頭土臉。就在他們準備離開時,人群裡突然有人舉着大喇叭喊了一聲“咔!”原來一切都是導演的安排,樂手們不知道,從他們進門那一刻起,故事已經開始。
從某種意義上說,阿茂夢裡這場毫無預兆的拍攝與五條人的現實遭遇有着某種奇妙關聯,像是夢與現實的正反兩面——2020年的夏天,五條人陡然走紅,如同一場沒有Action的電影,突如其來,如夢如幻。
但阿茂肯定,那不是一場夢。
五條人走紅之後,他們的生活并無太多改變,除了工作比以往繁忙些,最明顯的變化,大概是在那個夏天之後,他們因為在北京過冬,第一次穿上了秋褲。阿茂去逛街時,不再穿拖鞋。
前段時間,五條人發布了兩張新專輯:《活魚逆流而上,死魚随波逐流》和《一半真情流露,一半靠表演》。專輯錄制過程是五條人專輯錄制史上最享受的一次。從前他們錄制專輯,為了省錢,會提前将所有内容編排好再進棚錄制,但這次不同,所有人都放開了玩音樂。錄制《活魚逆流而上,死魚随波逐流》時,仁科隻帶了歌詞進棚,旋律和編曲是大家在錄音期間花三個小時即興完成的。

(仁科)漸變真絲襯衫、紅色西裝 均為BERLUTI
(阿茂)藍色提花羊毛連體衣 PRADA
“即興”一直以來都是五條人音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你能夠在這支樂隊的演出現場,看到他們與各類藝術家的即興合作。詩人方閑海曾評價五條人是“天生的音樂即興高手”。在傳統觀念中,人們通常認為即興音樂需要極其豐富的樂理知識和精湛純熟的技術,但在五條人看來,所有嘗試——哪怕帶着某種“瑕疵”,也會為探索音樂帶來更多自由和可能性。他們選擇用即興的方式創作,其實也是在避免“重複無聊”。
這一次錄制新專輯,五條人邀請到管樂演奏家張夢和傳奇搖滾樂隊“木推瓜”的貝斯手陳創遠加入。張夢在錄制完成後,稱五條人這兩張專輯是迄今為止全世界樂隊專輯中用到笙這件樂器最多的專輯。他記得錄音期間仁科和阿茂兩個人經常為作品而吵架,吵得很兇,但兩人都不記仇,完全不影響排練,這一點倒是貼合笙的氣質——“笙在古代被稱為‘和’,和而不同,有意思。”

采訪時問五條人,生活中有沒有哪些即興的時刻?阿茂從桌上拿起一罐啤酒說:“我現在即興喝口啤酒吧。”早些年,阿茂酒量不是很好,喝點兒啤酒就暈,後來開始做音樂,因為演出之前會緊張,他就嘗試喝幾口酒再上台。有時候巡演很累,酒精會讓人興奮,現場演繹的狀态更好。慢慢的,拎着酒瓶上台成為了一種習慣。
五條人的音樂現場總是少不了酒精的刺激。有一次在北京樂空間演出,他們喝得太開心,一直返場加演,演出整整持續了三個小時,返場四次,唱了七首歌,到最後所有人都喝斷片兒了,甚至忘記自己唱過什麼。
平時與朋友們喝酒時,喝多了他們也不吵不鬧,感覺自己喝大了就悄悄走掉。有次阿茂和頂樓馬戲團的貝斯手梅二一起喝酒,喝到一半人不見了,梅二四處尋找,最後發現阿茂趴在一個房間裡睡着了。

撞色針織衫、灰色斜紋長褲 均為EMPORIO ARMANI
仁科常在喝多時假意接電話離開,有次被人發現手機屏還是黑的。還有一次他和一群人喝酒,感覺自己馬上要倒了,決定先行撤退,手機也沒帶。其他人喝着喝着發現仁科不見了,給他打電話、發微信均無回複,最後調監控找人也不見蹤影。“我剛好在他們調監控的時間點之前走的,所以他們看不到我。不過想想那次,我其實也挺不負責任的。”
聊起喝酒往事,仁科想起五條人的一位老朋友——音樂人楊海。楊海是湖南人,曾在廣州漂泊過一段時間,一次在買打口CD時與阿茂相識,後來成為朋友,有段時間住在仁科那裡。楊海在做飯方面是一把好手,總能花最少的錢做出一大桌子菜。“毫不誇張,給他20塊錢,他能做出夠10個人吃的飯,有菜有肉還有酒,管夠,多牛逼。”
仁科記得,當時他們住的石牌村有人賣高度白酒,四塊錢一斤,酒很烈,極難入口。楊海發明了一招:把蜂蜜兌到酒裡喝。阿茂喝過一口便不再嘗試,“太難喝了。”但仁科喜歡甜味,覺得還不錯。那段時間,仁科和楊海兩個人日日在天台上舉杯對飲,隻喝今日酒,不問明日憂。直到有一天家裡來了一位朋友,那人問道:“你們這酒是哪裡打的?”得知地點後,那人說:“他那裡賣的都是假酒,兌工業酒精的。”從此,仁科再也沒喝過那款酒。

黑色桑蠶絲圓領衫 GIORGIO ARMANI
暗紋西裝長褲、紅色皮鞋均為 PRADA
黑色皮帶 BERLUTI
銀色戒指 KVK
聽五條人的歌也常有一種醉酒之感。他們曾在《像将軍那樣喝酒》中唱道:“我要像将軍那樣喝酒/上班的時候喝/我管它叫上瘾/行房的時候喝/我管它叫過瘾”。錄制《地球儀》和《食醉狗》那天,五條人喝光了一瓶威士忌。《地球儀》錄到後面,所有人都喝大了,仁科扯着嗓子嘶吼:“我想今夜我喝多了/不過話又說回來/為什麼你還是滴酒不沾/為什麼你還是鐵石心腸”,這首大時代情歌最後在撕心裂肺的酒氣中落幕。
《食醉狗》唱到第四分鐘,出現摔醉酒瓶的聲音。這首歌在五條人過去演出時曾與許多音樂人合作過,專輯中的版本是和即興前衛吉他手李劍鴻合作的。在阿茂看來,與不同的音樂人合作《食醉狗》會呈現出不一樣的醉酒狀态,有時是“微醺”,有時是“喝大了”。他心裡有一個“食醉狗計劃”,打算未來邀請不同的音樂人一起來玩這首歌。
仁科開始幻想這首歌合作名單上的人:“左小祖咒、易烊千玺……我們挑四個字的名來說——歐陽娜娜還有鳳凰傳奇,再加一個國外的大衛·林奇,我覺得可以,這絕對好!”他忍不住笑起來,“哈,如果要跟這幾個人合作,這首《食醉狗》就要改名叫《食醉狗狗》了。”

采訪中途,阿茂因為有事先行離開,後來與他單獨約了一次電話專訪。阿茂走後,屋子裡隻剩下仁科一個采訪對象,他笑稱這是“分開審問”。仁科不喜歡電話采訪,有陰影。有次跟一位記者電話聊天,聊了很久,說了很多話,對方一直沒回應,仁科覺得不對勁,看了一眼手機,發現它不知什麼時候關機了。“但我已經過了那個feel了,也不打算把它打開,就繼續走。”
時機很重要,感覺很重要,這東西說來就來,有時候非常猛烈,過了勁兒又蕩然無存。
早年間,仁科曾與記者講起他和一個哥們兒去廣州東站幫阿茂取自行車的經曆。當時阿茂和幾個朋友去外地騎行,寄回四輛報廢的自行車交給仁科,仁科和哥們兒一人各踩兩輛,一路從東站騎回石牌村。他當時說以後要把這個故事拍成電影,而如今故事已經擱淺。
前幾天,仁科突然來了靈感,想到一個新故事,立即拿筆将梗概寫到紙上,打算以後用低成本的方式把它拍出來。他對這個故事十分滿意:“創意非常好!拍出來絕對好看!”以前仁科總覺得要先把一個想法琢磨透再去思考其他,但現在他不這麼想了,決定先多想一些故事,到時候再看哪一個時機成熟就拍哪個。阿茂感歎仁科經常變來變去,“他有無數個idea,有無數個故事要拍。”

(仁科)綠色真絲襯衫PRONOUNCE
黑色西裝褲SANKUANZ
黑色皮短靴TOD'S
(阿茂)藍紫色真絲襯衫PRONOUNCE
暗紋西裝長褲、紅色皮鞋均為PRADA
黑色皮帶BERLUTI
銀色項鍊、銀色戒指均為KVK
仁科點子很多,所以在五條人的現場總能看到一些有趣的場面。一次五條人去西安演出,唱到《熱帶》時因為歌詞裡有提到地下賭場,剛好舞台旁邊有個麻将桌,他們就把麻将桌搬到舞台上,請了幾個朋友在台上打麻将;有次巡演到蘇州,碰巧趕上平安夜,他們便讓鼓手扮成聖誕老人,樂隊唱着Jingle Bells,鼓手在一邊給歌迷派糖;還有一次在衢州參加音樂節,五條人返場表演時拉了一隻羊駝上台唱完了最後一曲;2020年去阿那亞演出,他們又把專輯中的“夢幻麗莎發廊”搭建在海邊,并請來了一名專業的理發師傅。
2021年8月,五條人推出兩支“電影預告片”,很多人以為他們真的要拍電影了,結果發現沒有電影,隻有兩張“電影原聲大碟”。“沒有電影的電影原聲”,這個點子也來自仁科。
他有個朋友叫胡向前,是個行為藝術家,胡向前有個作品叫“向前美術館”——以身體為建築,記憶為空間。這個“記憶空間”裡收藏着許多胡向前認可的作品,他通過“述說”的方式将這些作品展示傳播。向前美術館裡有位藝術家,如果想要購買他的作品,所有合約都是口頭簽訂。

(仁科)綠色真絲襯衫 PRONOUNCE
(阿茂)藍紫色真絲襯衫 PRONOUNCE
暗紋西裝長褲、紅色皮鞋 均為 PRADA
黑色皮帶 BERLUTI
仁科還聽說有位藝術家做“隐形雕塑”,作品名字、尺寸、材質、相關介紹一應俱全,唯獨沒有實體,買家付款後可獲得一張藝術家的真品認證書,由此證明這件雕塑作品确實存在。
他覺得這太有意思了,并受這種觀念藝術的啟發,想到了沒有電影的電影原聲。“大家在聽我們唱片的時候去構建一部屬于他們的電影,我們已經提供了海報、演員、預告片和電影原聲,該有的都有,至于成片,你讓大腦自己播吧。你的大腦裡面有個電影院,就好比我朋友的大腦裡面有個向前美術館。”
那麼,五條人未來到底會不會拍電影?阿茂和仁科的回答都是“有可能”。但拍電影也要看時機,他們目前還在準備和練習,等待時機成熟。有人看過五條人的電影預告片後,表示想投資他們拍成真正的電影,仁科講述這件事時還不忘調侃《嘉人》:“到時候有資格當你們的封面人物了吧?”

阿茂和仁科生長于廣東海豐,那裡民風彪悍,出産過土匪和革命家,被他們稱為“全中國最吵的地方”。
阿茂小時候經常從村頭跑到村尾,玩膩了就跑到山頂待着。《童年往事》中的“吃碗雲吞/揮下賭攤”和《莫怪你老爹》中的“跑到山頂哦/偷摘積潮的荔果”都是兒時難忘的畫面。
他自小無拘無束,長大後也喜歡到處跑,在旅行中經曆過許多奇妙的瞬間。有一次在摩洛哥,他住在半山腰的酒店,傍晚穆斯林的禱告聲從酒店周圍的喇叭裡傳出來,一圈一圈擴散,衆聲合奏,蕩漾山間,很美妙,很震撼。
去塞爾維亞時,他在庫斯圖裡卡搭建的木頭城裡看到一個賣紀念品的小販,頭戴一頂鬥笠,嘴裡叼根雪茄,無所事事地賣東西。阿茂覺得那人很酷,開始幻想他是不是庫斯圖裡卡。
還有一次在泰國清邁,他騎着摩托車穿街過巷,因為是左車道,行駛不習慣,誤入了一條單行道,被警車直接拉進旁邊的警察局,交了三百塊罰款。阿茂後來把這段經曆寫成了一首歌,名字就叫《左車道》。
聊到與音樂有關的話題,阿茂的話會明顯變多。他回憶第一次接觸搖滾樂的經曆,15歲那年聽到鐵風筝的《這個夏天》,被深深震撼了——“我病了/我要死了/我老了/我膽小了……就是歌還能這麼唱?那種歇斯底裡,我完全被震住了。”從此,阿茂沉迷于搖滾樂。
談話間,他講起自己以前很喜歡的一位搖滾音樂人王磊,開始回憶早些年聽王磊的日子,滔滔不絕。“你看,我跟你聊王磊都聊了十幾分鐘了,他太酷了。”
仁科更熱衷于跟人探讨文藝和哲學,聊時間,聊空間,聊外星人,聊動物的語言,聊形而上觀念。十幾年前,他與朋友聊時間,以楊貴妃舉例,證明線性時間不成立。他伸出手指在椅面上畫出一道線:“我們畫一條線來表示一個人從生到死,但我認為,線性時間是不成立的,楊貴妃從生到死就是一個運動的過程。”

藍色提花羊毛連體衣
暗紋西裝長褲、綠色皮鞋 均為PRADA
他又從果盤中拿出一瓣蘋果放到圓椅中間,繼續解釋:“就像我把一個水果放在這裡,它即便不動,兩三天後還是會腐爛,因為它内部一直都在不斷地運動。所以在我看來,時間就是一個運動的過程,就算你不動,你的器官、細胞、細菌也在動。我們會幻想用時光機回到過去,因為一直理解的都是線性時間,而一旦否定了線性時間,這個‘回去’也就不成立了,甚至根本不會考慮有沒有時光機。”
在面對未知話題時,仁科會變得極為嚴肅——比如幻想平行世界。“這個問題的矛盾點在于,即便存在平行世界,你也永遠不能到達平行世界,如果你能去的話,它就不是平行世界。所以有沒有平行世界,這個事情沒法印證。但即便有,可能也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樣。維特根斯坦說,不能說的保持沉默。人類如果沒辦法去感知這個東西的話,我們隻能繞着它。”
他用開普勒太空望遠鏡捕捉行星為例:“望遠鏡沒有辦法直接拍到行星,隻能通過監測恒星亮度變化的方式來捕捉行星。我們聊平行世界也一樣,隻能聊一堆周邊的,圍着它去聊為什麼會這樣想,事實上聊完一圈之後發現還是不能補捉,但聊的過程我覺得是有用的。所以你要聊平行宇宙,可以聊,但我們要用這樣的方式來聊,我沒辦法把它娛樂化。”
聊到夢與現實的差别和聯系,仁科想起《哈紮爾辭典》中所描繪的故事:一個人的夢境是另一個人的真實生活,兩人中若有一人醒來,另一人必定入睡。在他看來,夢就是現實,白天的蘇醒與夜晚的沉睡并無本質差别。“白天也有星星,隻是陽光太燦爛了,我們才看不見。”他覺得那些看不見的夢就像白天的星星一樣,看不到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我後來想,我們常說的‘白日夢’或者‘走神’,其實就是夢,其實你一天都在做夢,從廣義上說,夢就是你的現實。”
這些年,五條人用音樂記錄形形色色的人,講述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歌唱被時代遺棄的溫情和詩意,風格寫實又怪誕,聽他們的歌常會有一種夢與現實的交錯感。如果像《哈紮爾辭典》中所描繪的那樣,五條人所經曆的一切,很可能也隻是世界上某個陌生人的夢。
那麼,現在的生活對他們來說是真實還是虛幻?阿茂覺得,這一切肯定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不會因為好像紅了,就感覺一切不真實,我們也還是那樣,沒怎麼變。”
前一陣子,仁科去中央美院附近的文具店買了一些畫筆,他打算找個時間重新畫畫。“可能在我落魄的時候會架起畫布,然後打電話給《嘉人》——哎,我現在畫了一幅畫,你們要不要登啊?隻需要300塊錢……哈哈,開玩笑,至少3萬。”

(仁科)綠色真絲襯衫 PRONOUNCE
黑色西裝褲 SANKUANZ
黑色皮短靴 TOD'S
黑色墨鏡 SAINT LAURENT BY ANTHONY VACCARELLO
銀色項鍊 KVK
(阿茂)藍紫色真絲襯衫 均為PRONOUNCE
暗紋西裝長褲、紅色皮鞋 均為PRADA
黑色皮帶 BERLUTI
銀色項鍊、銀色戒指 均為KVK

M.C.:昨天看了兩集《明日創作計劃》,節目現在還在錄制嗎?
仁科:還在錄。
M.C.:你們享受錄制的過程嗎?
仁科:其實當地錄制的環境很好,酒店看出去是荷花池嘛,一個人工湖。
茂濤:很江南的。
仁科:什麼叫很江南,本來就是江南,對吧?哈哈哈哈哈。就好比你去法國,說“好法國啊”。
茂濤:因為它是人工湖啊。
仁科:阿茂的幽默,有時候你要消化一下。
茂濤:其實當導師,我一開始還真不習慣,但慢慢地覺得越來越好玩,也會跟那些學員聊,聽聽他們的想法或是年輕人現在喜歡什麼東西,因為大家都是在做音樂嘛,所以很喜歡跟他們聊這些,是亦師亦友的那種感覺。
M.C.:選作品時你們會有一個什麼樣的标準嗎?
仁科:我們的标準可能不太一樣,阿茂你可以先說一下。
茂濤:音樂這東西本來就是各有所愛,首先肯定是選你自己認為可以的,是吧?但我不會隻聽我喜歡的,還是會跟着感覺去判斷。因為在聽了很多音樂之後,自己也會有一個判斷标準,像編曲這些我會有一個自己的标準在那裡。
仁科:因為它是明日“創作”計劃,所以我在選歌的時候會更加在乎原創性,現場唱得好不好或者一些技術性的東西,我可能會“夫略”。
M.C.:忽略是吧?
仁科:對啊,忽略(笑)。就是我不會挑TA這個,我會挑TA創作,比如這首歌創作得很好,但演繹得不太好,沒關系,我會忽略。(問發音)對不對?
M.C.:嗯,忽略。不要在意這些細節。
仁科:對,就是這個意思,不在乎這些細節,不在意“夫略”的忽略,隻在乎TA的表達。當然,演繹現場的形式感有時候我也看重,隻是不在意技術性的問題。比如一些節目會對唱歌有标準,在意你的聲音表現,甚至從專業角度來說要杜絕“瑕疵”。但我不想定這個标準,因為有時候修得太光滑了并不好,我喜歡更加流露本性的,帶有自己的特色。
茂濤:是的,保留一點“粗糙感”,因為它的主題是“野生野長”,所以你就想聽到更加野生野長的作品。
M.C.:留一點“毛邊兒”。
仁科:對啊,好比說這個人普通話不标準,其實TA也可以嘗試說好普通話,但就讓TA不标準,比如“夫略”這些,我會忽略的,我會忽略我的“夫略”,諸如此類,就略過,哈哈哈。
M.C.:前段時間五條人發行了兩張新專輯,到時候會做巡演嗎?
茂濤:暫時沒有考慮,因為年底要開演唱會,所以巡演目前不會有了。但我還是很喜歡LiveHouse的那種演出,可以淋漓盡緻地玩,怎麼着都行,停下來喝酒、聊聊天都可以,是吧?演唱會又是另外一種玩法了,燈光、走位、美術……一環扣一環,一分一秒都不能出差錯,它更嚴謹,當然也會更刺激喽。所以我也很期待演唱會的感覺。

(仁科)綠色真絲襯衫 PRONOUNCE
黑色西裝褲 SANKUANZ
黑色皮短靴 TOD'S
黑色墨鏡 SAINT LAURENT BY ANTHONY VACCARELLO
銀色項鍊 KVK
( 阿茂 )藍紫色真絲襯衫 均為PRONOUNCE
暗紋西裝長褲、紅色皮鞋 均為PRADA
黑色皮帶 BERLUTI
銀色項鍊、銀色戒指 均為KVK
M.C.:演唱會是在哪裡舉辦?
茂濤:廣州、上海還有北京。第一場是在廣州,到時候記得來看,主場啊,肯定很棒。
M.C.:聽說這次專輯錄制的過程還挺開心的。
茂濤:哇,享受!
M.C.:有很多即興的部分,是吧?
茂濤:是的。因為以前錄專輯都會先排好,編曲弄好,直接進棚,幾天就把它給搞定了,為了省錢嘛那時候。這次錄新專輯有好幾首歌是在錄音期間寫的,像《南方戀曲》和《活魚逆流而上,死魚随波逐流》,還有好多編曲都是在錄音過程中搞定的,基本上都是即興的。這次加入了笙(張夢)跟老炮樂隊木推瓜的貝斯手陳創遠,樂手們都特别棒,大家都特别松弛,特别有想法。包括鍵盤手小珂(李炎珂)也加入了自己的想法在《南方戀曲》《左車道》《越南》這三首歌裡面,大家真的是在玩音樂,所以整個過程很享受,很開心。而且這兩張專輯裡,我很滿意的一個點體現在“讓位”,就是音樂人之間玩音樂的那種“讓位”,你讓我,我讓你,最後就形成了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覺。
M.C.:這一次就完全不考慮棚費了?
茂濤:其實也有考慮啊,但我們也很快就把它搞定了,十天左右吧。
仁科:有考慮棚費嗎?我沒考慮。(笑)
M.C.:發現你們很喜歡即興,前年去葡萄牙巡演時也有跟當地的一些藝術家即興合作,之前有在《行走的耳朵》上聽到過其中一首還未發表的即興作品。
仁科:哦,對對對,我給阿飛(《行走的耳朵》DJ)的,其實就是在萊裡亞小鎮上錄的,我們有好多段,改天把它發出來。
M.C.:什麼時候發一張你們的即興專輯或者EP?
仁科:本來是準備要做EP的,有剪一些曲子,但是還沒混音。現在工程在哪裡?(現場沒人回答)你看,一紅全忘了(笑)。
茂濤:在混音師那裡。
仁科:對,在混音師那裡,我去拿回來,給它加點歌詞,可以出(EP),你提醒我了。
M.C.:感覺即興是五條人音樂中挺重要的一個部分。
仁科:其實即興分很多種,比如在傳統爵士裡面,确實是需要懂很多的樂理知識、有很厲害的技術,無論你怎麼提升也需要這個。但後來我們打破這些條條框框,主要也是受到阿飛的影響。他辦的“明天音樂節”和“爵士音樂節”,讓我們了解到了更多的音樂家,發現了更多元的音樂形式。而且我覺得這種多元可以上升到一種思考,因為他的爵士音樂節不是傳統爵士,不是保守的,可能有一些人看完之後不能理解,會說“這什麼玩意兒?”但事實上,你回顧一百多年前爵士樂剛剛興起的時候,也有一些很保守的人來諷刺爵士樂,說這啥玩意兒?完全就是唱片倒着放,形容演奏爵士樂像“亂碼”。可現在,你看那些曾經被别人說“亂碼”的音樂,已經成為傳統爵士。同樣的道理,你去阿飛的“明天音樂節”或者“爵士音樂節”,也能看到很多新的東西出現。我理解這是自由探索音樂的另外一個(方向),所以我們也想要做多點嘗試。包括剛才我回答你關于《明日創作計劃》的問題,我說我更在意他們的創造性,哪怕他們身上的某些“瑕疵”是天生帶來的,但能帶上舞台,我也覺得非常好,就好像我們說的“去中心化”。當然,我們還是非常需要這個“中心”,我并不反對“中心”,但我也不否定“周邊”,隻有這樣才會把音樂搞得好,是不是?
茂濤:對,你會有更多可能性出現。比如這次,我們兩張專輯裡面大量應用了笙還有長号,主要是笙,我覺得它和其他樂器碰撞之後會變出一個新的東西,這是特别有意思的。可能接下來我們去演出的時候,張夢的笙也好,仁科的電吉他也好,你要說每次會一模一樣,我覺得可能性不大。
仁科:是不可能。而且用這樣的方式來創作,也是在避免重複這些無聊。如果大家隻在一個框架内去即興,那彈出來的東西可能也會(無趣)。當然,也有一些固定标準的旋律,但反正在現場大部分歌我們都可以重新玩,比如即興去作曲,你既是在表演,也是在當場創作,也有這樣的快樂。哇,我回答得很正經(笑)。

(仁科)漸變真絲襯衫、紅色西裝、紫色西裝長褲
均為BERLUTI
暗紅色皮鞋 TOD'S
(阿茂)藍色提花羊毛連體衣、暗紋西裝長褲、綠色皮鞋
均為PRADA
黑色皮質腰帶 BERLUTI
M.C.:之前仁科有說過“即興的三大原則”,但你當時隻說了前兩條,到第三條時說“下回分解”,所以第三條是什麼?
仁科:你還記得前兩條嗎?
M.C.:第一個是在規則内達到無極限,第二個是從規則内到規則外。
仁科:對,一是在規則内達到無極限。這很好理解,就像《海上鋼琴師》裡面,1900說他不下那艘船,他說88個琴鍵對他來說已經夠多了,它能形成的音樂是無限的。這88個琴鍵就像是我們肉眼看到的規則,你可以在尊重現有規則的條件下創作出無數個非常牛逼的作品。然後第二個,從規則内到規則外。就拿約翰·凱奇的“預制鋼琴”來說,他可以在鋼琴上放釘子、夾子,放各種東西,發出非鋼琴的音色,你可以理解這是“從規則内到規則外”。再比如很多年前,我認識的一個在琴行工作的人,他很搞笑,有時候别人問他,這個鋼琴能拿來做什麼?他會不耐煩。有一次好像是店長問他,他來氣了,說鋼琴當然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可以彈它,你可以把蓋子蓋上在上面寫作業,你TM還可以把他劈了拿去燒。這也是“從規則内到規則外”。我隻是說到兩個,第三個也很精彩。
M.C.:所以第三個到底是什麼?
仁科:等下次你們找我們當封面人物的時候,我絕對說出來,我敢保證,真的。
M.C.:聽完兩張專輯和看完兩支預告片,會有一種現實和夢境的交錯感,好奇你們怎麼看待夢和現實的差别或者聯系?
茂濤:2004年的時候,我回到海豐拍一個紀錄片,關于我們當地的傳統活動“建醮”,是一個比較大型的祭祀活動,道士設法壇做法事,保佑人們風調雨順,整個流程很有意思。當時我去拍紀錄片是從頭跟到尾的,總共七天,我一直跟,非常集中精力,每個細節都想要捕捉到。後來我在做夢的時候說夢話,那個朋友聽到了,他說你做夢還在拍東西啊。這個要怎麼拍,那個要怎麼拍,說我叽哩咕噜說了一大堆。那一次我就覺得,夢跟現實有時候是連接在一起的。
仁科:夢其實就是現實。比如我夢見阿茂,夢裡面的阿茂可能不是他現在的樣子,但你在夢裡面認為他就是阿茂。比如有一次我夢見去美國,那個美國跟縣城一模一樣,但夢裡面告訴我這就是美國。還有一次我夢見我的家鄉捷勝,它在現實中是個小鎮,但在夢裡面高樓林立,就像未來一樣。我們說“能指”跟“所指”,夢就是“能指”跟“所指”的混亂。你可以在現實中控制自己的行為,而夢的内容你幾乎是沒有辦法控制的。如果你要說“清醒夢”之類的,那另說。我後來想,我們常說的“白日夢”或者“走神”,其實就是夢。人在睡着時大腦運作會産生夢,清醒時我們的大腦也沒有停止轉動,夢依然存在,隻不過那些夢就像星星一樣——白天也有星星,隻是陽光太燦爛了,我們才看不見。白天看不到夢,但不代表夢不存在,其實你一天都在做夢。所以從廣義上說,夢就是你的現實。
M.C.:除了發專輯和錄綜藝,你們最近還在做什麼?
仁科:尋找生活的裂縫,哈哈哈哈哈。除了錄綜藝、出專輯,目前還在接受《嘉人》采訪,占用我們幾個小時的時間,但我們很樂意,因為覺得你們很專業,整個過程很開心。
M.C.:謝謝。現在主要是待在北京嗎?
仁科:有時候在無錫和上海,有時候各處演出。
M.C.:五條人什麼時候會開辦一個展覽?
茂濤:其實我們之前在廣州畫廊有辦過一個海報展,其他展覽肯定要看有沒有好的idea,對吧……弄得感覺我們好像是在玩跨界啊,但這些可能性都是有的。
仁科:以前阿那亞那個也有點類似,這個好玩的,應該不會太久。

編輯/陳柏言ChicoChan
攝影/鬼馬易
撰文/一毛
造型監制/王喬
造型/TiaYang
化妝/麗橦s
發型/易東N
編輯助理/杜一鳴
場地提供/33 Art Space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