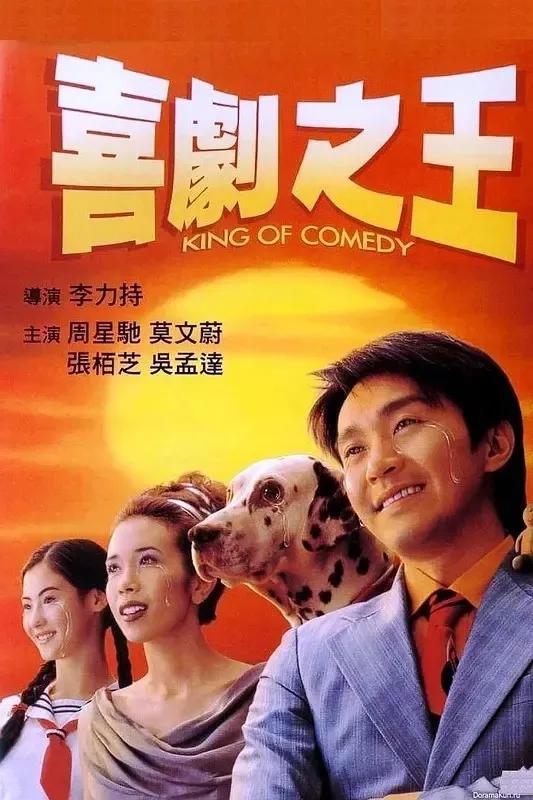趙季平接受本文作者專訪。(受訪者供圖)
前不久,在湖南師範大學音樂學院舉辦的“趙季平音樂創作國際學術論壇”上,中唱上海分公司向全球首發了一套五張“趙季平音樂作品經典系列”黑膠唱片。這是中國最老牌唱片公司花巨資,從德國全套引進黑膠生産流水線後,出版的首套名家唱片。
真是筆走龍蛇。中國的電影大片、熱播電視劇的配樂,近乎一半出自趙季平之手;影視作品的音樂中,走紅的主題歌,趙季平三分天下有其一;保守估計,有三代人、超過8億中國聽衆,聽過他的音樂。那年中國女排在歐洲打比賽,到了緊要關頭,忽然觀衆席上呼啦啦地唱起了《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
趙季平,在上世紀80年代電影《黃土地》以來的幾十年間,開創了中國影視音樂的一個“黃金時代”,導演張紀中說:“他給中國電影,帶來了無法抗拒的音樂力量……”
這僅僅是電影音樂。在音樂創作諸多領域,趙季平涉獵甚廣,包括交響樂、協奏曲、室内樂、歌劇、民族管弦樂、舞劇、藝術歌曲等,他的作品,題材之廣、數量之多、質量之高,令人歎服。
【人物檔案】
趙季平,男,漢族,1945年8月生于甘肅平涼,1970年畢業于西安音樂學院作曲系,1978年進入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學習,現任中國音樂家協會第八屆名譽主席。他是我國目前電影音樂界獲獎最多、獎次最高的音樂家。經他配樂的電影《紅高粱》、《孔繁森》分别獲得第八屆、第十六屆“金雞”獎最佳作曲獎,《五個女子和一根繩子》獲法國“南特”國際電影節最佳音樂獎,電視劇《水浒傳》獲第十六屆“飛天”獎最佳音樂獎,其中《好漢歌》獲最佳歌曲獎,《嫂娘》獲第十八屆“金鷹”獎最佳音樂獎。

趙季平寄語:“寫不盡我的祖國和人民!”(除注明外,均施雪鈞攝)
泥土芬芳承載大氣象
一個作曲家的黃金儲備,就是他對生活的思考和觀察的儲備,換句話說,就是要有内容豐富的外部經曆和内心經曆。

趙季平向湖南師大校領導贈送“趙季平音樂作品經典系列”唱片
趙季平難忘第一次“觸電”的經曆。1984年,他與陳凱歌、張藝謀、何群等年輕導演到陝北采風。在延安的窯洞裡,他們聽了農民歌手賀玉堂唱了整整一晚的陝北民歌。是夜,趙季平滿腦子都是貧瘠村落的一個個畫面。
在米脂縣,他們住進腳夫歇腳的大車店。“這晚,睡在炕上,我們蓋的被子與土地一樣黑,上面都是‘小爬蟲’,那條件,你想象不出有多艱難。可電影《黃土地》中的窮苦農民,卻一個個變得栩栩如生起來,有筋骨、有血性、有情感。”趙季平說。
雲層急劇的碰撞與刺激,便産生出奇妙的電閃雷鳴。作曲家靈感忽現,音樂從靈魂中汨汨流淌出來。很快,趙季平寫出了主題曲《女兒歌》。這晚,在窯洞裡,幾位導演将燈熄滅,黑暗中,傳來了如泣如訴、攝人心魄的歌聲。燈亮後,每個人眼中,都噙着淚花……
這是一次難忘的藝術“煉獄”!正是這次成功,鍛造了趙季平的未來。
此後幾十年中,無論在與陳凱歌合作《霸王别姬》《風月》《梅蘭芳》,還是與張藝謀合作《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挂》《秋菊打官司》,與張紀中合作《水浒傳》《笑傲江湖》《倚天屠龍記》等影視片,趙季平都如同旅行家,用“腳”在寫音樂。寫《水浒傳》音樂,他行走在齊魯大地;寫《喬家大院》,他數次深入山西忻州、河曲一帶采風;寫《狼毒花》,他多次前往陝晉蒙邊區;寫《大秦嶺》,他走進秦嶺山區腹地,如此等等……
趙季平的音樂,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達到一種新的境界。他将音樂與電影情節的結合,發揮到極緻,如同中國建築藝術的榫卯結構,絲絲入扣,嚴密無間。音樂,塑造出了一個個電影的靈魂,直擊人們的心靈。
所有的成功,趙季平都歸結為“站在泥土地上寫作,與民族音樂血脈相通”。他吸收融彙各種戲曲和民間音樂的風格、節奏、音階等語彙,當作音樂母語使用。
這種“泥土氣”,成就了趙季平音樂的氣象萬千。譬如,《紅高粱》中震天撼地的48支唢呐群,《菊豆》中遠古幽靈般的埙,《五個女子和一根繩子》中娓娓訴說的南音尺八,《心香》中清新飄逸的箫和古琴,《霸王别姬》中傾訴心聲的京胡,《秋菊打官司》中的彈月琴,電視劇《喬家大院》中令人叫絕的晉胡和二股弦這兩件地方特色樂器的運用,電視劇《大宅門》主題曲中糅進的京韻大鼓、京劇、平劇、豫劇、梆子、民歌、通俗七種音樂元素……
民間音樂的絕妙元素信手拈來,成為趙季平音樂作品的标記。這基因傳承,來自他的父親——“為大衆而藝術”的中國畫一代宗師趙望雲。
趙季平說:“我的藝術,繼承了先父的基因。父親的作品,追求的是人民性。他的藝術追求,從小就植入我心。所以我特别關注民間的東西,我的音樂中,大量是老百姓的聲音,可能和我父親畫筆下的窮苦百姓和勞動民衆,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山水靈境,萬種風情,給了趙季平“洗盡塵滓,獨存孤迥”的靈感。他的大腦,成了中國民間音樂和戲曲的巨大儲藏室。他的音樂作品,跳動着生活脈搏,有民間音樂的根。
然而,光環、鮮花、榮譽、名利,與世無争的趙季平都看作過眼煙雲。他說:“我的音符,長于泥土中。”
中西合璧成就大格調
追求“中國風格、中國氣質、中國精神”,是趙季平創作意境的大格調。
“我經常做的功課是,一邊采風,一邊悉心研究國内外大師的總譜,研究他們的語彙和技巧,一手伸向傳統,學習民間藝術;一手伸向世界,借鑒國際音樂優秀成果。這就是我今天的創作狀态。我要用中國音樂的母語,與世界對話。”趙季平告訴筆者。

趙季平在百年老店中唱上海公司音像資料庫
日本作曲家武滿徹很欣賞趙季平的藝術獨創性。2000年,由他推薦,柏林愛樂在“夏季森林音樂會”上演了趙季平的交響音畫《太陽鳥》、交響叙事曲《霸王别姬》,時間長達20分鐘。這是中國音樂作品在國際“藝術珠峰”上“零的突破”。
可容納2.2萬人的柏林“瓦爾德尼森林劇場”,有着世界性聲譽,是音樂名家們的夢想驿站。因為在歐美特别是德國,樂團的等級森嚴,分甲級乙級,或者A級B級,樂團要上演一部中國作品,是件極困難的事,有時往往需要全體演奏員投票後,才能做出演奏決定。
而此次,是國際樂壇對中國作品、中國作曲家的認可,也是中國音樂的榮光時刻。因為,在西方人眼中,趙季平是“最具東方色彩、中國風格的作曲家”,其作品滲透着中華傳統的精髓、中華美學精神。他的音樂,既具有一種特殊的門德爾松式的優美和雅緻,以及洗練明晰的結構,又極具張力,有品位、有風格、有個性。他被公認為是一位集音樂純潔、甜美、勻稱、優雅的旋律大師。他的音樂,符合東西方聽衆的聽覺審美,其音樂中豐富細緻的情感表達,能觸動聽衆感官纖維中最敏感的神經。
在創作中,趙季平沒有照搬模仿西方現代音樂的作曲思維和技法,而是将其運用到中國傳統音樂的思維中,并将它中國化。這使得他的中國視野擴展為國際視野,成了“中國音樂走出去”的先行者。
“越是民族的東西,越要與時代同步,越要走向世界、感染世界。民族音樂如果鎖在家裡,那如何向外尋覓知音,産生共鳴,成為世界的精神财富?在多元化的世界裡,音樂界也要解放思想,對外開放,讓世界認知中國音樂,讓外國人對中國文化肅然起敬。”趙季平說。
他的《第一小提琴協奏曲》創作便是如此。這部國家大劇院的委約之作,創作曆時一年,但作品卻醞釀了近十年。他心無旁骛,定下創作宗旨,要寫出一部“思想精深、藝術精湛”的作品。這部表現人間大愛、人性回歸的作品,在2017年10月10日國家大劇院的首演中,便獲得極大成功。趙季平很欣慰。他說:“令我感動的是,首演後觀衆反響非常強烈,懂音樂的、不懂音樂的都很喜歡。之後,國家大劇院還帶着這部作品到北美巡演,外國聽衆也很喜歡。”
而他創作的大提琴協奏曲《莊周夢》,同樣也被國際樂壇一線演奏家帶進西方國家的音樂廳。這部作品,無論在文化内涵還是技術層面,都堪稱上乘之作。以至于大提琴演奏者馬友友在首演前,作了大量的特别研究和藝術闡釋。首演成功後,《莊周夢》成了他在各國演出的保留曲目。
《莊周夢》在國際樂壇處處遇知音。比利時皇家音樂學院一位教授特别鐘愛這部“美妙得難以形容”的作品,在比利時和中國,都上演了此作。
中央音樂學院前院長王次昭說:“趙季平是改革開放40年中國音樂發展的一個縮影。他的創作,恰恰是對改革開放40年中國音樂反思最好的回答,許多讓我們困惑的問題、未來需要解決的問題,在趙季平的作品中解決了。他是中國當代音樂創作的傑出代表。”
面向大衆呈現大情懷

趙季平為樂迷簽名。有三代中國聽衆聽過他的音樂
趙季平深愛大西北。指着腳下土地,他多次對筆者說:“對西安這個地方,我有一個情結——‘不浮躁,人心靜’。藝術創作,最需要的就是不浮躁。我的磁場就在這!”
兒子趙麟,解釋了他父親的“磁場”一說。“我父親一直不離開西安,很大原因在于家族的基因和傳承。我爺爺上世紀40年代來到陝西,安家西安後,畫遍了大西北的人民和土地。到了父親這一輩,他用音樂,繼續描繪大西北……”
趙季平出身于名門世家。父親趙望雲,與張大千、徐悲鴻等名家畫友多有往來。自小,趙季平和兄弟們就在文人荟萃的濃厚文化氛圍中受熏陶。趙家七兄弟中,出了三個音樂家、兩個畫家。
在家中,哥哥、弟弟自小就有畫畫天賦,而趙季平卻顯不出有何能耐。溺愛他的母親,稱他為“傻四”。可“傻四”對戲文與音樂,特别有感覺。或許,拉一手好京胡、能唱全本京劇《玉堂春》的超級京劇迷父親,将文藝基因,重點傳給了他。
趙季平說:“對音樂,我簡直是入迷。我們家住在西安碑林,碑林裡每天放廣播,那時我還沒有上學,不愛聽廣播,就自己哼哼,瞎編調。在小學三年級的一次晚會上,每個小朋友站都起來報志願。我站起身,脫口就說将來要當作曲家。到了小學六年級,我在院子裡組織起‘球拍掃帚樂隊’,球拍當小提琴,掃帚當大提琴,我拿着詩,瞎編了一曲,指揮一群孩子,教他們唱。父親看到後,常在一旁笑。”
然而趙季平卻非常喜歡看父親畫畫。一有空,他就鑽進父親的畫室,時不時地在一旁“指點江山”。看到精彩之筆,如京劇票友一般大聲喝彩。久而久之,使得他對色彩及畫面極為敏感,無意間練就了畫家觀察事物的獨特眼光。他覺得,父親的畫中有詩、有音樂。
1970年,趙季平從西安音樂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到省戲劇研究院。當時,父親被下放到農村,趙季平坐長途班車去鄉下看他。“在棉花地裡,我沮喪地告訴了父親,不料他聽後非常高興。‘到那好啊,你在學院學的東西,是書本上,是基礎。你要把民間音樂這一課補上,那可是個戲窩子,你要堅持住!’父親這番話啟發了我,猶如播下的種子。在那,我一個猛子紮了21年。磨煉,是最好的課。”他接着說,“從小,父親從來不打我們,也不給我們什麼壓力,但有時他幾句話,就讓你受用一輩子。”
的确,趙望雲在長期旅行寫生中練成的堅毅性格,人道主義精神,遠大、獨到的眼光,形成了超乎常人的精神信仰和人格力量。這個被馮玉祥稱為“頂愛國”的畫家,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的兒女們。
早在20世紀30年代,趙望雲的農村寫生,開辟了中國創作的生活之路。他發表在《大公報》上反映中國農村破産和勞苦大衆生活的畫,馮玉祥配上了打油詩,讓趙望雲監工、老舍作序,刻成48塊石刻,聳立在泰山腳下;上世紀30年代之後,他的塞上寫生、西北寫生,用中國的畫筆和技法,記錄了一個時代。趙望雲把生活轉到畫面上,而趙季平,又将父親的畫面轉到音樂中。
很多年後,人們發現,趙季平的文化遺傳,子承父脈。趙望雲曾說:“美術是凝固的音樂”,現在,趙季平讓“音樂成了流動的美術”;趙望雲一生“為大衆而藝術”,兒子趙季平一生是“藝術為大衆”。與西北有着特殊情緣的父親,将天生懷有對勞動者尊重的個人情懷等“基因”,都遺傳給了“傻四”。
這種“紮根生活”的家訓,使趙季平沒有偏離父親的藝術思想。他的音樂,始終面向大衆,人人都能在一種音樂體裁中認識到它的美。
可貴的是,趙季平的家風,正代代相傳。趙季平常用父親的藝術人格和思想,教育兒子。他告訴趙麟:“當年,你爺爺坐着大車,騎着駱駝,三上敦煌,五進河西走廊,在艱苦的條件下,長年堅持在大西北旅行寫生。現在,交通條件便利了,你可以坐飛機到蘭州,沿着你爺爺走過的路,到祁連山去深入生活。”趙麟聽從了父親的建議,深入祁連山采風三個月,回來後很快寫出了大提琴與笙協奏曲《度》,由馬友友、吳彤與紐約愛樂樂團首演并引起轟動。“我對他說,你看,深入和不深入,就是不一樣。紮根生活,是你爺爺留下的家風!”趙季平說。
在紀念父親的文章《心語》中,趙季平寫道:“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創作至今,我始終不忘父親的教誨,堅持把自己的創作植根于中國民族音樂這片沃土……”
是的,沿着父親走過的路,趙季平創作出了管子與樂隊《絲綢之路幻想曲》《黃河遙遙》舞劇《大漠孤煙直》室内樂作品《關山月——絲綢之路印象》《大秦嶺》等衆多脍炙人口的音樂。
趙季平說:“我來到這個世上,就有一個使命,為中國創作黃鐘大呂!”
記者手記 | “紮根生活,從小植入我心”
西安古城,趙季平先生的書房。自打2003年以來,筆者有幸成了這裡的常客。到西安,去趙府,似乎已成常态。
季平先生是筆者的良師益友。有一次聽了他新寫的小提琴協奏曲後,筆者發了一通評論,季平先生來微信說:“你的文字,與别人不同,與我的搭檔、詞作家易茗一樣,常常會給我帶來靈感。”這讓筆者受寵若驚。作為中國音協名譽主席,一代名家,其謙卑、儒雅之風,令人肅然起敬。
為此,對季平先生的新作,筆者多有關注。他的音樂,常常打動筆者,以至于生出探個究竟的沖動:那富有神思幻境般的金色旋律,是從哪條“神山”中流出的?是喜馬拉雅山,還是唐古拉山的格拉丹東,而且總不斷流。他精神王國中的神秘語言,緣何能一次次融化成難以捕捉的美,在人的心靈中引起共鳴?
這個謎一樣的存在,忽然有一天有了謎底。他的夫人張甯佳告訴筆者:“季平将父親的精髓,完全化在了血脈裡了。”原來如此。
趙家兄弟中,季平先生在發型、神态、臉龐、身材方面,最像其父親。然更為重要的是,季平先生從骨子裡全盤繼承了父親的衣缽,将父親内在的人品、人格和藝術精神,完全化在了血脈裡。他用自己的情感,去感受音樂大衆的情感,不斷寫出攝人心魄、人民喜愛的音樂作品。
季平先生說:“‘紮根生活’,‘為大衆而藝術’……我父親留給我們的精神太珍貴了。我的藝術,繼承了我父親。”季平先生如此,他的三哥——長安畫派嫡傳弟子趙振川也是如此。
語言樸實無華,哲理卻深透。我想,這就是他音樂中“水活石潤,于天地之外,别構一種靈奇”意境之所在。
作者:特約撰稿 施雪鈞
編輯:王秋童
,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