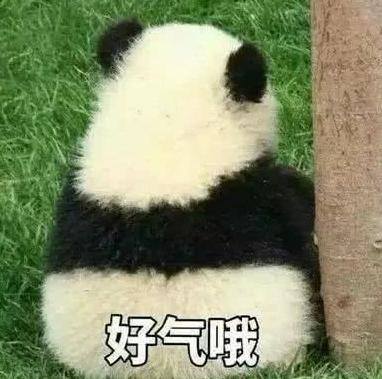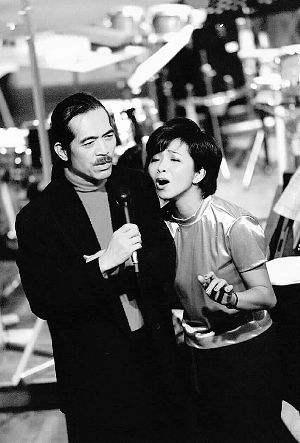作者:科普作家吳京平(平哥)
202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揭曉2022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已經正式揭曉了。得獎的是三位實驗物理學家:法國的阿斯派克特、美國的克勞瑟和奧地利的塞林格。獲獎的理由是“用糾纏光子驗證了量子不遵循貝爾不等式,開創了量子信息學”。

我很高興啊,因為這一次我猜對了,我在今年的諾獎揭曉之前曾經做了一次音頻節目,講的就是諾獎風向标。這三位科學家在2010年就曾經獲得過沃爾夫獎,這也是諾獎風向标之一,所以我猜他們有可能會獲獎。
量子糾纏與貝爾不等式有關量子糾纏這檔子事,最早可以推回到1935年。愛因斯坦和波多爾斯基以及羅森三個人合寫了一篇論文,提出了EPR佯謬。E代表愛因斯坦,P代表波多爾斯基,R代表羅森。

當時物理學界分了兩大派,一派是玻爾為首的哥本哈根學派,另一派就是愛因斯坦和薛定谔為首的反對派。愛因斯坦和玻爾吵架,始終也沒吵赢過。他主要是對量子的疊加态這個概念很不爽。就是為了給疊加态這個概念找别扭,才專門提出了這個EPR佯謬。
薛定谔也對疊加态很不爽,所以,他才設計了那個著名的“虐貓事件”。一隻貓可不可能既是死的又是活的,處于死與活的疊加态?毛病就出在這個疊加态上。疊加态塌縮更離譜了,難道你一觀察,貓的疊加态就瞬間塌縮,變成了決定性的,要麼死,要麼活?你這個觀察者這眼光也太厲害了吧。

所以,後來薛定谔在看到愛因斯坦的EPR論文以後,一個詞脫口而出——量子糾纏。這個概念就是這麼來的。
有關這個理論,我們不妨做個簡化版的描述。你可以設想這樣一個過程:一台機器會發射不同顔色的小球。如果愛麗絲接到一個白色的球,對面的鮑勃一定會接到一個黑色的球,反正是這兩個球的顔色總是相反的。

玻姆提出了一個隐變量理論。如果按照隐變量的理論,這兩個球在發射出來之前就已經決定了。這個觀念很符合大家的一般認知。
但是,如果按照疊加态的說法,這兩個球在發射出來以後,一直是處在疊加态。直到愛麗絲觀察到這個小球A的那一刻,小球才突然從疊加态随機塌縮成白色。同時,就像是心靈感應一般,對面的那個小球B也必須保持和A狀态相反。所以B也突然從疊加态塌縮成了黑色,不管距離多遠,哪怕在宇宙盡頭,也得立馬跟着變過來。
愛因斯坦認為,這種鬼魅般的超距作用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僅從觀察上無法區分到底發生了什麼。到底存不存在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到底存不存在隐變量,這就成了一個懸案。時間長了,這也就變成了扯不出答案的哲學問題了。
其實物理學家惠勒很早就提出了正負電子相互泯滅,會放出一對光子,這一對光子應該是相互糾纏的。1948年,哥倫比亞大學吳建雄和薩科諾夫成功地做出了這個實驗,這是人類第一次搞出相互糾纏的粒子。但是那時候搞出來的糾纏粒子都不太穩定,沒有多少實用性。

圖:吳健雄
後來嘛,大家注意力都不在這裡,大家都在鼓搗對撞機呢。一直到了1964年,物理學家貝爾才給出了一個驗證方法,這就是所謂的“貝爾不等式”。這就使得扯不清的哲學問題再一次變成了實驗物理的問題。


貝爾提出他的不等式以後,并沒有太多的人關心。但是,有一個人對這事兒特别留意,他就是這一次的諾獎得主克勞瑟。
前面鋪墊太長了,到現在主角才出來。
克勞瑟當時在加州理工,他就跟著名物理學家費曼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要做實驗來驗證貝爾不等式,結果費曼蹦起來就把他從辦公室給扔出去了。這是他自己後來回憶的,不是我瞎說。
後來克勞瑟去了哥倫比亞大學,因為哥倫比亞大學搞理論的有李政道,搞實驗的有吳健雄。這個環境好啊,你随便挑啊。
克勞瑟去了以後就跟吳健雄實驗室的人打聽,當年他們如何做出糾纏粒子的。這都過去20年了誰還想得起來呢?但是,克勞瑟也知道了,當年他們做出的糾纏的粒子很不穩定,沒法用來做其他實驗。
反正,當時克勞瑟癡迷于研究如何驗證貝爾不等式,自己的主要工作做得并不好。結合昨天我們講到的帕博(202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似乎這些未來的諾獎得主都得從不務正業開始。
克勞瑟後來成了激光大神湯斯的手下,湯斯是第一個在微波頻段實現受激輻射的人,其實就是頻率在微波波段的激光。湯斯這個老闆還是很開明的,他允許克勞瑟花一半的時間研究貝爾定理,這就是合法的不務正業嘛。

圖:湯斯
沒有湯斯的支持,克勞瑟很難取得後面的成果。克勞瑟與其他人一起改進了貝爾不等式,變得比較容易實驗。而且他們還改進了試驗方法。他們找到了一種新的方法來産生糾纏的光子。就是用紫外線來照射鈣原子,有一定概率會産生一對糾纏的光子,一個是551納米的綠光,另一個是423納米的藍光,顔色不一樣。

但是這個實驗依然很難搞,克勞瑟和小夥伴們累計試驗了200多個小時。制備糾纏光子對非常困難,大概一百萬光子裡隻有一對糾纏光子,比率太低了。在1972年,他們終于公布了結果,最後的結果不支持隐變量理論,實驗結果違反了貝爾不等式。
當然,這個實驗并不是沒有漏洞的,所以還是不能一錘定音。真正要取得下一個進展,還要等到10年以後。
阿斯派克特

提出貝爾不等式的那個貝爾本人一直在歐洲核子研究組織工作。這一天,有個學生開着車興沖沖地從巴黎趕來找貝爾。這家夥是貝爾的粉絲,也在惦記着做貝爾實驗。可貝爾不認識他,來的這個人自我介紹:我叫阿斯派克特。
大家别急哦,第二位主角登場啦。
這個阿斯派克特是法國人,他去喀麥隆當了3年的志願者,上非洲搞扶貧去了。在扶貧期間,他看了好多有關量子力學的書籍,對量子糾纏和EPR特别感興趣。做完了志願工作,他立馬拎包回了巴黎,一高興就考上了巴黎大學的物理學博士生。
你看人家的水平啊,要考上就考上了。
這個阿斯派克特也跟量子糾纏死磕上了。他也知道克勞瑟他們做的貝爾實驗,他要做的第一步就是重複克勞瑟的實驗。他改用激光激勵鈣原子,激光的效率非常高,做出來的效果比當年的克勞瑟高了好幾倍,實驗結果是大幅度偏離了貝爾不等式。

圖:當時的實驗室
第二步就需要利用雙通道的方法來提高光子的利用率,減少前人實驗中的所謂“偵測漏洞”。這個實驗也大獲成功,最後以40倍于誤差範圍的偏離,違背了貝爾不等式。這個效果比上次還要好得多。
第三步,他搞定了延遲決定實驗,這個主意還是貝爾出的。所謂的延遲決定實驗,就是要徹底斷絕兩個光子之間暗通消息的可能性。為什麼糾纏光子在通過檢驗的時候,偏振方向總是相互垂直的呢?到底是因為鬼魅般的糾纏作用,還是光在用什麼我們不知道的辦法暗通消息?
那好啊,我們等着光子飛出來,快要到檢驗器門口了,突然改變檢驗器的偏振角度。消息最快不超過光速。偏振角度切換極快,這時候兩個光子相距13米,無論如何來不及互相通消息了。這樣做出來的實驗漏洞更少。

阿斯派克特團隊最後獲得的結果,依然是大幅度偏離了貝爾不等式,基本可以認為愛因斯坦是徹底錯了。
但是,你非要雞蛋裡挑骨頭,漏洞總是有的。你用來控制檢驗器偏振方向的那個随機數發生器,是不是真随機呢?這就輪到第三位主角登場了。
安東·塞林格

安東·塞林格利用遙遠星系發出的信号作為控制信号。這可是真随機,而且這個随機數發生器太遠了,實在是沒機會參與作弊。結果依然是違反了貝爾不等式,漏洞也比以前更少了。
安東·塞林格專注的領域是在量子糾纏,這是貝爾實驗的基礎。他對多光子糾纏及量子傳輸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這種技術不但對檢驗量子力學的基本原理有很大的用處,而且還對量子信息發展提供了很大的助力,無論是量子通信還是量子計算都是離不開量子糾纏的。要是沒有量子糾纏技術,量子計算機相對于經典計算機就體現不出優勢了。
塞林格最重要的貢獻是在1997年實現了量子隐形傳态。潘建偉院士當時是他的研究生,對這篇論文也有非常重要的貢獻。
量子隐形傳态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打個比方,用顔色表示狀态,A粒子最初是紅色的,通過隐形傳态,我們讓遠處的B粒子變成紅色,而A粒子同時變成了綠色。
其實,我們完全不需要知道A最初是什麼顔色。無論A是什麼顔色,這套方法都可以保證B變成A最初的顔色,同時A的顔色改變。
當然,說起來簡單,做起來複雜。要讓遠方的B跟着起變化,就必須借助和B糾纏的粒子C。這個C留在家裡,和A距離很近,但是B必須傳送到足夠遠的地方才有實用意義。和5米開外的人通信,喊一嗓子就夠了,用不着量子通信。
所以,先要弄出一對糾纏光子。把一個光子發送到遠方,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一開始塞林格他們傳輸的距離很短,後來他們把糾纏的光子發過了多瑙河,實現了跨越多瑙河的隐形傳态。
再下一步是實現了非洲加納利群島各個島嶼之間的量子隐形傳态,距離就拉伸到了上百千米。最誇張的就是利用墨子号衛星實現高達上千公裡的量子糾纏。當然啦,這是我們中國人的貢獻。在諾獎揭曉儀式的講解之中,還特别提到了這個成就。

1997年實現的是單個光子的單個自由度的量子隐形傳态,現在要實現的是單個光子的多個自由度的量子隐形傳态。完整意義的量子隐形傳态,應該說是2015年才由潘建偉院士團隊實現的,現在我們才是這方面的領軍者。
不管怎麼說,克勞瑟、阿斯派克特和塞林格能夠獲得2022年的諾貝爾獎,就是國際科學界對他們巨大成就的認可。開創者和奠基者完成的是從0到1的突破。

同時,我們又一次發現,其實我們中國人也深度參與其中。從0.5到1的這部分,我們有參與。從1到100這段路還沒走完,現在看,我們也是領先的。
所以,我想再次重申我的觀點,盡管我們還沒達到前三名的水平,還不能站上領獎台。但是,我們也有優秀的科技人才在向這個水平靠近,他們就潛伏在台下,可能是第四名、第五名也說不定哦。未來一定有希望站上領獎台,對此,我們有信心,有耐心。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