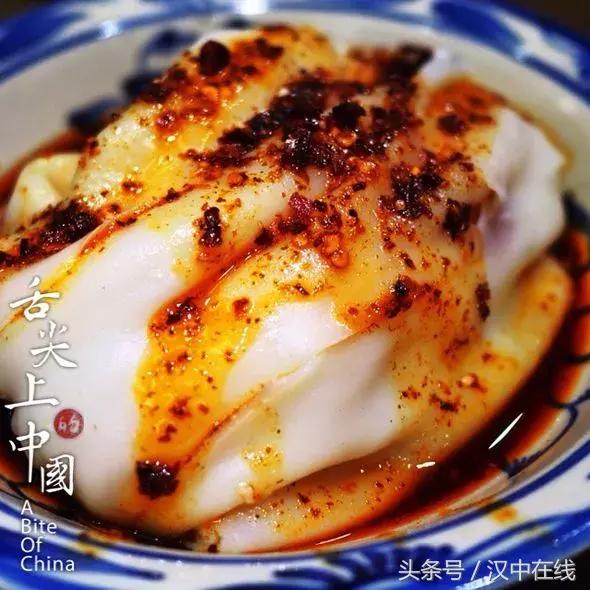了解王陽明思想,你不可不知的三個學說
我們都知道,陽明心學由三個重要的部分組成,即“心即理”“知行合一”和“緻良知”。不過,思想的形成都是有一個過程的,思想也是不斷臻于完善的。王陽明在龍場悟道,悟出“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即“心即理”之後,并不是立即提出了他的核心思想“緻良知”。
王陽明的高徒錢緒山曾經指出,王陽明的“學”有三變,“教”亦有三變。“學三變”是指:一、少時,馳騁于辭章;二、後來又沉迷于道教和佛教;三、在龍場曆盡艱難之後,豁然有得于聖賢之志。“教三變”是指:一、在貴陽時,提出了“知行合一”說(1509);二、自安徽滁州回來後,教授弟子“靜坐”說(1513);三、自江西回來後,提出“緻良知”說(1521),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
在提出“緻良知”說之前,王陽明曾經陸續提出過三種學說,即靜坐說、明鏡說和立誠說。這三種學說雖然各有局限,但是都為“緻良知”打下了基礎。所以,若想了解陽明心學,我們不可不知陽明思想的發展路徑。
“靜坐”說:陽明心學發展過程中的連接點
王陽明的“靜坐”說是陽明心學發展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連接點,它上承“知行合一”,下啟“緻良知”說。
正德五年(1510年)十二月,王陽明接到朝廷任命,前往江西吉安府廬陵擔任知縣。他離開湖廣省辰州府時,給諸位弟子寫了一封題為《與辰中諸生》的信,信中寫道:“前在寺中所雲靜坐事,非欲坐禅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拿,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這便是“靜坐”說。
王陽明為什麼要提出“靜坐”說呢?據《陽明先生年譜》記載,王陽明當時曾指出:“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即者。”
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之後,引起了很多争論。為了讓世人理解“知行合一”的主旨,王陽明主張通過“靜坐”去自己覺悟心性的本體。龍場悟道不是說“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嗎,那麼,就通過“靜坐”去體會“道”與“心性”。
當王陽明在辰州講授“靜坐”說時,有弟子誤認為“靜坐”就是禅僧所謂的“坐禅入定”。針對這一情況,王陽明在離開辰州後,特意給弟子們寫了一封信,向大家闡明“靜坐”的本意,告誡弟子們“靜坐”和禅僧的“坐禅入定”是不同的。
“靜坐”和“坐禅”在世界觀層面是完全不同的,哪怕它們在精神收斂層面存在共性,然而二者在本質上不同。王陽明将自己的“靜坐”說比作孟子的“求放心”功夫,“放”是“失落”的意思。“求放心”,就是找到失落在外面的心。而佛教的“坐禅”,是為了體悟一切皆空的“佛性”。
雖然王陽明知道辰州諸生對“靜坐”存在誤解,而且由此産生了一些弊害,但在滁州時期之前,王陽明一直都在提倡“靜坐”的必要性。
正德九年(1514),王陽明前往南京赴任。據錢德洪介紹,在那段時間,王陽明做的一次真正的講學還是在滁州時,當時他也是讓弟子們去學習“靜坐”。
王陽明曾經這樣闡述讓弟子們學習“靜坐”的理由:“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傳習錄》上卷)
王陽明的“靜坐”說往往會使人隻專注于求“靜”,而對“動”産生厭倦之情,容易使人忽視“存天理,去人欲”,最終導緻弊害産生。于是,王陽明又提出了“動處功夫”說。他指出:“徒知養靜,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傳習錄》上卷)
陽明學一般被認為是實踐哲學,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省察克己”和“事上磨煉”都是關于實踐的。
王陽明的“靜坐”說并不是隻專注于“靜處無事”時的修行,同時也沒有忽視“動處有事”的功夫。王陽明曾說:“所謂知得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弟子陸澄就曾經問王陽明:“靜守時我覺得自己的一些想法很好,但一遇到事情卻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這是怎麼回事?”
王陽明回答說:“這是因為你隻知道靜坐修煉,卻沒有在克己上下功夫。這樣的話,一旦遇到事情,那些想法就不管用了。”
弟子劉君亮要去山中靜坐,王陽明勸告他說: “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個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複于靜處涵養,卻好。”(《傳習錄》下卷)
王陽明晚年提出“緻良知”,認為良知是一個内外、動靜和上下渾然一體的生命實體,因此沒有必要再去論證動與靜的關系。
“明鏡說”: 聖人之心如明鏡,常人之心如昏鏡
正德五年(1510)十一月,王陽明回到京城,黃绾和應原忠前來拜訪,和他一起探讨學問。王陽明對黃绾和應原忠說:“聖學久不明,學者欲為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陽明先生年譜》)
應原忠當時已是王陽明的入室弟子,後來為了孝養雙親而辭職返鄉,在山中苦讀近十年。最後,應原忠又重新踏入官場,出任廣東省右布政使。
應原忠對王陽明在上文中提到的教誨不太理解,心存疑問。正德六年,王陽明為了解除他心中的疑惑,特意作《答黃宗賢應原忠》(《王文成公全書》卷四),其中詳細闡述了“明鏡”論:
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
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才拂便去。至于堆積于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為煩難而疑之也。
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
向時未見得向裡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禅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内”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
在《傳習錄》上卷中,王陽明曾借用“明鏡”來比喻實踐修行的重要性,他說:“聖人之心如明鏡,隻是一個明,則随感而應,無物不照。故聖人隻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卻須先有個明的功夫。”
而王陽明的高徒徐愛則說道:“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徐愛從王陽明“格物”說的立場解釋了王陽明在書信中闡述的“明鏡”論,是對王陽明“明鏡”論的有力補充。
王陽明的“明鏡”論所說的就是“心”的修行。但王陽明又非常擔心,如果過于專注于心的修行,就可能會演變成棄絕一切外部事物和人倫道德,最終陷入靜寂虛無的“虛禅”世界。鑒于此種擔憂,王陽明借用程颢的話,來表明自己的“明鏡”論并非如此。
王陽明指出“明道所謂‘敬以直内’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用“義”的有無來區别儒學和佛教。此外,王陽明還指出“釋家最終未談居敬”,又用“居敬”的有無來區别儒學與佛教。“居敬”是儒家特有的“心術”,也是宋儒用來否定佛教心術的重要概念。王陽明的“明鏡”論可以說是“居敬”思想衍生出的産物。
王陽明晚年将“良知”喻作“明鏡”,他認為明鏡有自淨的能力,良知自身也有去除私意習氣的能力,所以順其自然就好。
“明鏡”論和“緻良知”說之間存在着“本體功夫論”上的差異。我們知道,神秀和慧能曾分别作過兩首偈,其中揭示的“明鏡”論的差異其實也是“本體功夫論”上的差異。
神秀:“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慧能:“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若将王陽明晚年時期的“緻良知”說和上文中的“明鏡”論做比較,我們會發現提倡“明鏡”論時的陽明心學更接近神秀的思想,而提倡“緻良知”說時的陽明心學則更接近慧能的思想。提倡“明鏡”論時的陽明心學認為“心”和鏡子一樣,需要打磨,才能廓清私欲;而提倡“緻良知”時的陽明心學認為“心體”是主體性的,可以自主性地運動,通過“心體”自身的運動就可以克服私欲。“明鏡”意味着澄明的“心體”,王陽明在壯年時提出“明鏡”論,将“心體”(也可稱為“真性”)喻作“明鏡”,這其實為他晚年創立“良知”說埋下了伏筆。一旦他悟出“心體”具有主體性,且可以自主性地運動之後,自然就會悟得“良知”說。

立誠說:立誠是根本,好比執刀于咽喉處
王陽明說:“為學必誠。”他在晚年時将“緻良知”作為學術宗旨,在此之前,王陽明一直将“立誠”作為為學宗旨。
王陽明于南京講學之時,尤為重視立誠。他認為,若想去私欲、存天理,若想實現省察克治,必須先立誠。唯有立誠才是根本功夫。
王陽明曾寫信給黃宗賢,提出立誠乃細緻入微的本原功夫,好比執刀于咽喉處,必要格外用心。
正德十三年(1518),王陽明特作《修道說》(《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對立誠加以詳細論述。同年,薛侃刻印《傳習錄》。《傳習錄》中多處提到了立誠的必要性,其中包括誠意與格物緻知的關系,誠意與正心的關系,誠意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關系,誠意與明善的關系,誠身與明善的關系等。
王陽明教育弟子,非常注重“為學須得個頭腦功夫”,認為唯有如此,“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傳習錄》上卷)
王陽明所說的為學頭腦包括存天理、去私欲,體認未發之中,省察克治,等等。其中的關鍵點就是,促使心體發揮作用。對王陽明而言,心體作用的終極目的即為立誠。王陽明曾以樹根與枝葉來形容誠意與其他功夫,該比喻極為貼切。誠意為根本之功夫,其他任何功夫皆應出自誠意,如此才有存在的價值。
王陽明的弟子守衡曾向王陽明請教“誠意”。王陽明認為《大學》的主旨即為誠意,誠意之關鍵即為格物,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要由誠意來實現。此觀點準确地揭示了心學的精髓。對此,王陽明補充道,功夫之難點就在于格物緻知,格物即誠其意。意若誠,則心自正、身自修。然正心、修身之功夫又各不相同,正心為喜怒哀樂處于未發之時的功夫,修身為喜怒哀樂處于已發之時的功夫。總之,心若正則意“中”,身若修則氣“和”。
由上可知,王陽明認為,誠意是貫穿《大學》《中庸》始終的本原功夫。
王陽明提出,誠即心之本體,唯有思誠才能恢複心之本體,因此,也可将“誠”稱為本體功夫。
王陽明在提出“緻良知”之前,将誠意作為培根之學的主旨。當他提出“緻良知”之後,緻良知就成為培根之學的主旨。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