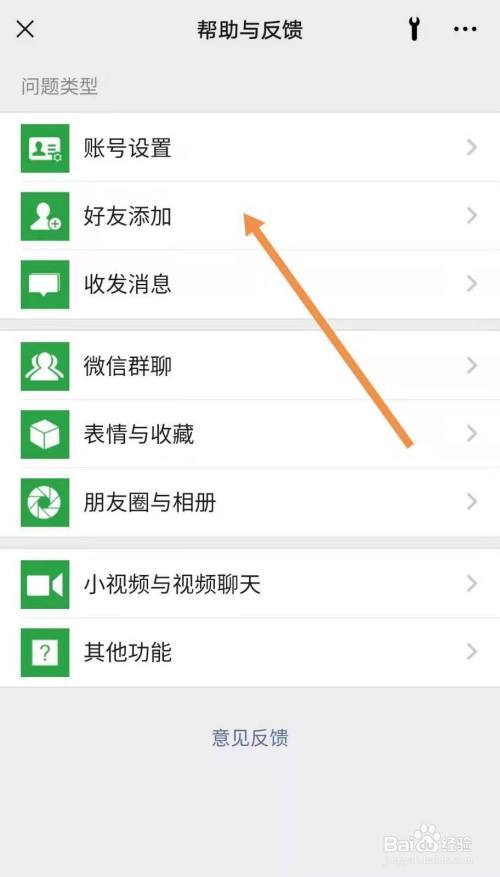(本文由Sir電影原創:dushetv)
有個字,生活裡提到它,我們如臨大敵。
它有時來得突然,讓人手足無措;有時會給個正式通知,讓我們精疲力竭。
一個到嘴邊總想繞開的可怕字眼——
死。
科學上這麼說:
“原有物質的新陳代謝停止,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不能恢複。是一種生命物質失去活性的狀态。”
但誰能活得如此科學、超脫?
今天要說的這部新片,可能會幫我們重新認識它——
《生命裡》

近期新上線的紀錄片。
由制作了《水果傳》《本草中國》《中國美》的團隊雲集将來出品,演員萬茜旁白。
它的鏡頭對準的,是一家醫院的特别病區。
或許你還有印象——2年前,Sir推薦過一套讓所有人淚腺失控的紀錄片,《人間世》。
那部劇的第4集,講述了一個特别病房。
沒有痛苦呻吟,沒有緊急搶救,隻有一張張病人迅速叠代的病床。
上海臨汾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安甯病房。我國少數幾個臨終關懷病房之一。

在這個病房裡,住着所有知道自己生命時限的人。
主要都是癌症晚期患者。
12天、1個月、2個月……
《生命裡》記錄下的,就是一天天走向終點的那些人的故事。
很多人對于“死”,隻有一個個瞬間的、具體的時刻——
電話那頭,親人故作平靜地互相催促着“快回來,TA不行了”。
手術病房前,厚厚一沓需要簽名的病危通知單。
然後,就是科學描述的“生命物質失去活性的狀态”:
一雙再也無力舉起的手;
緩緩合上的雙眼;
最後,一壇灰燼。
這些瞬間,是疼、是恍惚、是不忍回想的記憶,是“死亡”這個科學事實,留給生者的陣痛。
但我們仍不知道,離開的他們經曆了什麼?
《生命裡》試圖回答。
它用十多位病人的告别,向我們展示了生命另一端的光景,也讓我們重新被“死亡”教育。
這種教育不算吓人,卻很安靜。
它的鏡頭下沒有極度煽情,也沒有沖擊力超強的巨痛。
安甯病房有個單獨的房間,叫關懷室。
裡頭沒有搶救儀,沒有起搏器,隻有一盞燈、一張床、一座沙發,和一張半透的紗簾。
已經被确認生命體征即将消失的病人,會被推入簾内。
離人在左,等待最後一絲心力耗盡;
生者在右,靜靜陪TA吐完最後一口氣。
暖黃的燈光,見證着這場最後的陪伴。

死亡隻是一瞬間,但走向死亡卻不止。
《生命裡》替我們放慢了告别者的無數個瞬間。
來到安甯病房的人,剛開始面色都挺正常。
但很快,他們就像慢慢洩了氣的氣球,一點一點肉眼可見地癟下去。
陳曉軍,背部有腫瘤。
剛進院時,他還能雙手搭耳後,跟觀察病情的醫生“讨價還價”。
我是想最好能夠給我站起來
邊吃着老伴兒帶來的猕猴桃,邊跟查房護士争論,輸液裡到底有沒有營養。
女兒給他刮胡子,也乖乖配合。
但不出半個月,陳曉軍整個人都暗了。
腰椎使不上力,得靠搖床才能坐起。
手呢,虛浮腫脹,握不住筆。
意識渙散,眼睛也睜不開。
陳曉軍的變化還算比較直觀。
病房裡還有病情反複、時好時壞的老奶奶,更磨家人。
她耳朵背,說話得貼着耳後喊,才能稍微聽清。
好時,老太太清醒,會叮囑女兒打掃家裡,會擔心住院貴。
不好時,意識模糊,總說胡話,沖着照顧她的女兒說謝謝。
像孩子一樣張口詢問“啥”
越到“終點”,越活成了孩子。
身上難受,想發脾氣。
感覺生活質量低,就總是訴苦個不停。
這種情況,老人可憐,老人的家人也耗神。
病床上除了等待,還有回憶。
人在離世前,平時不想的事,都會找上門來;平時心裡很輕的東西,都會變得無比重。
床上的陳曉軍,就總在遺憾。
遺憾當兵後就不曾謀面的老哥哥,死前是再見不到一面了。
遺憾被自己病情耽誤的女兒,等不到看她有個好歸宿了。
沒有《生命裡》,沒有安甯病房,陳曉軍的遺憾和愧疚,可能隻會有自己知道。
《生命裡》的病房,主角不再是情況危急的病人、醫術高超的醫生。
而是一個個知天命、曉大限的普通人。
以及一個個陪他們走完最後一程的護士、護工和志願者——
他們的工作有照顧:
每天擦身,整理房間。
替病人擺弄床頭的花、魚缸小寵物,熱熱鬧鬧地過節。
最不起眼也最重要的就是:
陪他們聊天。
是啊,人活一世,好多事沒人問,自己都要忘了。
68歲的魯勝蘭,總想起年輕時被派去新疆的日子。
想起去新疆上火車前,老娘的淚。
想起年輕時,吃過的瓜。
是嗚嗚嗚像吹口琴一樣吹過去那種情形現在沒有了
也偷偷跟護士說,拉扯孩子時撐不住的辛苦。
那些過去,聽起來都是簡單的隻言片語。
可在聊天中細細展開,母親、青春、孩子、邊疆……就是一生。
在生命最後,能撫慰他們的不是藥物、儀器、看護,而是靠近、聆聽。
Sir印象最深刻的,是家屬或護士聊天時,手上的親密小動作。
指腹輕輕摩挲着TA的眉心、眉梢、指甲蓋,看着他們的眼睛。
像對待心愛的人一樣,專注又溫柔。
死是人都怕。
也正因如此,死,需要被溫柔對待。
就像開頭Sir說的,不少人對死心存忌諱,閉口不提。
有人不想死在家,所以選擇來醫院,轉移“晦氣”。
家屬也說,裝修再好的病房,也是用來等死的。
甚至還有病房周圍的人家,也在外牆挂鏡子,反彈“晦氣”。
忌諱本身,“晦氣”本身,就是所有走到生命最後的人,無形的心理壓力。
本片最想告訴我們的,也許就在這。
“等死”是個糟糕的詞,因為沒有質量。
臨終關懷,是一件需要破除忌諱、破除恐懼的專業事業。
是每一個人活着的最後一項人權。
人們(觀念裡)隻有優生從來沒有覺得優死也是一個人享受的基本權利
生是一種值得慶賀的見面,那麼死,又何嘗不是一種值得尊重的道别?
紀錄片裡的護士張敏說,有些病人,在彌留之際身上還插滿醫療器具。
其實這種時候,已經是在為家裡人硬撐。
有的人,被醫療器具弄得渾身是傷,多過一天,于家人是慰藉,于病人卻是痛苦。
留他到最後一刻,未必就是孝順和尊重。
安甯病房中有個叫汪明昌的老人,對于幾十天後的離别,他相當坦蕩。
進醫院也隻有一個要求:
不想沒有生存質量地活着。
老人家住進來,每天收拾得整整齊齊。
後事交代得明明白白。
不開追悼會,一切從簡
最後那幾天,他跟病房裡的人聊天,聊年輕時進的好單位,聊年輕時認識的好老伴,跟着手機哼唱着人生中最愛聽的曲子——
在陽光正好的午後。
直到生命最後一刻。
一切如他所願:有尊嚴、有知覺地離開。
臨終關懷,聽着高深。
但做的事卻再普通不過:
給他平靜度過的一段時間,給他回憶美好的一段時間。
你是重要的,因為你是你,你一直活到最後一刻,仍然是那麼重要,我們會盡一切努力,幫助你安詳逝去,但也盡一切努力,令你活到最後一刻。——“臨終關懷”理論創始人桑德斯隻有3集的《生命裡》,對臨終關懷的探讨可能無法太深入,但這一課上得真好。
死者善終,生者善别。
中國人,我們太久忘記了這句話。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想看的,b站和騰訊都能看
編輯助理:莫妮卡住了
Sir電影原創,微信ID:dushetv
微信搜索關注:Sir電影
微博搜索關注:毒舌電影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