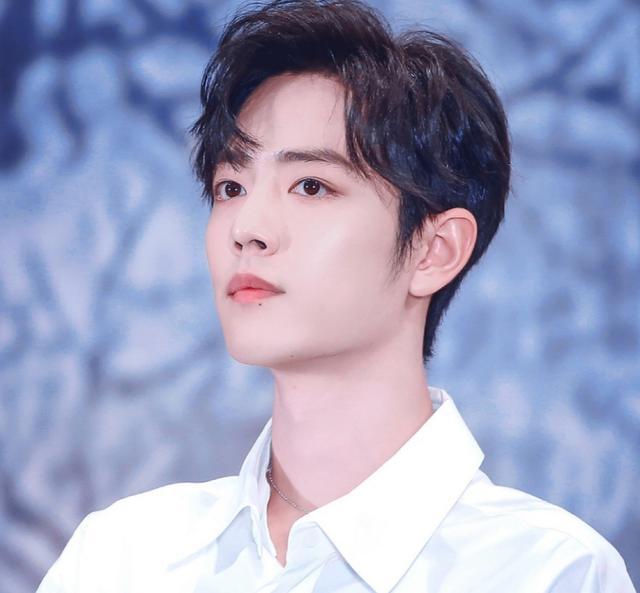導讀:去年以來,疫情使許多中國人無法到海外的精品店消費,而把消費留在了國内,但是,即使是在中國市場上發生的高端消費,受益者卻大都是國際精品品牌。 一方面,中國制造已經逐步開始走上高質量發展道路;另一方面,在品牌打造上,許多企業的理念仍然落後,甚至把借助資本跑馬圈地、擊鼓傳花的遊戲當做必經之路。 中國企業需要怎樣的品牌戰略?觀察者網就這一話題采訪國際精品品牌戰略研究院院長盧曉,以下為訪談實錄:
觀察者網:上次我們在訪談中已經談到了,中國要打造精品品牌是有市場空間的。随着中國高端制造業的發展,以及新時代年輕人對國産品牌的信心越來越強,我們已經看到有一部分國産高端品牌出現。
同時,最近我們也看到一些國際奢侈品牌,在中國市場上有一些不太合适的行為,民間輿論對他們有一些批評的聲音,應該說,随着中國這些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我們的消費需求、消費層次已經得到很大的提升,那麼中國的品牌,有沒有準備好呢?
盧曉:應該說大部分中國品牌還沒有準備好。
日本軟件公司Monstar Lab最近的調研數據顯示,2020年起始,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全球奢侈品市場萎縮23%,但中國内地市場份額幾乎翻了一番,從去年的約11%增長到2020年的20%,成為全球奢侈品行業反彈增長的關鍵引擎。中國的奢侈品銷售額的線上滲透率從2019年的13%左右增長到2020年的23%,整體線上渠道銷售額增長約150%,這種增長已經持續多年。
原因顯而易見,首先,因為疫情使許多中國人無法到海外的精品店消費,所以把消費都留在了國内;其次,精品消費的價格逐漸出現了海内外拉平的現象;第三,在海外和香港都不太能去的情況下,海南打造自由貿易港,成為一個新的精品購物旅遊的好去處,度假勝地的優勢得到特别的彰顯。

三亞國際免稅城内
疫情把中國真實的消費能力展現了出來,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即使是在中國市場上發生的高端消費,受益者卻大都是國際精品品牌。中國的精品品牌是缺乏的,“中國制造”的精品供應能力是落後的。
為什麼中國到了必須要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階段?因為要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各個消費領域都必須有中國公司提供的高端産品,其他國家的生産能力無法滿足這樣龐大的需求。
這同時也是中國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心重塑的過程。
觀察者網:您看好中國的高端産業和精品市場的發展嗎?
盧曉:我十幾年前就預言,中國的高端品牌一定會崛起,這與我的個人經曆有一定的關系。
上世紀90年代,我考入當時最熱門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但畢業後沒有像很多同學一樣立刻投入風起雲湧的市場大潮,而是繼續讀了企業管理方向的研究生,到盧森堡的一個中國投資基金項目實習,協助資方盡職調查。
中國加入WTO前夕,法國高等商學院(ESSEC)校長來華講學,我由此得到赴巴黎繼續深造的機會,在選擇研究方向時,我考慮,要選擇一個當時歐洲很強、中國很弱,但國内發展又必然繞不開的領域,最後選定了國際精品品牌管理的方向,進行博士階段的研究工作。


盧曉早年在法國講學
我當時的想法也朦朦胧胧,我認為,中國1949年建國後,一直在補1840年以來落下的現代化功課,到2000左右時其實已經取得巨大的進步,将來中國的制造業企業一定會走向國際的高精尖水平,那麼在品牌塑造和管理方面,就會有這方面的需求。
在20多年前我是這麼想的,當時不被很多人理解,哪怕現在,很多人仍然不理解,有時候我跟别人談高端品牌塑造,對方會回答“我們正脫貧攻堅呢”,但是,現在中央顯然已經定下了高質量發展的方向,也有一些企業已經走上了這條路。
作為一門管理學科,國際精品品牌管理非常前沿,至今隻有大約20年的曆史,當時在法國也是剛剛起步,起初我連導師都沒有,後來路威酩軒集團成立,在自身發展過程中發現存在大量(家族)中小企業如何整合做強,以及建立精品品牌管理的迫切現實需要,才與巴黎高商合作建立了研究中心。
我的研究方向則是探索中國制造企業如何從小做大,建立精品品牌。我和我的導師,以及同門師兄弟姐妹們共同創建了國際精品品牌管理理論體系,目前我是這個領域獲得博士學位和做理論創建工作的唯一的亞洲人。所以在這方面,中國與全球幾乎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
我還想借機會澄清一點,很多人看到我們這個領域都是“奢侈品”,以為我也是搞奢侈品的,其實我要搞的是适應目前和将來中國高精尖制造業發展的國際精品品牌戰略。

國際精品品牌(管理)作為一個學科的曆史實際上隻有約20年,期間,路易威登和古馳是兩大“霸主”
觀察者網:那麼據您觀察,目前中國高端産業的發展有沒有回應您的期待?
盧曉:其實有些領域已經起來了,比如說手機行業有華為走在前面,OPPO、 vivo等品牌也正在努力;汽車行業,有小鵬、蔚來這些“造車新勢力”逐步崛起,但是像化妝品、珠寶、服裝這些大類,走精品道路的中國品牌發展就慢一些,數量也比較稀少。關鍵看這個領域中的龍頭企業是否在走高質量發展國際精品道路。
因為手機和汽車的制造門檻本來就比較高,行業集中度也較高。而化妝品、珠寶、服裝這些大類在國内市場的從業人員是以銷售端為主,之前主要做外國品牌代理,賺取一些渠道費用,有的是做山寨貨出身,現在即使想往研發端、制造端發展,也往往困于比較低端的市場,行業嚴重内卷。
這些行業中有一部分企業确實想往高端品牌發展,卻遇到瓶頸,因為高端是一個體系,從産品的材料、顔色、款式、工藝、高級美感、精細化工、服務等等各個維度都必須做到高精尖,這就需要先進的理論體系做支撐。在我的“國際精品品牌戰略”理論中,用“精度”的概念來表達高端化的程度。

2021年凱度Brandz(國際知名品牌資産研究機構)最具價值中國品牌排行榜
觀察者網:上次訪談中您也提到,中國的市場體量足夠大,但是對于做高端品牌來說,這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是有足夠的市場容量,但另一方面,這讓大量的中低端企業非常容易存活,隻需要找到一小塊細分市場就能夠活得很滋潤,而不必往行業高端去費力攀登。
盧曉:是的,我把這樣的發展稱之為“二維”發展,也就是在低附加值的前提下拼命擴大産量,這就是一種求面積的做法,中國的市場面積足夠大,所以低附加值的“二維企業”特别多,在這樣的市場上,隻要開出成百上千家店面,即使利潤很薄也可以上市,甚至隻要是有足夠的營收,哪怕利潤率是負的,也可以上市。
觀察者網:這是一種資本無序擴張的打法,某些企業家通過一個“故事”說服資本,通過資本燒錢在某一塊市場“跑馬圈地”。
盧曉:作為一些資本來說,并不在乎這個故事是真是假,隻在乎在這個故事破産之前找到買家全身而退,這是一個擊鼓傳花的遊戲,資本隻需考慮不接最後一棒。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多例子,這對于社會資源配置來說,是一種低效。
那麼,我要強調在上面這個“二維”發展模式上,增加一個衡量維度:精度。
而且,這種“精度”必須是一種“國際精度”,也就是說在今天的全球化水平之下,所有有志向的中國企業都不能隻滿足于做一個“中國最好的品牌”,而必須以身處中國的全球企業自居,做發源于中國的,追求國際最高水準的品牌。
一旦有中國企業能夠達到國際最高端的精度,那麼就能夠得到最高的附加值,背靠中國這樣一個大市場,“二維”面積本已足夠大,再加上高度,就是一個“三維”發展模式,原先是求面積,現在是求體積,利潤空間迅速打開。一旦由中國企業做到“三維”,那麼就會成為一個巨大的“收割機”,很多其他國家的大企業依靠一些存量技術積累的市場優勢會被迅速打破。而且,這個過程是不可逆的,我們已經在鋼鐵、造船、港口機械、高鐵等很多行業中看到過這種情況發生。
如果,再加上第四個維度:時間,也就是說在一段長時間内,都要動态地堅持在市場覆蓋的基礎上追求精度,那麼這種“四維”發展模式就會對其他企業造成“降維打擊”。所以到這裡你就明白了,我搞的國際精品品牌戰略是一個四維的動态理論。
實際上,在中國市場上做這樣的“四維”發展是效率最高的,中國的市場體量足夠大,經濟發展速度足夠快,高端消費需求迅速湧現,現在國家又提出“高質量發展”戰略,有足夠的政策支持,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齊備,隻看我們的“一把手”企業家有沒有這樣的格局去攀登。
觀察者網:為什麼要強調“一把手”的重要性呢?
盧曉:因為“一把手”是企業的第一責任人,如果“一把手”對這個問題沒有足夠的認識,沒有把它作為整體戰略通盤考慮的話,是無法實現系統性提升的,隻靠下面的品牌部門、設計部門、市場部門、廣告部門各自為戰,無法提升一個企業的整體格局。
就我接觸到的企業家來說,很多是從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發家緻富的,有的對當時的發展模式有路徑依賴,有的有很強的“小富即安”意識,有的被今天市場上充斥的“資本遊戲”邏輯所迷惑,許多“一把手”的認識高度是不夠的。
無論是華為的任正非,還是小鵬汽車的何小鵬,蔚來汽車的李斌,他們都有追求成為全球領先企業的格局,這不但體現在口頭上,還要體現在行動上。
與之相對的是“跟随者”戰略,追求小富即安,達到行業平均精度,得到行業平均水平的利潤,但這是市場上大部分人都能做的,很容易出現“内卷”現象,因為這是一個完全競争市場,要維持平均利潤水平非常困難,會不斷有人壓低利潤,甚至會不斷有得到資本加持的“攪局者”賠錢也幹,擾亂市場。
某些資本隻關心财務數字,對于産品“精度”并不在乎,隻要把營收做高,擊鼓傳花尋覓下一個買家。相應的,一些設計師或企業家雖然口頭上對投資人說要追求“精度”,做世界一流,但是在産品設計上并沒有實際行動,反而經常把“某某投(資)了我”挂在嘴邊,這隻是一種與資本互相欺騙的遊戲。
我也曾經勸過一些企業家,在經曆了資本主導的迅速擴張後,現在已經出現了很多退潮後裸泳的案例,跑馬圈地是不可持續的,是否沉下心來夯實一下自己的品牌基礎呢?可惜這種建議不會為很多“上升期”的企業家接受,真的到了上升階段停止了,往往已經來不及了。
觀察者網:這種模式是我們不看好的,那麼,這些靠資本燒錢擴張,卻沒有高端追求的品牌,對真正的高端品牌是否會有威脅呢?
盧曉:如果這些高端品牌不做低端市場,一般就沒有威脅,原因很簡單,由奢入儉難,如果沒有大的變故,今天的中國人都很難回到上世紀70年代改革開放前的生活,而習慣了高端産品品質的人,很難再用回低端的産品。
從産業端來說,高端品牌是可以向下兼容,做一些低端産品的,但低端品牌向高端攀登要難得多。
觀察者網:有沒有資本會意識到這種模式的不可持續,而與有追求的企業家相互吸引呢?
盧曉:有的,一些更高層面的資本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已經脫離了純财務的層次,會追求一些更複雜的,附加值更高的項目,甚至追求一些更高層面的社會目标,這樣的資本,往往是一些有産業背景的資本,它們比較容易與我們的國際精品品牌戰略産生共鳴。
觀察者網:我們之前在采訪中得到過一些例子,比如從事一些電子産業和IT行業的人,過去幾十年來一直習慣于美國引領整個行業,每10年更新一代,但是到了2010年,突然發現美國巨頭們失去了動力,沒有在物聯網領域繼續引領時代向前,反而依靠自身壟斷地位遏制創新,阻礙技術進步。
盧曉:是的,這種現象現在已經比較明顯了,并不是說某些領頭企業不前進,時代就會停滞,有些曾經強大的企業衰老了,背叛了将其帶到今天的地位的那種精神,躺在壟斷地位上身不由己,企圖把所有人跟自己一起拖入墳墓。
但這是徒勞的,時代是滾滾向前的,比如曆史上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将東西方的交流阻隔數個世紀之久,但其他人會前赴後繼,會沖破這種阻力,爆發更強勁的動力。阻力一旦被沖破,阻隔者就灰飛煙滅。腐朽賣國的滿清閉關鎖國是另一個例子,最近的例子是香港一些頑固分子,他們反對修建港珠澳大橋,還認為中國内地開放必需走香港這條唯一通道,這些都是不可持續的。
美國在之前的200年具有的前進動力,同樣是一種相對于當時曆史更進步的格局推動的,但現在已經把當時的志向全部丢掉了,一個比較顯性的現象是“印度化”,大量印度裔開始把持美國的上層建築,“種姓制度”這種封建固化的思維開始占據上風,這代表着今天的美國精神已經迅速衰朽,成為一種阻礙進步的力量。
回到品牌上,舉例來說,今天的酩悅·軒尼詩-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 Moët Hennessy,英文簡稱LVMH)集團裡,既沒有“路易”也沒有“威登”,因為在精品品牌道路上的真正傳承,傳承的是精神而非血統,不斷有後繼者向珠穆朗瑪峰上接力攀登。
今天,像美的、格力、海瀾之家、安踏、太平鳥等等許多中國企業仍然非常努力,甚至煥發出全新的生命力,也有一些企業和企業家是昙花一現的,關鍵在于這些企業有沒有矢志不渝地走在向“精品”攀登的道路上,讓自己的研發-銷售-變現-研發的循環不斷持續。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内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将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