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57 年 3 月 8 日,美國紐約的紡織女工為抗議不平等的工作環境和低薪走上街頭。随着女權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國際婦女節于 1975 年 3 月 8 日确立。作為女性運動的主體,“婦女”仿佛自帶着一種被固化的女性形象,對此,美國女性主義研究者朱迪斯·巴特勒用她的理論警示我們對“婦女”身份的誤用。
在她的早期著作《性别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颠覆》的第一章節中,她質疑了人們對婦女主體本身的理解方式,指責女性主義在為了滿足政治意義下作出的粗糙表達。在她看來,“婦女絕不是一個穩定的能指……即使在複數的情形,它也是一個麻煩的詞語、一個争論的場域、一個焦慮的起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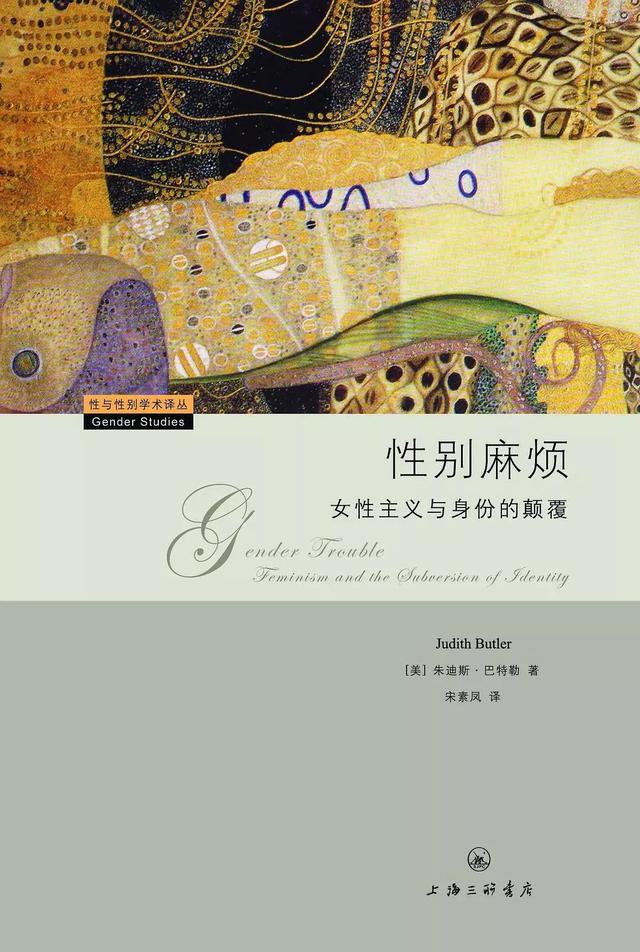
《性别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颠覆》
[美] 朱迪斯·巴特勒 著
宋素鳳 譯
上海三聯書店 出版

“婦女”作為女性主義的主體
大體來說,女性主義理論假設存在有某種身份,它要從婦女(譯者按:涉及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政治範疇的“women”譯為“婦女”,而在第二章、第三章精神分析話語及其他語境中則譯為“女人”。)這個範疇來理解,它不僅在話語裡倡議女性主義的利益和目标,也構成了一個主體,為了這個主體追求政治上的再現。然而,政治(politics)和再現(representation)是争議性的詞語。一方面,在追求拓展婦女作為政治主體的能見度與合法性的政治過程中,再現作為一個運作的框架;另一方面,再現是語言的規範性功能,被認為不是揭露、就是扭曲了那些關于婦女範疇我們所認定的真實。對女性主義理論來說,發展一種全面或是足以再現婦女的語言,對促進婦女的政治能見度似乎是必要的。有鑒于在廣泛的文化情境裡,婦女的生活不是受到錯誤的再現,就是完全沒有得到再現,這點顯然益形重要。

朱迪斯·巴特勒在演講中
近來,這種普遍存在的認為女性主義理論與政治之間具有關聯的觀念,從女性主義話語内部遭到了挑戰。對婦女主體本身的理解方式,不再限于穩定或持久的框架。有大量文章對“主體”作為再現——更确切地說是解放——的終極代表的可行性提出了質疑;但是,對于什麼建構了、或者應該建構婦女範疇,這些文章彼此之間極少有一緻的意見。政治和語言再現的領域先設定了一套主體形成的标準,結果隻有被認可是主體者才能得到再現。換句話說,必須先符合作為主體的資格才能得到再現。
福柯指出權力的司法(juridical)體系生産主體,然後又再現這些主體。司法性的權力概念似乎以完全負面的方式來管控政治生活——也就是說,通過一些具有曆史偶然性、并可以撤回的選擇的運作,對與那個政治結構相關的個人進行限制、禁制、管制、控制,甚至“保護”。然而受到這些結構管控的主體,由于它們服從于這些結構,因此是根據這些結構的要求而形成、定義以及複制的。如果這樣的分析是正确的話,那麼把婦女再現為女性主義“主體”的語言與政治之司法建構,它本身就是話語建構的,是某種特定形式的再現政治的結果。結果女性主義主體成了那個原本應該是推動其解放的政治體系的一個話語建構。如果這個體系證實了是根據一種統治的分化軸線來生産性别化的主體,或是生産那些被認定為男性的主體的話,那麼從政治上來說這就大有問題。在這樣的情形下,不加批判地訴諸這樣的一個體系來“解放”婦女,顯然是自砸陣腳。

米歇爾·福柯,法國哲學家和思想史學家、社會理論家、語言學家、文學評論家、性學大師
“主體”的問題對政治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特别是對女性主義政治,因為司法主體一律是通過某些排除性的實踐生産的;這些排除實踐在政治的司法結構建立完成之際就不再“彰顯”。換句話說,主體的政治建構是朝向某些合法化以及排除的目的發展,這些政治運作被某種把司法結構當作基礎的政治分析給有效地遮掩以及自然化(naturalization)了。司法權力無可避免地“生産”了一些東西,而宣稱它隻不過是再現它們而已;因此,政治必須關注權力的這個雙重作用:司法的與生産的。事實上,律法生産“律法之前的主體”這樣的概念,而後又将之隐藏,為的是把這個話語結構當作一個自然化的基本前提調用,然後用它合法化律法本身的管控霸權。隻探讨如何使婦女在語言和政治上得到更充分的再現是不夠的;女性主義批判也應當了解“婦女”這個範疇——女性主義的主體——是如何被生産,同時又如何被它賴以尋求解放的權力結構本身所限制。
事實上,婦女作為女性主義主體的這個問題提出了這樣的可能性:也許并沒有一個在律法“之前”的主體,等待在律法裡再現,或是被律法再現。也許主體,和對一個時序上“之前”(before)的調用一樣,都是被律法建構的,作為律法取得合法性的一個虛構基礎。關于普遍存在的認為律法之前的主體具有本體完整性這樣的假定,也許可以這樣理解:它是自然本質的假設——亦即那構成古典自由主義司法結構的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t)神話——殘留于當代的痕迹。對一個非曆史的“之前”的一再操演調用,成為保證人的前社會本體的一個基礎前提;而個人在自由意志下同意被統治,從而構成了社會契約的合法性。
然而,除了支持主體概念的基礎主義虛構以外,女性主義在假定婦女這個詞代表了一個共同的身份這方面,也遭遇了政治上的問題:婦女絕不是一個穩定的能指,充分得到了它要描述和再現的對象的同意;即使在複數的情形,它也是一個麻煩的詞語、一個争論的場域、一個焦慮的起因。如同丹尼斯·瑞裡(Denise Riley)的書名《我是那名字嗎?》所暗示的,這個提問正是從這個名詞可能有的多重意指産生的。如果一個人“是”女人,這當然不是這個人的全部;這個詞不能盡攬一切,不是因為有一個尚未性别化的“人”,超越他/她的性别的各種具體屬性,而是因為在不同曆史語境裡,性别的建構并不都是前後一貫或一緻的,它與話語在種族、階級、族群、性和地域等範疇所建構的身份形态交相作用。因此,“性别”是不可能從各種政治、文化的交會裡分離出來,它是在這些交會裡被生産并得到維系的。

1914 年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的德國海報
認為女性主義必定要有一個普遍的基礎,而這個基礎是建立在一個所謂跨文化的身份上的政治假設,通常伴随着這樣的概念:對婦女的壓迫有某種單一的形式,可以在父權制與男性統治的普遍或霸權結構裡找到。近年來普遍父權制的概念廣泛受到批評,因為它不能解釋性别壓迫在它們存在的具體文化語境裡是如何運作的。這些理論是考慮到了各種不同的語境,但這不過是為一個從一開始就預設的普遍原則,尋找一些“例子”或“例示”而已。這種形式的女性主義理論建構受到批評,不僅是因為它試圖殖民、竊用非西方文化,用以支持一個高度西方化的壓迫概念,也因為這些理論有建構一個“第三世界”、甚或一個“東方”的傾向,在其中性别壓迫很微妙地被解釋為一種本質的、非西方的野蠻性的症候。女性主義急切想為父權制建立一種普遍性的特質,以強化女性主義所宣稱的它具有代表性的表象,有時候這促使了女性主義者過于急功近利地祭出統治結構在範疇上或是虛構上的普遍性,而據此生産婦女共同的屈從經驗。
雖然普遍父權制這樣的主張已經不再像當初那麼具有公信力,但是想要置換由這個框架推演出來的結果,也就是關于“婦女”的設想有某種普遍的共通性這樣的概念,一直是要困難得多。當然,已經有很多相關的辯論:婦女之間是不是有某種共通性,而且是先于她們的壓迫?或者,是否單單她們的壓迫經驗本身,就足以使“婦女”之間有某種結盟?婦女的文化是不是有某種獨特性,獨立于迫使她們臣服的霸權、男權文化之外?婦女的文化或語言實踐的獨特性與完整性,是否總是以某個比較優勢的文化結構為參照,因此也局限于這個框架?有沒有“獨特的女性”這樣的領域,它不僅因此與男性領域區分,而且在這樣的差異裡,它可以從“婦女”的某種未标記的、假定的普遍性上辨識出來?男性/女性的二元分立不僅成為使那獨特性可以被辨識出來的獨一的架構,并且在所有其他方面,它也使得女性的“獨特性”再度完全脫離了語境,而在分析上以及在政治上,與階級、種族、族群等建構,以及其他建構“身份”、同時也使單數的身份概念成為錯誤命名的權力關系軸線分隔開來。


曆史上的女權運動
我認為一般所假定的女性主義主體的普遍性和統一性,實際上因為它所賴以運作的再現話語的種種限制而有所松動。過于急促而不成熟地堅持主張有某種穩定的女性主義主體——理解為一個嚴絲合縫的婦女範疇,必然造成對這個範疇多重的排拒。即使這建構是為了解放的目的而精心設計的,這些排除的領域還是顯示了這個建構的強制性與管制性所造成的後果。的确,女性主義陣營裡的分歧,以及矛盾地來自“婦女”——女性主義宣稱它所代表者——對它的反對,顯示了身份政治必然具有一些局限性。有人建議女性主義可以試圖擴大它所建構的主體的再現範疇,但反諷的是,由于這樣的提議拒絕考慮這些再現主張的建構性權力,結果使得女性主義的目标面臨了失敗的危險。以純粹“策略”的目的而訴諸婦女範疇的做法,不會使這個問題得到改善,因為策略總是有超出它們意圖的目的之外的意義。在這裡的情形,排除就可以算作這樣一種無意為之而适得其反的意義。為了符合再現政治上女性主義必須表達一個穩定的主體的要求,女性主義因此使自己受到了粗糙的錯誤再現的指責。
顯然,我們的政治任務不是拒絕再現政治——好像我們可以做得到一樣!語言和政治的司法結構構成了當代的權力場域;因此,沒有一個理論立場是外在于這個場域的,我們隻能對它自我合法化的實踐進行某種系譜學的批評。基于這樣的情況,重要的出發點如馬克思所說的是曆史的當下。我們的任務是在這個建構的框架裡,對當代司法結構所生産、自然化以及固化的身份範疇做出批判的論述。

2017 年 2 月 7 日,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女性舉行“無上裝”遊行示威,要求平等和婦女權利
或許在這個文化政治的關鍵時刻,在一些人所說的“後女性主義”的時代,我們有機會從女性主義觀點的内部,對建構一個女性主義主體這樣的指令進行反思。在女性主義的政治實踐中,我們必須從根本上重新思考本體論的身份建構,才能夠設想出一種可以在其他基礎上複興女性主義的再現政治。另一方面,為了使女性主義從必須建構一個單一或持久的基礎這樣的必要性裡掙脫出來,我們也到了該考慮某種激進批判的時候了,因為單一或持久的基礎不可避免地會遭到一直被它排除于外的那些身份位置、或是反身份位置的挑戰。把女性主義理論建立在“婦女”作為主體這個概念上的排除性實踐,是否悖論地破壞了女性主義拓展它所主張的“再現”這個目标?
問題也許要更為嚴重:把婦女範疇建構為一緻的、穩定的主體,是不是對性别關系的一種不明智的管控和物化(reification)?這樣的物化不是正好與女性主義的目的背道而馳嗎?在何種程度上,婦女範疇隻有在異性戀矩陣(the heterosexual matrix)的語境下才獲得穩定性和一緻性?如果穩定的性别概念不再是女性主義政治的基本前提,我們現在也許可以期待某種新的女性主義政治來挑戰性别和身份的物化,這種政治形式将把可變的身份建構當作一個方法上和規範上的先決條件——如果不是一個政治目标的話。
追溯那些生産并隐藏合格的女性主義司法主體的政治運作,正是一種探讨婦女範疇的女性主義系譜學的任務。在我們質疑“婦女”作為女性主義主體的努力過程中,可以證明不加置疑地調用這個範疇,使女性主義作為一種再現政治的可能性從一開始就被排除了。把再現的對象擴及一些主體,而這些主體的建構是建立在排除那些不符合對主體的一些心照不宣的規範要求的主體之上,這有什麼意義呢?當再現成為政治唯一的重心時,這在不經意間維系了什麼樣的統治與排除的關系?女性主義主體這個身份不應該成為女性主義政治的基礎,如果主體的形成是在一個權力場域裡發生,而由于對這個基礎的主張,這個權力場域在一般的規律下是被掩蓋的話。也許非常悖論地,隻有不再一味認定“婦女”這個主體的時候,才能夠顯示“再現”對女性主義是有意義的。

編輯丨是鴨
圖片來自網絡
點擊上圖,購買全新上市的《單讀 19 :到未來去》

▼▼“再現”這個目标。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