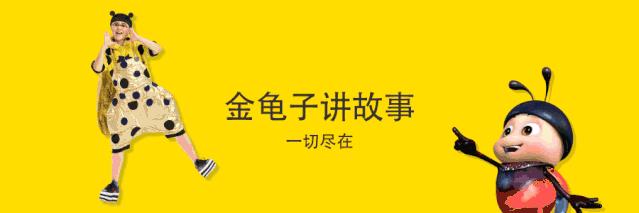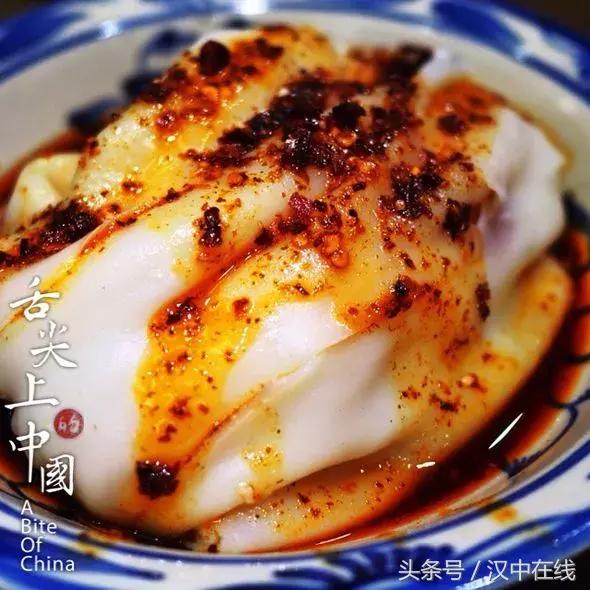圖為朱安
“我寄給你的信,總要送往郵局,不喜歡放在街邊那綠色的郵筒中,我總疑心那裡會慢一點。”這句廣為流傳的情話出自魯迅先生的《兩地書》,收錄了魯迅與愛人許廣平的書信往來,可以說是魯迅與許廣平的愛情見證。
提起魯迅與許廣平,大多數人的腦海中都會浮現出情比金堅、伉俪情深、天作之合等詞語。
1923年,魯迅與許廣平相識于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當時,魯迅受邀到北平女師大講學,就這樣,成為了大二學生許廣平的老師,并最終走到了一起。
魯迅與許廣平的相識相戀,無疑是一段令人豔羨的童話故事,但現實永遠不會像童話那樣完美。早在魯迅跟許廣平相識之前,他就已經有了妻子。

圖為魯迅
魯迅的這位“妻子”名為朱安,是魯迅家裡安排的結婚對象。魯迅與朱安的結合,其實就是被無數人唾棄和诟病的包辦婚姻。
朱安出生于1878年6月,同魯迅一樣,也是浙江紹興人。她家祖上曾做過知縣一類的官,家境還算殷實。
雖沒上過學,但性格溫和,端莊賢良。按照過去的眼光,算是一位标準的“賢妻良母”式的女子。魯迅的母親魯瑞,便想讓這位女子做自己大兒子的妻子。
周、朱兩家很快就定下了這門婚事,約定等到魯迅從南京學成歸來,二人便完婚。

圖為魯迅與許廣平及兒子
但身為“後來者”的我們知道,魯迅從南京畢業後,又去了日本留學。這樁婚事也就随着魯迅的留學,暫時被擱置了。
在日本讀書的魯迅,很快接受了新思想的影響。他不能違背自己的内心,接受這樁封建的包辦婚姻。為了不耽誤朱安另嫁,他及時給母親魯瑞寫了信,勸家裡拒絕這門婚事。
魯瑞很快回信,說這門婚事是她自己求來的,怎麼能推掉呢?更何況,一旦悔婚,周家跟朱家的顔面又該往哪裡放?而且在那個年代,如果一個女子被夫家悔婚,那這個女子基本上就等于被判了死刑。不論她本性如何,樣貌好壞,以後都很難再嫁出去了。

圖為魯迅與朱安
母親不同意,魯迅又是個大孝子,他最終隻能同意了這門婚事。但接受這門婚事前,他對朱家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讓朱安“放足”,二是讓她“上學堂”。
然而他自己也說過,“改造自己,總比禁止别人來得難。”
長期被封建禮教束縛的朱家自然是不同意他的提議的。“三寸金蓮”是女子美的象征,“女子無才便是德”,也要求女子不能進學堂。在他們看來,魯迅的提議,無疑是荒唐且有違綱常倫理的。
見朱家不同意,魯迅别無他法,隻能待在日本,想用這種方式,讓朱家放棄跟自己的婚約。
就這樣,等到魯迅在日本讀了四年書,時間也就來到了1906年。那年魯迅25歲,朱安已經28歲了。
紹興有一條規矩,“養女不過二十六”,眼看着女兒已經28歲了,魯迅卻遲遲不回國,朱家人開始着急了。這時的魯瑞也坐不住了,便給魯迅寫了信,騙他說自己病重,讓他趕快回國。

圖為魯迅
接到母親的來信,魯迅十分擔心,很快回了國。等到了家,才知道母親是裝病騙他回來結婚的。沒有辦法,魯迅隻能選擇跟這位素未謀面的朱姑娘成了婚。
婚禮當天,魯迅戴着紅纓大帽,裡面還拖着一條長長的假辮子。他站在花轎前接新娘,穿戴着傳統婚禮服飾的朱安從花轎上下來。
朱安知道自己的丈夫不願讓自己裹小腳,為了不被反感,她還特意穿了大碼的鞋子,但是由于鞋子不合腳,下花轎時鞋子竟然從腳上掉了下去。她小小的“三寸金蓮”,還是被魯迅看到了。
“魯迅先生結婚是在樓上,過了一夜,第二夜魯迅先生就睡到書房裡去了。印花被的靛青把魯迅先生的臉也染青了,他很不高興。”周家的傭工王鶴照這麼說。

圖為魯迅
印花被的靛青把臉都染青了,這無疑是魯迅把臉埋進被子裡哭所導緻的。
試想,一個接受了新式思想,終其一生都在反封建的人,卻沒有逃脫封建的包辦婚姻,魯迅先生心裡,該有多麼不甘和痛苦啊!
可是,痛苦的隻有魯迅一人嗎?顯然并不可能。
新婚之夜,桌上的喜燭還搖曳着燈火,牆上還貼着大大的“喜”字,本該是人生中最為溫馨甜蜜的時候,卻隻有新娘一人獨守空房。這個時候,朱安又該是多麼無措哀傷呢?
可是,在那個年代,朱安會怪罪丈夫嗎?她不會,她隻會迷茫,自卑,認為是因為自己不夠好,才得不到丈夫的喜愛。

圖為魯迅
封建式婚姻像是牢籠,魯迅不能讓自己就這麼被禁锢,他要逃,要反抗。
婚後僅僅三四天,魯迅便返回日本,繼續求學了。可從小受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思想影響的朱安,她想不到要逃,她也無處可去。她能做的,隻有守好嫁進來的這個家,照顧好自己的婆婆。
就這樣,苦等了七年婚姻和愛情的朱安隻能目送魯迅離開,連句挽留的話都沒法說出口。
“早早起,出閨門,燒茶湯,敬雙親,勤梳洗,愛幹淨,學針線,莫懶身,父母罵,莫作聲……”這是朱安從小學習的《女兒經》,她也的确是這麼按照書裡做的。
在魯迅離開後,她恪守自己作為一位妻子的職責,用心照顧和供養婆婆。每天洗衣做飯,忙裡忙外,在一日複一日的枯燥中,等待着自己的丈夫。

圖為朱安
1909年,魯迅終于從日本回國。
朱安也終于在長達十年的等待中看到了一絲希望,她以為這回她能跟丈夫安安穩穩過相夫教子的日子了。但是魯迅回國後,并沒有如她期望的那樣,而是到處東奔西跑。就連夜裡,也會挑燈抄寫古籍,與她相處的時間非常短,更不要說像普通夫妻那樣親近了。
就這樣,從紹興到北京,雖然朱安一直跟在魯迅身邊,但兩人始終沒有親近。就像有着夫妻之名的陌生人,雖共處在同一屋檐下,卻連最基本的交流都很少。
魯瑞遲遲抱不上孫子,便去問朱安原因。朱安沒有辦法,隻能老實回答,是魯迅不同她親近。

朱安與魯瑞
在魯瑞看來,這是很沒有道理的,她認為朱安是一個很好的兒媳。于是便私下裡這樣問魯迅,“朱安究竟有何不好?你為何不願意跟她親近?”
面對母親的詢問,魯迅是這樣回答的:“不是什麼不好,而是和她談不來。和她談話沒味道,有時還要自作聰明,不如不談。”
魯迅為什麼說朱安“自作聰明”呢?這裡有必要提這麼一件事。
某天,魯迅心情很不錯,便多跟朱安說了幾句話,跟她聊起了日本的一種東西,說很好吃。
朱安聽後,便道,“是的,是的,我也吃過的。”
但實際上,那時的中國根本沒有這種東西,朱安怎麼能吃得到呢?
她這麼回答,難怪魯迅要說她是在“自作聰明”。

圖為魯迅上海故居
可是朱安知道,魯迅對她不喜,這麼平平常常的一次對話,她不知道要等多久。
她難道不明白自己的“小聰明”會被魯迅識破嗎?可她還是這麼說了。為了什麼?不就是為了能跟他多說幾句話,拉近一下夫妻間的距離嗎?而且,她始終以丈夫和婆婆為先,自己又舍得吃什麼好東西呢?
在磚塔胡同時,魯迅曾生過一場大病。那時他剛跟弟弟周作人鬧翻,幾乎把全部身家都留給了弟弟,經濟并不是很寬裕。但是朱安沒有半點抱怨,就踩着那被魯迅厭惡的小腳,東奔西走地為他抓藥請醫生,衣不解帶地照顧他。

圖為魯迅八道灣故居
“大師母每次燒粥前,先把米弄碎,燒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買糟雞、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平時喜歡吃的菜,給大先生下粥,使之開胃。她自己卻不吃這些好菜。”魯迅當時的鄰居俞芳曾這樣說道,這裡的“大師母”指的就是朱安。
默默對他好,把一切好東西都留給他,朱安就是這麼對待那個始終不喜歡自己的丈夫的。她見識不多,隻能用自己的方式思考,覺得隻要自己始終對他好,終有一天,魯迅會覺察到她的好。
就像田野裡的向日葵,默默地向着太陽,為它獻出飽滿的瓜子仁,期望得到它的回應,但卻沒有考慮到太陽到底喜歡什麼,也許它更喜歡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或者是傲立寒冬,不屈不撓的臘梅。

圖為朱安及其娘家人
1923年,許廣平出現了。許廣平開放、獨立,她敢于反抗,向往自由。她就像潔身自好的荷花,也像不畏嚴寒的臘梅。
許廣平跟魯迅其他女學生一樣,她們都剪着齊耳短發,穿着校服短衫,朝氣蓬勃,敢想敢說。在這些開朗青春的女學生面前,朱安就好像一件毫無生氣的舊物件。
她也曾試過改變自己。隔壁院子裡住着俞家的一對姐妹,她們時常來找魯迅讨論學術問題,朱安聽不懂,便隻能做些端茶遞水的活兒。
她曾央求過俞家姐妹教她做體操,期望自己也能變得有活力一些,但是有些動作她又覺得太過“不雅”,做起來時總是束手束腳,看起來及其不和諧。見她們留着代表“新思想”的短發,便想着也要把頭發剪短,但“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她又覺得剪發于禮不合。
總之,她做了諸多嘗試,魯迅卻還是離她越來越遠,并最終跟許廣平一起離開北京,去外地生活了。

圖為魯迅西三條故居
魯迅離開後,魯瑞又被留給了朱安一人照顧。他很少回來,即使偶爾回來一次,也不過匆匆見母親一面,跟照顧自己母親的朱安,卻連話都不願說。
為一個根本不愛自己的丈夫守着家,還要辛苦照顧他的母親,這種日子無疑是十分艱難且無趣的,但朱安其實是有兩次機會遠離這種艱難無趣,回紹興老家安度晚年的。
第一次是從紹興搬去北京。
魯迅當時在北京的八道灣買下一處院子,想把一家人接到北京生活。那時朱安已經四十多歲了,就算跟魯迅去了北京,生活其實也不會發生什麼改變。而且她這一走,很大可能就再也無法回到故鄉了。
她自己也是明白的,臨行前還跟娘家人照了照片。但在她心裡,丈夫就是她的天,即使對娘家十分不舍,她依舊選擇跟魯迅離開。

圖為許廣平與兒子
第二次是他們搬到磚塔胡同之前。
那時魯迅曾找她談過話,讓她自己做一個選擇。她可以選擇留在八道灣,或者回到紹興老家。如果她願意回紹興,每月會寄錢供養她的生活。
魯迅并沒有給她跟自己一起走的選項,顯然就是告訴她,讓她不要再跟着自己了。
她難道不明白魯迅的意思嗎?可是在她看來,已經出嫁的女兒,是沒辦法再回到娘家的。既然她嫁給了魯迅,就願意一輩子跟着魯迅。生做周家的人,死做周家的鬼。這也是父母一直教她的道理。

圖左為朱安
于是,為了自己的丈夫,她就這麼去了異鄉。
現在,魯迅有了自己的愛人,跟愛人一起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了。朱安卻被留在了北京,終日照顧年邁的婆婆。
1936年,魯迅在上海離世。消息很快傳給了朱安。作為妻子,她的第一反應是去上海幫丈夫料理後事。可是,她如果去了上海,年邁體弱的婆婆怎麼辦呢?
自從她嫁進周家,到現在已經三十年了,長久的陪伴和照顧,讓她跟婆婆的關系早已親如母女,她怎麼放心就這麼撇下婆婆離開呢?
思來想去,朱安最終選擇留在北京,接待前來為魯迅吊唁的親朋好友。

圖為魯迅
此後又過了許多年,朱安一直跟婆婆一起住在北京的西三條。失去了丈夫的她更加全心全意地照顧婆婆,直到魯瑞壽終正寝。
從嫁進周家到婆婆離世,朱安幾乎是獨自一人,走完了這漫長的37年。
在這三十多年裡,她獨自照顧着婆婆,把魯迅該盡的孝也一起盡了。她是否有過後悔和埋怨,是否感歎過命運不公,這些都無從得知。但我們知道的是,這些本該丈夫做的事,她都毫無怨言地一并做了。

圖為魯母
婆婆去世後,朱安隻能獨自生活在西三條了。她沒有按照婆婆的囑咐,接受周作人給的生活費。
魯迅生前就跟周作人不和,她怎麼能不考慮魯迅,接受周作人的錢呢?因而她隻能靠着魯迅好友們的接濟過活,日子過得十分拮據。

圖為周作人
在生命的最後那段時間,朱安有一個最大的願望——與魯迅合葬。魯迅雖然不喜她,但那是她拜了堂的丈夫,在一個封建女子心中,死後也一定要跟丈夫在一起的。
為此,她還托人給許廣平寫了信,希望她可以幫助自己完成這個願望,但是,魯迅先生早已不再隻是她的丈夫,又怎麼能同她合葬呢?許廣平隻能婉拒了她。
1947年6月29日,69歲的朱安走完了她寂寞的一生。

圖為魯迅、許廣平和兒子
她被孤獨地葬在了西直門外的一處墓地,與魯迅合葬的願望到最後也沒有實現。後來,她的墓地遭到破壞,被夷為了平地,至今也不知她魂歸何處。
生的時候無法同丈夫親近,連死後也不能同丈夫合葬。朱安這一生無疑是孤獨悲凄的,她稱自己是魯迅的“遺物”,魯迅卻說,她隻是母親送給自己的“禮物”。
雖從未得到過魯迅的認可,卻固執地守着“妻子”的名分,朱安無疑是封建的、無知的,但作為兒媳和妻子,她無愧于周家,無愧于魯迅。

圖為魯迅墓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