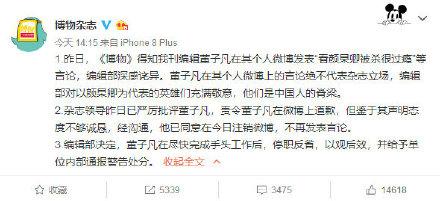顧恺之(約345—406年),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今江蘇無錫)人。顧恺之多才多藝,在詩賦書法和繪畫上都有很高的造詣,當然最突出的還是他的人物畫成就。這一成就使他不僅在魏晉南北朝人物畫族群中出類拔萃,鳌頭獨占,而且對後世也有巨大影響,堪稱曆代楷模。在這方面,他與書聖王羲之在書法領域中所享有的藝術地位是十分類似的。
考察顧恺之的人物畫,大緻可以依據如下兩種材料:一是作品本身。雖然顧恺之的人物畫作品皆為後世之摹本,但這些摹本基本上體現了顧恺之人物畫的面貌和水準。另外,南北朝的一些壁畫作品亦可作為參證。二是後人對顧恺之及其繪畫作品的各種評價以及顧恺之本人所發表的繪畫見解,這兩種材料相互結合和對照,可以較好地把握顧恺之人物畫的真實風貌。
考察顧恺之人物畫的語言特征和風格境界,可以首先集中于他的“線條”運用。那麼,顧恺之人物畫的線條有什麼特點呢?從傳世的《洛神賦圖》《女史箴圖》《列女智仁圖》及《斫琴圖》等作品來看,其線條大都為舒緩、綿勁而細長—這與漢代帛畫人物的線條品格是一脈相承的。顧恺之正是在此基礎上加以發揮和創造,使線條顯得更加遒勁而富有韌性,更加舒展而從容不迫,更加宛轉而趨于精微完善。有學者認為,顧恺之的線條“圓而轉”,可能受到當時篆書中鋒用筆的影響,是有一定道理的。從上述作品的線條性狀來看,其運筆在控制中,速度比較緩慢,但卻毫無滞澀之感,從而呈現出均勻、圓轉而又自然的筆調,這與篆書的确是相通的。後來明代詹景風在評價他的《洛神賦圖》時說,“其行筆若飛而無一筆怠敗”,“亦似遊絲而無筆鋒頓跌”。還有人用“春雲浮空”“流水行地”“春蠶吐絲”等語來形容顧的用筆(線條),可謂形象而貼切。特别是“春蠶吐絲”四字,将顧恺之用筆(線條)之“綿”“緩”“韌”“細“圓”“轉”的特點很好地揭示出來了。

東晉·顧恺之
洛神賦圖(宋摹本)(局部)
絹本設色
縱27.1 厘米
橫572.8 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顧恺之人物畫用筆及風格特點集中地體現在《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中。《洛神賦圖》有唐人和宋人兩種摹本。我認為唐人的摹本應該更接近顧恺之的畫風。作品中描繪了衆多的人物形象—其衣紋飄帶、面容手足乃至山石樹木和雲水,完全是以細勁、綿長的線條勾勒而成的。《女史箴圖》中的人物描繪,線條更加細健、圓轉而飄逸。顧恺之的人物畫以“神”取勝,對此後世有不少論述。如唐代張懷瓘說,“象人之美”“顧得其神”。還說:“神妙無方,以顧為最。”大詩人杜甫則賦詩曰:“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張彥遠在評價顧恺之所繪的“維摩诘像”時,說他能成功地表現出“清羸示病之容,隐幾忘言之狀”。明代何良俊在評價顧恺之的《女史箴圖》時說,“此神而不失其自然”“皆有生氣”。顧恺之自己也反複強調要“以形寫神”,要“傳神寫照”。很顯然,要做到“傳神”,首先須着眼于人物儀容風貌的刻畫。顧恺之之所以能夠以“神”取勝,應該和他人物畫的用筆(線條)特點有很大的關系。對此,張彥遠在《曆代名畫記》有一段相關論述,值得仔細地研讀:
顧恺之之迹,緊勁聯綿,循環超忽,調格逸易,風趨電疾,意存筆先,畫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曆代名畫記·論顧陸張吳用筆》)

洛神賦圖(局部)
所謂“緊勁聯綿”,就是前文所說的“春蠶吐絲”。這種用筆特點除了表現為“綿”“韌”“細”“圓”“轉”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征狀,這就是“緩”。然而這裡的“緩”之義與張彥遠所說的“風趨電疾”卻是相牴牾的,如何解釋這種牴牾關系呢?應當說,就顧恺之的運筆速度而言,可能是“緩”(慢)的,猶如春蠶吐絲,徐徐而出,否則就不會做到謝赫所說的“筆無妄下”“格體精微”。縱觀顧恺之《洛神賦圖》等一系列作品,不難發現,他那種從容不迫、綿緊而韌勁的筆調顯然是“疾”筆無法做到的,可以想見畫家在用筆(線條)進行人物造型時一定是“意存筆先”且“運思精深”的。但就線條本身的性狀—或者說,就用筆而産生的視覺感受而言,則不一定是“緩”,而完全可以形成一種“風趨電疾”的審美效果。在這一點上,顧恺之的線條既不同于兩漢的帛畫—其運筆緩,且視覺效果也緩。也不同于兩漢的一些壁畫和漆畫一味的奔放快疾。毋甯說,顧恺之人物畫的用筆(線條)乃是“緩”與“疾”的對立統一。 也就是說,顧恺之的線條既有“綿”“韌”“圓”“緩”的一面,又有“細”“緊”“轉”“疾”的一面;它是“春蠶吐絲”“春雲浮空”的,又是“流水行地”“風趨電疾”的。前者偏于“靜”,後者偏于“動”,是“靜”(緩)與“動”(疾)的對立統一。而當線條之運行與人物那種飄逸的身姿、飛舞的裙帶融為一體時,其“緩”(靜)的一面仿佛隐而不覺了,而“疾”(動)則以非常強烈的趨勢和傾向展現出來了,這就是張彥遠所說的“循環超忽,調格逸易”。用筆做到這點,人物情态當然會越發見出風采和神氣。這都表明,人物畫的神氣不僅見于眉目容貌的描繪,而且也在于筆墨運用中所煥發而出的風力格調—它托舉着人物的造型并循環、彌散在四周。所以張彥遠說:“骨氣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歸乎用筆。”概言之,線條的美感以及與之相關的人物姿态和服飾,在表現人物之“神”上都具有重要的輔助作用。宗白華曾指出:中國人物畫“在衣褶的飄灑的流動中,以各式線紋的描法表現各種性格與生命姿态”。顧恺之将此稱之為“助神”,他說,“服章與衆物既甚奇,作女子尤麗衣髻,俯仰中,一點一畫皆相與成其豔姿”,“作人物骨成而制衣服幔之,亦以助醉神耳”。應該說,服飾(“服章”“衣髻”)有“助神”之功,而描繪服飾的線條(“一點一畫”)也有“助神”之能。反之,如果畫家在審美創造中忽視線條的作用,忽視線條在人物造型(“形骨”、“豔姿”)中特殊的輔助作用,那麼人物之“神”的表現将是很不充分的,按照張彥遠的話來講,就無法做到“全神氣”。

洛神賦圖(局部)
與此相關的乃是顧恺之人物畫造型的“疏體”和“密體”問題。所謂疏、密二體,就是指人物畫造型中線條構成的疏密程度。繼顧恺之之後,陸探微的人物畫就是一種“密體”;而張僧繇以及唐代的吳道子則表現為一種“疏體”。張彥遠曾指出:“若知畫有疏密二體,方可議乎畫。”他還将顧、陸二人并稱為“筆迹周密”之“密體”代表,而将張、吳的“離披點畫,時見缺落”劃為“疏體”範疇。其實,陸探微(“密體”)和張僧繇(“疏體”)都是從顧恺之那裡變化、發展而來的。因而如果顧恺之純乎“密體”或純乎“疏體”,那麼陸、張兩人的“疏密”之體必有一者難以溯源。我認為,顧恺之的人物畫的語言構造雖以“密體”為主,但同時還包含了“疏體”因素,是疏密二體兼而有之。例如他的《洛神賦圖》《女史箴圖》就明顯是“密體”,其線條如春蠶吐絲,連綿不已,與“疏體”那種“離披點畫,時見缺落”的樣式是大相徑庭的。這種“密體”的形成乃緣于衛協的影響,衛協之“精”在顧恺之的手中發展為更加完善的“精密”。與此相對照,顧恺之《列女仁智圖》中的有些人物造型則傾向于“疏體”,其“線條”構造也不像上述兩幅作品那樣細密連綿,而是呈現出剛健、疏朗之像。這與衛協那種“不該備形似”、以“壯氣”見著的畫風可能也有一種淵源關系。所以後來的理論家和藝術家對顧恺之人物畫有兩種評價。如謝赫說顧恺之的繪畫“格體精微”,明代詹景風說顧恺之的繪畫“精古而雅秀”,“婦人衣飾金裝極精麗,使人目駭心驚”。這些評價表明“密體”乃是顧恺之人物畫一個非常重要的審美特征。但還有另一種評價。如宋代黃伯思評顧恺之的《列女仁智圖》說“此圖簡古”;“略其玄黃,取其驵雋,惟真賞者獨知之”。元代湯垕評顧恺之人物畫時說:“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有或失,細視之,六法兼備,有不可以語言文字形容者。”這些評語乃是對其“疏體”特征的很好說明。後來明代詹景風在指出顧恺之人物畫“精古而雅秀”的同時,又說其“俊爽而雅勁”,并認為兩者“不妨并傳也”。可見顧恺之人物畫确有兩種(“疏密”)體系。如果聯系到他“用筆”上的特點來看,其緩筆則往往為“密體”,為“格體精微”;而“疾”筆則可能傾向于“疏體”,傾向于“簡古平易”和“俊爽而雅勁”。

東晉·顧恺之
女史箴圖(唐摹本)(局部)
絹本 設色
縱24.8 厘米
橫348.2 厘米
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上述所闡發的用筆(線條)特點以及“疏”“密”二體構成了顧恺之人物畫“語言”的基本樣式。但是必須看到,任何語言樣式都不是孤立的,它總是隸屬于、服務于人物造型(形象)的,而且隻有統一于人物的造型,它才會獲得審美價值和意義。顧恺之人物畫的語言和造型正是這樣一種水乳交融的關系,并且在這一基礎上形成了顧恺之人物畫所特有的風格面貌—高古。
對于這種高古的風格面貌,後世不少理論家和藝術家都有論述。唐代張彥遠将顧恺之的繪畫(“顧陸之迹”)視為可與“上古”并齊的“中古”風格。其“中古”一詞雖然是一個時間概念,但所謂“中古質妍相盡”,則指出了它的風格内涵,表明顧恺之的人物畫在内容(質)和形式(妍)上達到了和諧完滿的統一,“高古”的氣象正是從這種統一中煥發出來的。明代詹景風說顧恺之的《洛神賦圖》“高古神奇”“精古而拙”“意緻潇灑”。清代李葆洵說顧恺之的人物畫“古樸渾論”,有“古拙之趣”。清代吳升說顧恺之的《女史箴圖》:“此圖畫既高古。”清代安岐也說《女史箴圖》“筆法位置,高古之極”、“洵非唐人所能及也”。可見,“高古”乃是顧恺之人物畫風格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征。
顧恺之人物畫“高古”風格的形成首先得之于他的線條(用筆)特點。他那綿韌、細勁、若遊絲一般的線條所構成的密體,蕩漾着一種春雲浮空、令人忘塵的“高古”格調和氣象。顧恺之的人物畫在着色上雖然濃豔,但整個調子仍然純粹而統一,仿佛是從人物造型以及線條中自然生發出來的色相,而不是某種外在的藻飾。明代詹景風說顧恺之的繪畫“着色雖濃豔而清澈于骨”。元代湯垕、夏文彥等人也說顧恺之“傅染人物容貌,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藻飾”,“不求暈飾”。這表明,顧恺之人物畫的着色同樣展現了清澈自然的“高古”境界。

女史箴圖(局部)
從造型上來看,其人物的綽姿意态之間也流露出一種“高古”的風範。清代葉德輝說顧恺之的人物畫“猶存漢石室石阙畫像遺意”。李葆洵也這樣稱贊顧恺之,“虎頭妙筆絕古今”,“古樸渾論,類漢畫石”。的确,顧恺之人物畫在造型上明顯帶有漢代畫像石(磚)那種圓渾質樸的遺風。如《列女仁智圖》,人物衣袖寬袍的處理是那樣飽滿充盈,呈現出漢代畫像石(磚)人物畫常見的圓弧形的張力與渾樸。《洛神賦圖》右邊尾端那一組人物的面容描繪,也與漢代畫像石(磚)那種橢圓造型相當接近。當然,顧恺之的人物畫造型并不是漢代畫像石(磚)的簡單翻版,事實上,畫像石(磚)那種厚重的造型質感在顧恺之這裡已為其飄逸的形态所取代。有些作品(如《女史箴圖》)的人物造型和姿勢更富微妙變化,并呈現出一種清瘦修美的面貌,初現後來“秀骨清像”之倪端。但從總體上看,顧恺之的人物畫與漢代畫像石(磚)在造型結構上多有契合貫通,經過顧恺之重新錘煉和創造,終于形成了一種“高古”的風格範式。這種風格範式對後世人物畫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前面談到,顧恺之人物畫十分強調“傳神”。他認為,眼睛的刻畫對于“傳神”具有關鍵作用(“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之中”)。此外他還有一個重要見解,即認為人物環境的描寫對于“傳神”也起着一種特殊的作用。顧恺之說:
凡生人無有手揖眼視,而前無所對者,以形寫神而空其實對,荃生之和乖,傳神之趣失矣。空其實對則大失,對而不正則小失,不可不察也,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對之通神也。(《論畫》)

東晉·顧恺之
列女智仁圖( 宋摹本)(局部)
絹本 設色
縱25.8 厘米
橫470.3 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這就是講,畫家所描繪的人物,不能脫離一定的環境(“所對者”),否則就不可能達到“傳神”的目的,即所謂“空其實對”,“傳神之趣失矣”。而且不僅不能“前無所對”,同時也不能“對而不正”—畫家必須在審美創造中注意到人物與環境之間的微妙的呼應關系,這就叫做“悟對通神”。顧恺之這些見解十分精彩,這是繪畫實踐的深刻總結。他的《女史箴圖》《洛神賦圖》《列女仁智圖》,都是“悟對通神”的典範之作,如《女史箴圖》中的漢武帝與班婕兩人關系的描繪就是如此。圖中班婕端莊伫立,漢武帝則在車辇中回首相招,這不僅很好地表現了“班婕有辭,割歡同辇”的情節,而且将漢武帝和班婕各自的心理狀态(“神”)在這種難舍難分而又堅辭同辇的關系中非常生動地揭示出來了。該圖卷尾的兩位偕行的女子,體态綽約,相顧而語,眉目之間,神氣相融。《列女仁智圖》中的人物幾乎都是兩兩相對,或俯或仰,或正或側,或招呼或回應,其衛靈公與靈公夫人“悟對通神”的情狀更是意韻連綿,缱绻不已。
以上所說的環境(“所對者”)乃是指人際關系。此外,顧恺之的人物畫還十分注重自然環境的描寫,這同樣關系到人物之“神”的傳達和表現。如畫名士謝琨,置于“丘壑”之中,這樣才能将他那超凡脫俗、寄情山水的人生情态(“神”)完整地展示出來,而《洛神賦圖》更是這樣一幅代表作品。圖中人物“披羅衣之璀粲”,“曳霧绡之輕裙”,柔情綽态,轉盼流精。随着長卷徐徐展開,布列如織的山巒、佳木、流水等自然景物如漢畫中的祥瑞一樣籠罩着每個人物,從而使畫面洋溢着一種難以言喻的美妙而迷離的氛圍,人物神氣則在這種氛圍中悠然恍惚地彌漫開來—此乃顧恺之在對人物與自然環境描繪中所營造出來的意境之美。正如唐代張懷瓘在評顧恺之繪畫時所說:“雖寄迹翰,其神氣飄然在煙霄之上,不可以圖畫間求。”《洛神賦圖》的構圖也頗具匠心,人物安排錯落有緻,時前時後,忽聚忽散,既有節奏感,又有秩序感。自然物象與人物相互穿插而又渾然一體,圖中所描繪的遠山、遠水及上空的飛禽與近景若即若離地拉開了層次和距離,從而使人們在視覺上産生了一種縱深感。畫面的中後部分,視野逐漸疏曠開朗,境界變得杳渺而空闊,主人公對洛神的眷戀不舍、惆怅無着之情仿佛随着空闊的境界而顯得茫茫無垠而遙不可及。“忽不悟其所舍,怅神霄而蔽光”,“攬騑辔以抗策,怅盤桓而不能去”。應該說,顧恺之以其視覺語言極為出色地诠釋了《洛神賦》所蘊含的濃郁的詩意。
顧恺之在人物畫上的貢獻是巨大的,他的成就和影響是當時許多畫家—無論是顧恺之之前的曹不興、衛協、荀勖,還是顧恺之之後的陸探微、張僧繇、曹仲達和楊子華,都難以與之争雄。所以唐代李嗣真說“顧生天才傑出,獨立亡偶”,“思侔造化,得妙物于神會,足使陸生失步,荀侯絕倒”。很顯然,顧恺之的出現,為中國人物畫的發展昭示了更加明确的審美方向,中國人物畫的審美品格在顧恺之手中變得更加清晰起來,達到真正成熟和完善的水準。顧恺之是魏晉南北朝人物畫族群簇擁出來的最璀璨的巨星,他的繪畫成就是經先秦、秦漢長期藝術曆史培植而成的藝術奇葩,他從繪畫實踐中提取和總結出來的美學觀點,與謝赫“六法”一樣,堪稱千古精論,影響深遠。
本文來源《中國人物畫史》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