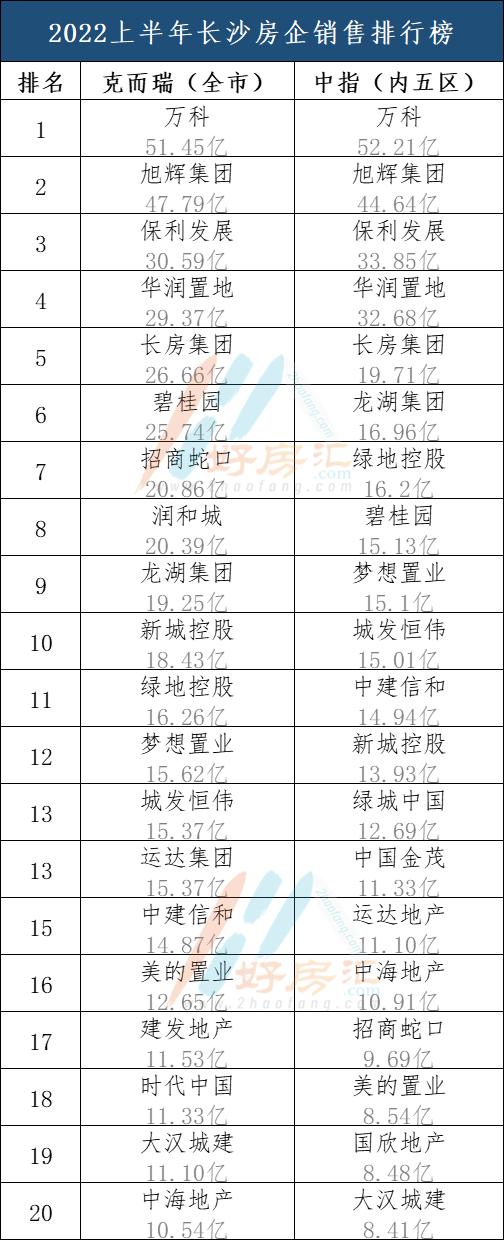人們常說:父愛如山。養不教,父之過。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保證小孩成才的關鍵所在。網友周志輝的文章發人深思。本文作者:周志輝
我最後一次挨父親耳光那天正好是我30歲的生日。

那時,我已是一所中學的教導主任,女兒剛滿周歲。生日那天中午,我有許多朋友去了我老家,其中有深圳的老馬,還有老盤、功滿、老海與我一些要好的同事。
中午的聚餐是幸福而快樂的,大家喝酒說笑,無拘無束,那是一種忘乎所以的快樂。酒酣耳熱之餘,老馬激情滿懷,手握幾雙筷子做話筒狀,一馬當先做起節目主持人。老海是當時的文化館長,蓄着魯迅式的胡子,瘦削的臉型也很有些魯迅的樣子。老海筆名季婁,取意為有禾有米、有子有女,當然也包含有紀念魯迅的意思。老海即席賦詩,是那種比打油詩文氣也講究些格律的詩,描繪了即時快樂的氣氛。老盤,江湖人稱盤哥,是現已經偃旗息鼓、但仍然名噪夷江兩岸的酒協會長。盤哥醉眼迷離,乘興高歌一曲《一無所有》。功滿,盤哥旗下酒協少掌門,他一曲京劇清唱《打虎上山》,赢得了滿堂喝彩。
我欣喜地接受着朋友們熱情的祝福,陶醉在生日興奮的快樂當中。喝的是本地茅台,不是很正宗的米酒,家鄉石床名聲在外的曲子酒。這種本地茅台喝多了以後又口幹又上頭,但令人窘迫的是,好酒沒的喝,又不能不喝酒,喝開了也就是好酒。
那時候,我們這幫子朋友在一起,基本上是不醉不罷場,酒場子鬧起來比戲場子還鬧然,拍桌敲碗猶如铙钹齊奏,唱聲、笑聲、喝彩聲聲聲振耳,那場面在外人看起來還真有點鬼哭狼嚎、群魔亂舞的樣子。

然而,就在我們盡情快樂時,不經意間出了一個緻命的疏忽,那就是冷落了我脾氣暴躁的父親。
中午的酒宴沒有請他出面,他獨自一人關在房間裡喝悶酒,一直到我朋友離開,他沒有走出房門半步。等到我們一家人吃晚餐的時候,母親叫他出來,他沒有吭聲。母親要我去叫他,我說了一句别管他。就這麼一句話惹怒了他,他突然沖出來,照我臉上就是一耳光,然後怒吼道:誰要你管?一個鳥教導主任,有什麼了不起。
那一刻,全家人瞠目結舌,我更是不知所措。頃刻間,一股怒火從我心頭生起,我跨步上前就要揪父親。突然間,我見已經明顯比我矮小了的父親往後一退。這一退,我霎時驚詫了,突然間止住自己難以抑制的沖動,而一種頹然的悲怆或悲怆的頹然驟地湧上心頭,摻雜着憤懑與愧疚的淚水嘩地蹦出眼眶。白發蒼蒼的父親顫抖着身子站在我的面前,飽經滄桑的父親一下子顯得那麼蒼老。
我一時怔住,立在父親面前一動未動,父親也立着一動未動。那不是一種對抗的僵持,而是一種情感不知所措的凝固。母親先反應過來,她沖過來隔在我們父子之間,厲聲質問父親:你為什麼打人?你怎麼無緣無故打兒子?父親一言不發。這時候,我妻子發起難來,她大哭着走向父親問道:你打他,是不是也要打我?一個父親當着媳婦的面打自己沒有過錯的兒子,不就是要打給媳婦看,你憑什麼教訓他,憑什麼教訓給我看?妻子一連串的發問,父親僵立在那兒無言以對,臉上的表情是難以言狀的苦楚。
妻子一把拉住我說,我們走,這個家沒法讓人呆了。一家人慌了神,亂着一團。外婆與我女兒哭,外公唉聲歎氣,弟妹或噤聲或啜泣,母親好言相勸妻子,妻子不依不饒。父親在混亂中走進他的房間,嘭的一聲關上房門。直到我們第二天離開家時,也一直沒有見到他的面。

我30歲生日那天父親的一記耳光,結束了我挨父親耳光的曆史,也似乎結束了我弟妹們挨父親耳光的曆史。小時候,我與弟妹們都挨過父親的耳光,到底挨過多少次已無法記憶,誰挨多挨少也無法說得清楚。事實上,我們很少與父親生活在一起。
父親忙于他的政事,極少回家。但就算是很少回家,他每次回家都會因為我們的淘氣調皮或無端哭鬧而發脾氣。我們五姊妹都挨過父親的巴掌。父親的巴掌不是橫飛到臉上,就是直擊屁股。飛到臉上的,小臉上便爆出指印;擊落在屁股上的,那是火辣辣的疼。
我依稀記得,一次我追着要跟他去縣城,他一時火起,一把将我從自行車後座上拎起來就往地上扔,我幾乎被扔出一丈遠的地方。母親追過來,以為我小命不保了,誰知道就在父親跨上單車走了不遠,我爬起來再一次奮不顧身地去追,父親回過頭看了我一眼,加快了單車的速度。

父親粗暴的教育方式,讓我們在他面前都噤若寒蟬,也使我們小心翼翼地長大成人。父親信奉的就是不打不罵不成人,棍棒底下出孝子。直到如今,他依然将我們五姊妹能健康成長、不惹事生非以及聽話孝順,歸功于他嚴厲的教育方式。事實上,都已長大成人的我們五姊妹,沒有一個繼承父親的粗暴性格,在各自的工作崗位和生活圈子裡,都是與人為善,生怕惹上麻煩與糾纏。
當然,我們都知道,這不僅是由于父親的嚴厲,更主要的是外公對我們的循循善誘,他從來就不在我們面前發脾氣,總是說道理,用各式各樣的道理說服教育我們,像和煦的春風一樣滋潤溫暖着我們幼小的心田。父親的粗暴和外公的和善所形成的鮮明對比,讓我們在反感父親的同時,更主動地學會了友善,更深刻地體會到尊重人的重要和可貴。

長大後,我曾無數次思考過關于父親耳光的意義問題。我隻能認為,父親的耳光是一種天賜的懲戒,具有父命難違的權威性和不可抗拒的威懾力。我們可以承受父母雙親有理或無理的耳光,除此之外,任何來自其他方面的耳光對于我們都是一種不能忍受的恥辱,這是生命生存的哲學。
父親的耳光把父愛對子女的庇護用極端的方式表露出來,其用意就在于不好好做人就會挨打。父親的耳光大多是因為恨鐵不成鋼而引發,他的正面意義就在于催人上進,隻要落後于人就要挨打。父親的耳光更深刻的生命哲學,可能出于自古以來物競天擇适者生存的人生法則,那就是作為長輩認為自己的後人與其被人欺侮,不如自我訓誡;與其為惡他人,不如自我懲救。這是一種自私的愛,一種悲憫的生命情懷,一種被許多人所摒棄又被許多人所仿效的禮教傳統,一種難以根絕的中國式家庭教育方式。

我與朋友談起教育孩子的事情。一位朋友說,他有一次氣得要打自己的兒子,1米75的他揚起手,手至半途,發現要打着1米85的兒子,必須擡高自己手的角度。打起來已經很費勁了,他高揚起的手在空中停滞,然後無力地垂落下來。另外一位朋友說起他妻子打自己兒子的故事,妻子打了兒子一耳光,兒子說,媽媽你已經打過我了,不能再打了。妻子氣不過,揚手再打的時候,兒子伸出雙手輕輕一擋,做媽媽的抵擋不住跌坐于地。兒子笑着說:媽媽,我要你莫打啊,你偏要打。說着一把拉起又氣又無奈的母親,做母親的隻有哭訴着說:兒啊,我是為你好啊。在我們湘西南,一直流傳着這樣一句俗話:爺(方言,指父親)不打攀肩膀的崽,娘不打會梳頭的女。現在的父母,極少用耳光或棍棒教育子女了。記得我女兒剛上小學時,一次我教她拼音,她不用心,我輕輕一巴掌拍在她屁股上,女兒很委屈很傷心地望着我哭,那一刻我心裡是揪心的痛。我想起父親的耳光,我突然強烈地意識到我不能用巴掌教育我的女兒,我隻能用愛心去教育我唯一的女兒,我隻能用寬廣仁厚的父愛去呵護女兒的成長。從那以後,我沒有用一根指頭對待過我的女兒。

人們常說父愛如山,但在我的體會中,沒有挨過父親耳光的兒女是難以真真理解父愛如山的寓意。我至今沒有埋怨過父親的耳光,相反我一直懷念父親留給我的最後一次耳光,我始終認為那是一種天賜的懲戒,是為人兒女者必須承受的生命的痛楚。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