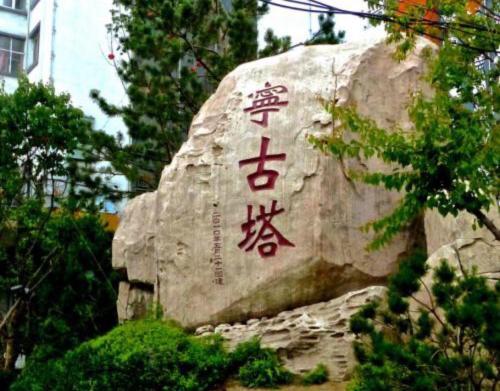友人見拙文《生煎脞談》,便慫恿我寫《鍋貼脞談》和《小籠脞談》。我回複說,生煎鍋貼一文一武,我是不喜歡吃鍋貼的。鍋貼的長相就比較兇,有尖尖的兩個角,吃起來很容易“紮”到嘴唇,也很容易将其中湯汁随意射出,甚是不雅。錢锺書說“偏見是思想的放假,它不是沒有思想的人的日常家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天的娛樂,假如我們不能懷挾偏見,随時随地必須得客觀公平、正經嚴肅,那就像造屋隻有客廳,沒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裡照鏡子還得做出攝影機頭前的姿态”。
我和小籠的故事總是從這裡開頭的。

常年來,家母一直不時念叨我小時候胃口之好。讀小學時早飯就要吃三兩小籠加一碗蛋皮湯。我小學的地址在雲南中路三十五号,現在的延安高架邊港陸廣場的後面。這個大廈的原址是上海針織二廠門市部,邊上就是一爿“南翔小籠店”。那時候的小籠每兩十二個,母親提到的事情大概發生在我一二年級的時候,因為我已經記不清了。大概也是在那個時候,我有一次在書場裡遇到夏夢,她還說我這麼小年紀就來聽書了。這也是媽媽告訴我的,我已經沒有記憶了。
最近一次吃小籠是疫情前在山陰路萬壽齋。十幾年前,在魯迅公園山陰路側門有一家“魯藝書場”我還經常去聽書,就知道了萬壽齋和邊上的光頭生煎。去之前還在魯迅紀念館逛了一圈,特地等到一點左右才去萬壽齋,以免排隊,即使這樣服務員還是忙忙碌碌。萬壽齋小籠一兩八個,十元,咖喱牛肉湯八元,已經是十分廉價了。我正好和同去的黃師聊到近來寫的一篇文章《古風》,列舉諸項已經消失的“古風”。當三兩籠小籠上桌,我下意識地和服務員說,請給我兩個碟子,她卻睬都不睬。黃師說“自己去拿,這是‘古風’”。
萬壽齋的小籠味道好,且皮較厚是我喜歡的類型。缺點是“顔值”不高。小籠上的褶大概要在十二到十八個之間,我以前一直以為要有二十四個,暗合二十四節氣。在故宮裡的一些圓形欄幹上就是做出二十四個皺褶,以暗合二十四節氣的。
兒時每次到嘉定南翔古猗園春秋遊,總要去邊上的小籠饅頭店大快朵頤。近來那裡的小籠雖有所退步,但是進門那股噴香的酸醋味道已經說明了一切,要知道在上海大部分的小吃店,裡面的酸醋多是兌水的,以至于我長期以來到家附近的小吃店,總是自己帶醋。南翔太遠,上海豫園裡的南翔小籠店就能嘗到美味。那裡常年排隊,原本不大的店堂裡更是摩肩接踵,每桌上都是臨時拼桌的食客。一次和幾位朋友一起看完在豫園舉辦的徐三庚藝術展後就去吃那裡的小籠,拼桌的是一對中年夫婦。我的一位朋友正巧說到齊白石等人的書畫,那對夫婦就和我這位朋友聊起來了,最後對他說“白相有啥白相頭,要自家買呀”。
鼎泰豐是台灣著名的小籠店,像那裡的“高記生煎”一樣,都與我們熟悉的味道不一樣,而台北的朋友一直以為這就是正宗的味道。我十年前第一次到台北,就嘗了鼎泰豐。那家店在一家叫“金石堂”書店的樓上,後來得知是鼎泰豐的老店。之後一次陪母親去台北,到的是一〇一大廈樓下的鼎泰豐,見到了他們家那塊招牌,原來是于右任手書。有一年的上海書展我有幸和老師以及滬上前輩篆刻家共同在主會場簽名售書,午飯就請遠道而來的朋友在展覽中心對面的上海商城吃鼎泰豐,當時點了各色小籠還有其他菜肴。我為山東的朋友點了花雕酒,飯店裡還拿來了雪白的骨瓷執壺和酒杯,朋友戲稱這麼喝酒是“文吃”。
長期以來我們所謂的小籠都是“南翔”小籠,是“鹹口”,而無錫小籠是“甜口”的,且一兩隻有兩個,個頭較大。在無錫有一家叫“錫盛源”的名店。這三個字讀成“錫長源”,“盛”字讀成“長短”的“長”。上海曾經有一家賣帽子的名店叫“盛錫福”,也讀成“長錫福”。(施之昊)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