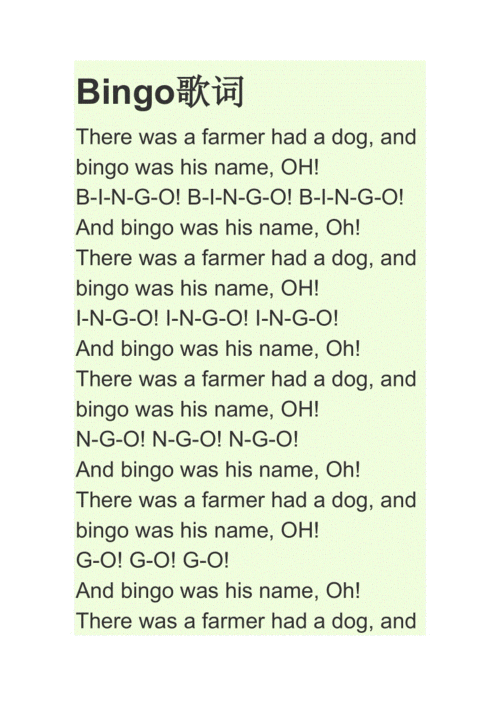我的父親母親34集電視連續劇? 引子這是王家的故事,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我的父親母親34集電視連續劇?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引子
這是王家的故事
故事裡裝着父輩們的心酸與苦辣
父親母親是本飽含哲理的書
年幼的我們常常讀不懂
直到真正長大
重新打開這本書
卻已是淚如雨下
我的父親母親
自序
春去秋來,寒來暑往。轉眼之間,父親離開我們已經快十年了,母親也已經85歲高齡,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晖。想起父母艱辛的一生,才體會到窮盡自己的所有也報答不了父母的養育之恩。雖然歲月匆匆,時光流逝,對父親的思念及對母親的愧疚卻與日俱增。
這個世界上,最珍貴的是父母與兒女之間的親情。這種親情是上天與生俱來的,她給予我們更多的是繁瑣的斷斷續續的回憶,當風雨來襲時,總有人為你撐着一把傘;當寒冬降臨時,總有人為你披上一件暖暖的棉襖;當你出門晚歸時,家裡總有一盞小小的燈為你而亮着;當你遠行時,總有一雙眼睛時刻注視着你。這就是我所理解的親情。暖在心裡,刻在骨子裡。成為抹不去的永遠的回憶。
半夜醒來,回憶起父母親當年的歲月,我就碾轉難眠。 父親母親的勤勞、善良、堅韌、 艱苦拼搏、勇于擔當的一生,值得我們永遠回憶。父親去世的第二年,就想寫篇回憶父親一生的文章。這個念頭存在我腦海中已經很久了,想把父親的樣子描繪得深刻點,以免自己忘記。用質樸的語言勾畫出父親艱難曲折和剛毅的一生。可能是因為瑣事太多,不能靜心的緣故吧。直到今年父親去世九年了,才有機會寫出《憶我的父親》這篇文章,給姐姐看,姐姐對我說,給父親和母親寫個小傳吧,貢獻給家族和後輩欣賞,希望老王家的兒女添磚加瓦,家庭幸福,事業有成,共享天倫之樂!
我也一直想寫這樣的一篇傳記,寫給父親母親,也寫給自己。也許是很久沒有動筆了,真的寫時才覺得難度很大,也許我的文筆不是那麼流暢,但我想重要的是我對父母的情感是從我的心靈深處順着我的筆尖流出,父親,母親便是我筆尖上綿長的回憶!
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父親和母親,有一天他們終将離我們而去,無論相隔多麼遙遠,我們和父親母親之間的親情,都将在我們的心中永遠長存。在這個春暖花開的季節,我用愛和思念編織成最美的華章,獻給我的父親和母親,獻給我的家!
苦難的童年和少年
父親王凡星農曆1936年10月初10出生于邵東崇山鋪鄉幸福大隊嫁吉小組仁厚堂—一個貧窮偏僻的小山村。适逢國家内憂外患的年代,父親于農曆2013年6月27日歸于塵土。我的祖母一共生育了五個子女,父親排行第二,上有一個姐姐,下有三個弟弟。母親尹秀英1937年農曆11月12日出生于邵東縣崇山鋪鄉寶善大隊餘慶堂,母親至今已經85歲高齡,雖然已至耄耋之年,但耳聰目明,還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的外婆養育了六個子女,母親在六兄妹中排行老大,下面有二個弟弟和三個妹妹。父親已經離開我們快十年了,但父親陪我們走過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父親勤勞、樸實、節儉、有責任,有擔當。在任何風雨和艱難險阻面前從來不畏懼、不妥協。母親善良、仁慈、寬厚、明事理、吃苦耐勞。父親母親的這些優秀的品質至今仍然深深影響着我們姐弟。 父親是老王家出生的第一個男丁,祖父祖母自然格外開心。祖父勤勞樸實,誠實守信;祖母心地善良,勤儉持家。祖父的家風非常嚴謹,他特别喜歡吃苦耐勞能幹的。父親是家裡的長子,祖父的教育是直接的,也是非常嚴厲的,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父親年齡尚小時,祖父就會安排我的父親幫家裡分擔繁重的勞動。清早就被祖父叫起來去耙雞糞,狗糞,當時這些都是田裡和土裡主要的肥料來源,如果去晚了就會被别人耙走。耙完雞屎回到家裡已經是八九點了,父親匆匆忙忙吃完飯就要趕到田間地頭去割豬草和魚草,一把鐮刀和一個背簍就是父親割豬草和魚草的全部裝備。父親滿山遍野地去找合适的野菜,然後佝偻着腰去割,再放進背簍裡,要想割滿滿滿的一筐那可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情,畢竟還得漫山遍野地找。有時一根根滕刺藏在野草裡看不見,父親的手掌常常都是傷痕累累。豬雖然對吃的要求并不高,但是也不是什麼草它都吃的,特别是有些有毒的草一定認識,否則豬和魚吃了就有性命之憂。祖父做事非常精細,自然對待我的父親也很嚴格,祖父交代的事情父親總是一絲不苟的完成。父親後來對待工作高度負責、嚴以律己的精神。嚴謹細緻的态度,精益求精的作風,都得益于祖父良好的家風。祖父養了一頭牛,每天黃昏,父親就去放牛,放牛看似簡單,其實很有學問,那時農村的地很金貴,到處都種滿莊稼,沒有太多的空地,放牛隻能在小路邊或沿河兩岸,這些地方放牛割草的也多,草并不茂盛,往往放幾個小時。牛隻能吃個半飽。父親放牛有時要欠到很遠的水草茂盛點的地方,等牛吃飽了,再把牛牽到水塘邊讓牛喝飽水,已經是晚上七八點了。父親十二歲就幫家裡去賣自家做的爆米花糖,瘦弱的身子挑着幾十斤的爆米糖要賣到離家幾十裡外的地方。三斤稻谷換一斤米糖,米糖賣完了,父親的肩膀上就變成了沉重的稻谷,回家的路上,父親瘦弱的身軀怎麼承受得住這重負。走一段歇一腳,如果遇到刮風下雨,路上滑,就更不好走,最麻煩的是遇到冰雪天氣走夜路,父親常常是高一腳低一腳的趕路,有時候把鞋子都走丢了,光着腳在雪地裡走,回到家,父親的腳都被凍得麻木了。農忙時父親還要和祖父一起去田裡上田埂,土裡去挖土。母親是家裡的長女,也是家裡除外公外唯一的“勞動力”。六歲時,母親清早就得到家對面的土山上去采摘黃花。黃花采摘的季節是六月,朝陽似火,黃花至少得持續一個月才能摘完。母親中午都不能休息,因為采摘黃花是分早、中、晚三個時間段,早采晚采黃花都得降低等級或者報廢。一天十幾個小時,頂着烈日的烘烤,母親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濕透後又被高溫烤幹,如此反複,母親的臉上被太陽曬得通紅,身上全是鹽漬的結晶,對于當時隻有六歲的母親來說是難以想象的。母親十二歲時,除了要采摘黃花,還得幫家裡犁田,耙田,扶田埂,打小工。這些活兒本都是大人幹的,可母親瘦小的身體就要承受着繁重的勞作。幹完田裡的活,母親還得去扯豬草,割魚草,照顧妹妹和弟弟。一天到晚,母親都沒有歇息的時間。
父親和母親的童年和少年是沒有屬于自己的快樂的,有的隻是苦澀,辛苦的勞作,以及關于汗水的記憶。母親每次和我閑聊起她和父親的過去,總是不斷的用衣袖擦拭着眼淚。聽着母親對往事的叙述,父親母親的過去在我腦海中突然變得清晰明亮了。如今,父親走了,母親也已經85歲高齡,我這個老小兒每天都會牽一牽母親的手,享受着和母親在一起的幸福。
勤勞能幹的母親
我愛我的母親,源于她的善良,她的明事理,她的堅韌,她的吃苦耐勞。她為這個大家庭的無私付出。母親一生艱難曲折,經曆了數不清的磨難,但她不抱怨,總是不聲不響的幹活,吃進的是草,擠出的是奶。在人生的旅途中,母親所經曆的點點滴滴都讓我回味無窮。
母親嫁給我父親時,家中的主要勞動力就是祖父和我的父親。母親從來就沒有閑暇過,日夜操勞,從來都不知道累。每天天剛微微亮,母親忙碌的一天就開始了。扯滿一背簍豬草,然後背回家,喝口水然後扛起一把鋤頭下到田裡,将田埂上的草除掉後,用鋤頭勾上泥巴覆蓋在田埂上。母親做事又快又好,就連做事嚴苛的祖父都豎起大拇指誇獎。母親在娘家是主勞動力,嫁給父親後又承擔起繁重的農活,成了家庭主要的勞動力,母親一輩子注定就是勞累命。我母親的到來,讓我祖父祖母的勞動強度得到了極大的減輕。
祖父勤勞,腦子靈活,時不時也會做點小買賣,相對于村裡一些家庭還是比較殷實的。父親母親結婚的第二年,村裡的幹部找到我祖父,要我父親去當兵,當時家裡除了我祖父,也就我父親一個男勞動力。家裡本來就活兒多,事兒重,如果我父親去當兵了,家裡就隻有祖父一個人幹活了,所以我的祖父沒有同意我的父親去,這為我家後來埋下了禍根,反右時部分村幹部以此為理由對我家進行打擊報複。那時候父親也成年了,祖父就希望父親能夠學一門技藝,以後也能憑着自己的本事吃飯。于是找到靖縣的姑奶奶給父親找了個木工師傅,要父親去學木匠,也讓父親離開當時的是非。從家裡到靖縣姑奶奶家有300多公裡,那個年代地市之間是不通公共汽車,不像現在坐高鐵幾個小時就可以到。當年父親就隻提着家裡為他準備的一小袋紅薯幹糧,背上的棉被還是母親出嫁時外婆陪嫁的被子,褲子上系着母親用過的皮帶。父親靠着兩條腿步行300多公裡,有路就走路,沒有路就爬山,差不多一個多星期才到達姑奶奶家,然後又走了三天到達貴州,自此開始了父親的木工學徒生涯。
父親去學藝後,家裡的勞動力又減少了,田裡土裡的事千頭萬緒,祖父一個人已經應付不了。挑豬糞是件又髒又累的活,豬欄裡潮濕陰暗,臭氣熏天,蚊蟲又多。母親雙手掄起耙頭,一耙頭下去将豬糞勾進糞箕裡,用扁擔挑到外面堆砌成小山的模樣。農忙季節,擡闆桶、打禾,這些本該由男人幹的重體力活就落到了母親的肩膀上。沉重的拌桶壓在肩上,祖父在前,母親在後,擡到田邊母親已經是全身濕透了,放下拌桶後,母親都站立不起。打完稻谷,和祖父一擔一擔的将谷子挑到家裡,曬幹上倉。在父親離開家的三年時間裡,母親頂替父親成了家裡的主要勞動力,和我的祖父一起包攬了所有的勞作,母親用她的能幹,吃苦耐勞幫助家庭度過了難關。
在田地還沒有包産到戶之前,生産隊适應的是工分制。生産隊都是按照勞動強度以及完成生産任務的進度來分配工分的,母親拼死拼活的做,居然能掙10分,頂得上一個男勞動力的工分。我對工分沒有什麼概念,母親說:10個工分能換兩毛錢。即便如此,家裡還是會欠生産隊的工分,特别是後來祖父祖母去世後,父親長年在外,家裡就靠母親一個支撐,既要照顧我年紀尚小的叔叔,又要參加生産隊集體勞動去掙工分,晚上還要就着煤油燈昏暗的燈光做家務活,縫補衣裳,一年辛辛苦苦下來,糧食還是不夠吃,父親辛辛苦苦在外所掙的工資,大部分就補給了生産隊,來換取口糧。
父親每個月都會穿爛一雙鞋子。母親白天要勞動沒有時間,她就在每天晚上擠出一點時間給父親做鞋子,三年時間,母親給父親做了36雙布鞋,祖母去世後,家裡所有人穿的鞋子就都落到了母親的手上。至今,我每次握着母親的雙手,腦海中就浮現出母親在昏暗的油燈下縫縫補補,飛針引線的情形。那專注的如同一尊雕塑的神态。
祖母去世後,家裡欠下了許多外債,既要還債,一家人還要不能挨餓,父親和母親經過商量後,決定将三叔和四叔的戶口簽往通道。手續辦好後,母親帶着我的兩個叔叔坐了三天的車才到達通道,父親把三叔和四叔安排進學校念書,母親就到馬路上去錘沙子。六月,驕陽似火,馬路上熱氣滾滾,生的雞蛋放到石闆上都能被烤熟。母親戴着一個小草帽,手裡拿着大約一尺錘把的小榔頭,坐在鋪着一層稻草的地上,用錘子把石塊錘成小沙粒,連續幾個小時錘下來手臂和腿已經酸麻沒有知覺了,特别是手掌,磨破的血泡和着汗水粘連在一起,那種火辣辣的疼痛,我難以想象母親當年得有多大的毅力去承受那鑽心的痛。一方石塊3塊錢,一天不停歇的話能掙1塊錢。周末,三叔四叔也會來幫着錘。養護段因為工作的性質,常常居無定所,父親每天在離單位很遠的工地上班,母親也在很遠的工地錘沙子回不來家,三叔和四叔早晨和中午就自己做飯,吃完了就去上學。直到晚上我的父親母親回來。 母親就這樣日複一日的錘着沙子,把掙來的錢一點一點的積攢起來。如今母親已經85歲高齡了,那雙手也已經變得蒼老無力,端東西時總愛掉在地上,看着母親哀歎自己的手怎麼會越來越不管事,我的内心就會泛起陣陣心酸。
在通道的二年,母親錘沙子差點連命都丢了。第一次是母親的腳筋被山上滾落的石頭砸斷了,幸虧三叔和四叔看到了,扯開嗓子向遠處的工友大聲求救,工友們馬上把我的母親扶到路邊,然後扶上車子往回趕,父親聽到消息後後扔下手裡的活立馬趕到車站,背着母親到雙江醫院,醫生說萬幸,差一點點腳就得殘廢;第二次是母親在通道造紙廠,母親在馬路邊的岩石下錘沙子時,松動的土方上面的一塊巨石突然滾下來,母親聽到響聲,起身一跳就到了馬路中央,幾百斤的石頭砸到馬路邊,砸出了一個坑,工友們以為我母親難逃一劫,當看到母親安然無恙時,都無比驚奇,說我母親了不得。第三次是母親下班坐在養路段工程車的駕駛室内拐彎時和另一輛車迎面對撞,母親卻毫發無損,這也許就是上天冥冥之中對母親的眷顧。最嚴重的一次母親頂着烈日連續錘了很多天沙子,回家後實在是精疲力盡,在生活煮飯時站在柴火爐竈邊兩眼一暈,頓時坐在裝柴火的屋腳,剛好有根柴棍豎立着,母親一屁股坐下去,柴棍硬生生插入母親的肛門,當時母親疼得臉色慘白,渾身冷汗直冒,幸虧父親發現得早,立即送到醫院,母親說當時柴棍抽出來時留了很多的血,我不知道當時醫生把柴棍抽出來時母親得有多疼痛,為此母親在醫院住了一個星期,為了省錢,母親還沒有痊愈就急着出院了。直到現在,還留下後遺症,遇上天氣變化,母親就會犯病。
一件偶發的事件,讓母親不得不又回到老家。1962年上半年,家裡的欠債終于還清了。随之而來的是母親的戶口遷移出事了,母親,三叔和四叔的戶口遷移證被别人掉包了燒毀了,留下的都是假的落戶證,上面于是開始來人調查母親戶口遷移的事,最終母親,三叔和四叔的戶口都被取消,戶口取消就意味着口糧沒有了,不得已我母親,三叔和四叔隻得返回老家。
母親的善良和明事理
母親沒有讀過多少書,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母親明事理,懂大義。母親心地善良,别人家遇到困難,母親總是樂于幫助,從不計較得失。有時遇到有乞丐上門,母親總将“乞丐”請到屋裡,盛上滿滿的一大碗飯,當時的家裡自己都吃不飽。做為沒有多少文化的母親,在自身困難的情況下卻去周濟處于困境中的乞丐,母親的善良和善心源自于外婆的血脈。母親和鄰裡之間相處的很是融洽,從來不會與人争吵,上屋下屋都知道母親心地善良,他們對母親很是信任,誰家遇到不順心的事都愛和母親聊,但她從來不會到處去說搬弄是非。遇到不講道理的,母親也都選擇了隐忍和退讓,母親的人緣好,在村裡的口碑很好,就算十裡八村的人隻要說起新屋裡的建嫂,沒有人不誇。
母親是個明事理,識大體的人。母親說和我的祖父祖母相處的日子裡,他們之間從來沒有争吵過,父親在世時在我和他聊天時也得到了印證。當我們兩兄弟和别的小朋友發生打架時,母親總是問清緣由,是我們錯了,就要到别人家去賠禮道歉,特别是當她勞作不在家時,母親就會告誡姐姐:弟弟和别人發生了矛盾,一定要把他們拉回家,母親常常教導我們做人要有志氣,要誠實,有時吃點虧是種福氣。母親心胸豁達,從不為一點小事發脾氣,在和父親生活的将近60年,母親将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獻給了我們這個大家庭,有時還是會受到誤解,就算不被理解,也從不埋怨,母親都會以寬闊的胸襟和聰明的智慧化解掉矛盾,母親總是說,退一步海闊天空。
我參加工作後,工作很辛苦,工資也不高,每次回家,母親總是用她清瘦的小手在我臉上,手上和背部“摸來摸去”,嘴裡念着這麼大了都不知道照顧自己,瘦得手都摸不到肉了,然後就會去殺一隻家裡的雞,用補藥炖幾個小時,炖好後,母親盛一大碗端到裡屋,然後把我拉進去關上門,母親就一直坐在床沿上看着我吃完,起身收拾好碗筷。在家裡的日子,我盡情的享受着母親的疼愛,卻沒有發現母親的兩鬓已經多了些許銀絲。母親知道我錢不多,在外面還要交朋友,免不了需要花費,母親總是擔心我的身體,臨走前,母親會悄悄塞給我一些零花錢,還會在我的包裡放幾包父親接到的舍不得抽的好煙。
如今,母親老了,動作也不太靈活了,但她的忙碌卻沒有停下來,看到我在外面為了家而拼搏,母親就會早早起床,做好可口的營養早餐,回家就能吃到母親精心準備好的熱騰騰的飯菜,母親總是目不轉睛的盯着我吃,每當我吃得一絲不剩,母親的臉上就會露出舒心的笑。如今,我也已年過半百,我已經習慣了被母親“盯”的感覺,也享受着這種感覺!
勤奮節儉的父親
到達貴州後,父親跟着師傅走鄉串村,鄉間都是小道,山路多,遇到下雨,都變成了泥漿路,特别難行,稍不注意就會滑倒,甚至很多山路下面就是萬丈深淵,父親肩上還得挑着兩個箱子,裡面裝着做木工活所用的工具,當時的條件非常艱苦。
父親勤奮,好學,做事不怕苦不怕累,師傅在做的時候父親一有空就瞅着看,不懂就問師傅,直到完全弄明白了才作罷,師傅很喜歡父親的這種鑽研精神,正常情況下要二年才能掌握的木匠技藝,父親隻用了短短的六個月時間,東西隻要擺在父親跟前讓他瞧上一眼, 就能夠做出來,不但做工精細,而且堅固耐用,師傅很是驕傲,對父親常常是誇不絕口。父親出師後本來是要回家的,在師傅的再三挽留下父親留了下來,繼續跟着師傅走鄉串村的幹活。在這段時間裡正好碰到通道養護段招工,特别需要木匠師傅。父親就跑去報名,沒想到被順利錄取了,并且每個月有了15塊的工資和45斤的口糧。
一九五七年的春節悄悄的臨近,父親回家了。背上背了一大袋做工時人家送的貴州糍粑。他把這三年的經曆說給祖父祖母和母親聽,祖父聽到自己的兒子有工作了,心裡很是高興,祖母雖然不是很懂,但是看到祖父高興,自然也心情愉快。父親回家,母親還是很興奮的,畢竟三年了都沒有見我的父親。祖父更是把糍粑幾乎盡數分發給了鄰居和好友,因為父親的歸來,又快到過年了,家裡的氣氛比往時熱鬧輕松了許多,盡管生活還很困難,但是祖父祖母還是盡力置辦了些年貨。相聚的時光總是那麼短暫,年剛過完,父親的假期也結束了。
父親當時每個月的工資是15塊錢,父親非常節儉,在通道工作時,父親每個月的所有開支不能超過五塊。一塊錢買旱煙絲,用那種廢舊的紙滾起來抽;每餐的夥食是五分錢一份的酸菜,炒酸菜有個好處,又鹹又辣能就飯。早餐更方便,湯是不要錢的,二個饅頭就着一碗鹹湯就可以解決,兩項相加剛好是四塊,還剩下一塊父親就留作急用。剩餘的工資他都寄給了我的母親。他從來都不敢多用一分錢。聽母親說:父親身體有個感冒都不會去找醫生看,怕花錢,有時發燒了就拿塊毛巾敷在額頭上。第二天照樣上班。同事們覺得父親這麼長期下去身體是要垮掉的,大家後來知道了我父親家裡的一些情況,他們不再說我父親,也理解了我的父親。有些同事故意裝作吃不完,然後夾些菜放到我父親的碗裡。父親是個知恩感恩的人,對于别人的幫助,總是心存感激,别人家需要幫忙,父親總是不計報酬,能幫盡幫。
70年代,父親調回了家鄉邵東工作,母親在家種地,那時候我們三姐弟都已先後上學,雖然家裡的條件比以前有所改善,但是多年的辛苦勞累消耗掉了父親母親的身體健康,母親患上了風濕,父親每次回來勞作完躺在床上我都能聽到他在床上翻來翻去痛苦的呻吟聲。父親的工資在他所有同工齡的人裡面是最低的,除了要供我們姐弟上學的費用,母親治病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父親一點也沒有感到輕松。那時候單位可以加班,每次下班後父親就會找到當班班長要求任務,除了周末要回家幹活,父親每天都加班五六個小時,雖然工資不多,但對于父親來說,有收入,家裡的日子就會好過一點。
食堂的飯菜雖然味道好,但是對于父親卻是很奢侈的。五分錢一份的酸菜和五分錢一份的蔬菜,外加一碗免費的洗鍋湯就是父親的标準餐。父親美其名曰為“幹部套餐”。父親每個月有45斤飯票,由于要加班,每個月的口糧就捉襟見肘,父親于是每個星期都會從家裡帶上一瓶豆鼓或者剁辣椒。早上多買一個饅頭,晚上餓了先倒上一杯白開水,把饅頭撕成小塊放到裝着開水的杯子裡,再從瓶子裡夾出一些幹菜,和着開水很容易就咽下去了。每次回家看到父親勞動時脫下外衣身上幾乎都是皮包着骨頭,母親總是心疼不已,有幾次我看到母親背過身去在偷偷的擦拭眼淚。
如今,父親走了。看着父親的遺像,我雙膝跪地,淚如雨下,父親生前的一幕幕往事如魔方般萦繞在我眼前,父親一生經曆坎坷,在缺衣少吃的年代,父親用他的勤奮努力工作,生活中節衣縮食,遇到大事勇于擔當,以他的智慧在那個艱難的年代把我們一家人平平安安帶出來。
感謝父親一生對家庭的默默付出!
父親母親扛起家庭重擔
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母親被大隊抽調到鐵廠去煉鐵,做“扯爐鼓風”的工作,當時的集體食堂都是四兩飯,對于勞動力來說隻能吃個半飽。大躍進結束後,接着就是反右傾翻案運動,大隊部分幹部給祖父祖母安上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說我父親故意對抗社會主義,不去當兵;說我祖父犁田跳間,做事偷工減料;說我母親把自己家的魚仔拿去娘家賣等等“罪名”。将我家裡稍微有點價值的東西裝進籮筐挑走了。接着對我的祖父祖母輪番進行“批鬥”。祖母的頭被他們扇得左右搖晃,看到祖母被批鬥的慘狀,母親甚至都不能哭出聲音。家裡遭受這場運動,祖父祖母的身體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加之饑餓,祖父祖母的身體徹底垮了。
三年自然災害讓家裡的日子更加困難,母親和父親結婚後就吃了一個月的純米飯,後來碾米的糠就被用來做糠粑粑,飯吃不飽就吃一個糠粑粑,雖然難咽,但是能填飽肚子。生活的艱難,讓母親千方百計去找吃的,對門的再初叔叔就叫上母一起到田間地頭挖野菠菜,鵝葉子草,蛇子草,用菜刀斬碎加入一點米糠做成粑粑,邊蒸就邊吃。挖這些東西得偷偷去,因為當時的田土還是集體的,被抓到了就得被關起來。有一次,祖母餓得實在不行,母親就冒着風險摸黑到田裡扯了一根蘿蔔菜,母親記得當時都沒有洗幹淨,倒點水在禍裡放點鹽煮熟後端給祖母吃。四叔也因為餓偷挖了一個紅薯而被人用土把四叔埋到胸口上了,幸虧被發現得早才救下來,家裡的房租也被征收做了豬欄,祖父一家被趕到犁樹住了将近一年。祖母幾次病危,祖父打了幾次電報給我父親,每次回來要花幾個月的工資,來來回回幾趟,到祖母去世,家裡欠下了300塊的外債,而當時父親每個月的工資隻有20塊。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二日,祖母終于沒有熬過饑荒和病痛的折磨,帶着對祖父和兒女們的萬分不舍,走完了她苦難的人生,時年四十九歲。
祖母去世後,父親接到母親發來的電報,一刻也不敢耽擱,第三天才趕回家,父親回來之前的這幾天都是母親在操心,當時還是吃的集體食堂,祖母去世時,連口像樣的棺材都沒有,母親就把床上的床闆抽出來,臨時叫來木匠用了兩天才拼好,父親回來後和母親一起打理了祖母的後事。母親說,辦祖母的喪事吃了100塊錢的蘿蔔。因為假期有限,安葬好了祖母後,父親就回到了單位。
1963年春節過後,天氣非常寒冷,因為戶口問題沒有解決,母親帶着三叔和四叔又回到了老家。自己就在生産隊做事掙工分。祖父因為營養缺乏,身體越來越差,家裡也拿不出多餘的錢給祖父治病,在饑餓和疾病的雙層折磨下,祖父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母親在祖父的病榻前當着三奶奶,一奶奶兩位長輩承諾把三叔和四叔扶養長大。1963年2月12日祖父與世長辭。母親毅然獨自擔當起操辦祖父喪事的重擔。她将豬欄裡唯一的一頭豬宰了,殺了60斤肉,母親從通道回來時錘沙子攢下的幾十塊錢都貼補上了。
祖母祖父的先後去世,本已捉襟見肘的家境更加雪上加霜。縱使萬般無奈,父親母親也隻能接受這個現實。那年父親23歲,母親22歲。他們責無旁貸的用稚嫩的肩膀扛起養活一家人的重擔。母親賤行自己對祖父的承諾,和父親一起引領着這個家艱難前行,盡管生活困難重重,但父親母親毫無怨言。父親一年隻有一次探親假,除非家裡有母親解決不了的事情,父親才會臨時請短期假回來。母親獨自在家默默的支撐着這個苦難的家庭。在父親和母親的共同努力下,把一家人平安帶出那個舉步維艱的年月。
1970年,四叔被推薦當上了教師,每個月有20塊的工資。四叔每個月自己隻留下10塊,剩下的就都交給我的母親以貼補家用。三叔辍學後,父親想着三叔必須要有一門技藝,以後才能夠自己掙錢養活自己,就打電報給母親,要她親自跑到父親的師弟梅老頭家裡,希望他能收三叔為徒,母親好說歹說,梅老頭就是不答應收,母親心裡很是難過,于是向外婆借了20塊錢,(當時的20塊就是父親一個月的工資)母親将錢交給三叔,要他到雙江去找我的父親。當時三叔身上都是穿得破破爛爛的,要出去連身像樣的衣服都沒有,我的母親就拆下一床從娘家帶來的唯一的一床新棉被,被面扯下來,為三叔做了一件外衣,一條褲子,棉花就為三叔縫制了一件棉衣,由于是第一次出遠門,我的母親對三叔是千叮咛萬囑咐。三叔經衡陽,桂林,最後到達雙江。在我父親那裡推了三個月的刨子後,稍微有點木工基礎了,父親就請假帶着三叔親自回來到他的師弟金普(外号如老頭)家裡,挨不過父親的臉面,最終三叔得以拜師成功,從此,三叔開始了他的學藝之路。三叔腦子活,隻學了六個月的藝就出師。四叔教了一年多書後,剛好公社文教有個保送上大學的指标,而四叔是村裡唯一一個讀了高中的,學曆符合,要想被保送還需要得到全村人的簽名按手印通過才能去上學。父親知道情況後馬上請探親假趕到家裡,連夜請全村村民簽了名,蓋完手印。第二天清早,就有人跑到公社告狀,幸虧當時我的大姨父是公社的文教主任,四叔上大學的事情才沒有節外生枝。
四叔在邵陽上大學期間,我的父親已經到了邵陽工作,父親每個月的工資是20塊,其中的5塊給四叔做生活費,10塊寄給我母親,剩餘的5塊父親留下做生活費和回家的車費。三叔有了木工手藝後,就有人來給三叔做媒,犁樹的家滿娘找到我母親,說我的嬸娘會做鞋子,當家理事都不在話下,我的母親帶着三叔到我的嬸娘家裡,雙方見面後,三叔就由我的母親做主把親事定了下來,我的母親講,當時數了6塊錢的茶錢。事後不久,按照家裡的習俗,要過梗,我的母親準備了三牲,還有二件衣服托媒婆送到了我嬸娘家,三叔就等着結婚了。後來一段時間,三叔得了小腸下垂,經常喊肚子疼,但是疼一會兒就會好,這樣持續了一段時間,有一次小腸垂下來再也上不去了,到醫院後醫生說必須進行手術治療,再也不能拖了。家裡當時拿不出錢給三叔治病,但三叔的病情又不能耽擱,萬般無奈之下,母親把家裡的唯一值錢的一對魚簍,還有一些木料賣掉,把三叔送到正公祠醫院,由于醫院沒有血液,情況又緊急,關鍵時刻醫生說還有一個辦法,隻要是兄弟身上的血液也可以,可當時隻有二叔在,而且他的身體也很虛弱,母親也顧不了那麼多,心急如焚的走出去和二叔商量,沒想到二叔還沒有等我母親說完,就撸起袖子對着我的母親說:“嫂嫂,就抽我的吧”。這種血濃于水的親情把醫生都感動了,鮮紅的血液順着輸液管緩緩的流進三叔的身體,三叔得救了。在我母親的精心護理下,三叔的身體恢複得很快。三叔的病好了,我的母親也就放下心了。
四叔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了邵東水東江第十二中學,成為了一名高中化學教師。當時,我嬸娘的母親也在同一學校教書,四叔工作認真,為人正派,被嬸娘的母親看中,經過和嬸娘一段時間的相處,他們确立了戀愛關系,過春節時,四叔将嬸娘帶回家中給我的母親看,以征求我母親的意見。我的母親尊重四叔的選擇,表示隻要四叔喜歡她就喜歡。這樣,四叔的婚姻就得到了我母親的認可。三叔手術後,身體恢複良好,三叔的婚事就被提上了日程,在我的母親的操勞下,為三叔和三嬸舉辦了一場簡單的婚禮。随後不久,四叔和四嬸也結婚成家。
至此,我的母親完成了祖父去世前對于她的囑托,母親總是默默付出,克服重重困難扛起了家庭的重擔。母親一生簡樸,一世辛勞;父親一生任勞任怨,時時牢記肩上的責任,用他有力的臂膀撐起了這個苦難的大家庭。母親的善良,勤勞,樸素,堅韌以及父親的簡樸,有責任有擔當,一生任勞任怨,遇到困難從不退縮的堅強而又剛毅的精神是我們做子女的永遠也學不完的。
母親生病
父親的一生都在奔跑的路上。為能夠更方便照顧家裡,減輕母親的負擔,父親曆盡千辛萬苦從通道調到邵陽紙闆廠,在邵陽工作5年,父親終于到了家鄉邵東焦化廠工作。父親的幾次調動,讓父親失去了幾次漲工資的機會,父親從通道到邵陽,工資反而降低了一級。剛到邵東工作時,我們三姐弟都已經上學,姐姐上高中,我和弟弟都上小學了。母親總是精打細算的過日子。知道父親的不容易,手頭拮據的時候,母親就厚着臉皮到親戚或者認為可以借到錢的人家去借錢,拆東牆補西牆,母親很守信用,借的錢一定會想辦法還上,所以母親出去借錢總不會跑空。母親把錢總是劃算着用,恨不得一分錢扳成二分錢用。以前父親離家裡遠,對于父親的生活更多的隻是從母親的回憶裡了解到。現在父親離家近了,和父親的接觸次數自然而然的多了,才慢慢的感受父親的真實生活。小時候,我們以為父親是超人,無所不能,直到長大後才發現父親也隻是一個普通人,也會生病,也有喜怒哀樂。對于曆經政治壓力和家庭遭受各種苦難的父親,唯一的選擇就是自立自強,心身的疲憊可想而知。父親是一個“好演員”,他把自己僞裝得很強大。相比母親,父親表達愛的方式更加含蓄、被動,有時甚至是生硬,言不由衷。對父親,我們總有些距離感。長大後我才感覺到其實“最孤獨的就是父親”。父親隻是默默地付出卻很少表達,深藏的情感深沉又熱烈。多年的操勞,父親身體落下了很多疾病,父親從三十多歲開始身體就垮了,但父親從來都不會和家裡人提起。父親每次回來,身上總會帶着藥瓶子,當年的我們并沒有注意到父親身體所隐藏的危機感。
我上小學二年級時,母親的身體終究抵不過長年的勞累病倒了。走路都感到困難。由于家裡的醫療條件有限,在父親的安排下,母親就帶上我和弟弟到了父親單位,随之我也轉到了焦化廠子弟學校念書。剛到邵東時,母親不能做任何事,燒火做飯都得等父親下班回來,經過一段時間治療,母親的病情有所緩解,母親就開始做一些輕微的家務事。因為是住在廠區内,燒火煮飯炒菜的原料都是母親到廠區的馬路上等着過往裝焦炭的汽車在拐彎處時的慣性作用,焦炭就會從車上掉下來,然後母親就會拿着鐵夾子把焦炭夾起來放到手上的小籃子裡,爐子起火就更容易了,出門就是父親工作的木工場所。母親可以去那裡撿些父親刨下的刨木絲和小木塊給爐子生火,煤炭也不用買了,家裡就能省下一筆錢。星期天,廠裡有專門接送職工上街買菜的汽車,那種老式的解放牌,車上裝個四面有圍欄的鐵架子,車尾有個鐵制樓梯上下,母親也會在這一天坐車上街買點菜改善夥食,如果碰上時間久點,沒有趕上最後一班車,母親就隻能走路步行,路上要歇息幾次才能走到廠裡。母親住在廠裡時,父親一個人的工資要養活全家,而且母親治病也需要花錢,我們三姐弟讀書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但是在母親的精打細算下,倒還是馬馬虎虎能過得去,父親的生活也有了一定規律,夥食也有了一定的改善。父親的體質有了些許好轉。父親在單位樂于助人,平時誰家要修個凳子,桌椅,或者做個小東西,隻要是不違反工廠的規章制度,父親都會利用空閑時間去幫别人弄好,所以很多受過父親幫助的廠裡職工時不時會在上班時順帶着些菜給母親,母親對于那些給予幫助的工人都心存感激,父親的生活其實非常清苦,他吃酸菜從通道吃到邵陽,再從邵陽吃到邵東,一吃就是幾十年,每到一個地方,父親的這個特殊生活習慣就會被單位的同事廣為宣傳,他們給父親起了個“響亮”的外号,叫“五分錢木匠”,可想而知,父親的身體怎麼會不垮下來。經過治療,母親的病情基本穩定下來,她覺得自己的身體已無大礙,加之一家人的開支實在太大,母親就萌生了回老家的念頭。經過父親的左右權衡,父親終于同意母親的要求,我跟随母親回到了老家。
雙搶
我們三姐弟的出生,家裡的負擔越來越重,母親除了要照顧我們姐弟,家裡還喂有豬,包産到戶後的每年“雙搶”,那是一年中最忙最累的時候,所謂“雙搶”就是“搶收”“搶種”,即趁盛夏酷暑,将成熟的稻谷收割起來,并栽下會在秋季成熟的晚稻禾苗。父親調回邵東後,事先就請好探親假,淩晨四五點鐘,父親和母親擡着笨重的打谷機走在前面,一步一個腳印。我們姐弟就跟在父母身後,我們年小隻能做些割禾、扯秧、插田等相對輕松一點的活。收割稻谷前,父親和母親會把雙腳叉開,彎下腰,揮起鐮刀把禾苗割下整齊擺放在田裡,等割到一半時,他們的腰都要很久才能直立起來。别人家裡都是幾個人輪流着踩打谷機,而我們家裡踩打谷機的總是父親和母親,父親和母親一隻腳踩在打谷機的踏闆上,雙手握住我們遞給她的稻穗在打谷機的滾輪上來回翻滾,烈日當空,看着父親和母親的衣服和着汗水像漿糊一樣粘在身上,我才知道什麼叫“汗如雨下”。收割完稻谷後,父親和母親得将打下來的糧食一擔一擔挑回家則成了父親和母親的“專利”。那濕漉漉的一擔稻谷,足足有百二三十斤重,父親和母親一天下來要挑二三十來擔,但我從來沒見父親和母親在我們面前叫過半句苦。那時,在我的眼裡,隻覺得父親和母親的能幹,根本就沒想到個中的辛勞。将糧食挑到家後,父親和母親還得将田裡的稻草全部收撿上來,父親和母親在水田裡來來回回,将剛剛脫去谷子的稻草捆紮綁好,再拖到岸上,雙腳和稻草攪動的水聲在寂靜的田野裡顯得特别的清亮。這樣的勞動是極其艱辛的,新鮮的稻草經過水的浸泡,異常的沉重,尖利的稻葉還會在手臂上留下一道道刺傷的痕迹。等到把一丘田的稻草全部整饬完畢,搬到田埂,已經是晚上七八點,甚至八九點,父親和母親整個人差不多累得虛脫,那樣一種疲憊感是難以言喻的。父母親将稻谷用籮筐挑到家以後,遇到好的天氣,就會将谷子倒在曬谷坪裡曬,每隔一段時間,父親就拿着耙子教我們像犁田一樣在曬谷坪犁稻谷,稻谷上出現一道道整齊的溝壑。前一遍橫着犁,後一遍就要豎着犁,交錯進行。因為我們家種的是雙季稻,半個月左右的時間裡,就要将早稻曬好收到倉裡、晚稻種下去,時間非常緊張,所以稱之為“雙搶”。父母親白天在田裡累得死去活來,晚上還要将曬幹的稻谷用簸箕倒進風車裡除去雜物。然後把曬幹的稻谷裝進籮筐用麻繩吊進樓上的倉庫裡,當把所有的稻谷裝到谷倉,父親的手掌都被麻繩磨出了無數個血泡,被汗水一泡奇痛無比,但是父親就像一個“鐵人”一樣,我當時不知道父親是不怕痛還是忍住不想讓我們看見。搶收完早稻,就是搶插晚稻。插秧是門技術活,如果不會退步,田裡就會踩得到處都是大洞小洞,秧苗就會浮上來,盛夏的太陽像火爐一樣,要把整個大地都蒸幹。插秧尤其辛苦,氣溫高,田裡的水滾燙滾燙,螞蝗也多,特别是蚊蟲叮咬的傷口,總會招來螞蝗的“光顧”。整個雙搶就是一場艱苦卓絕的“大會戰”,如今,那些逐漸淡去的年複一年的“雙搶”就如父母親額頭上一輪一輪的皺紋,化成記憶融入我的血液和骨頭。由于過度勞累,父母親四十多歲的年紀看起來是那麼的蒼老。當我成家立業,有了自己的兒女,特别是自己生活不如意時,才更加懂得當年父母所經曆的苦難,自從父母親擔當起家庭重擔開始,父母親就起早貪黑的忙碌,曬幹了手,累彎了腰,曆經别人數倍的磨難。繁重的勞動過早的消耗盡了他們的生命能量。
父親因病退休
1986年10月,父親因常年勞累身體積勞成疾,已經不能正常的工作,在父親的強烈要求下,單位為父親辦理了病退手續。因病退休後,父親的工資減少了很多,隻有正常工資的一半多點,由于父親和母親的身體都不好,每個月的藥費都是一筆很大的開銷,以前在單位看病還有部分報銷,回到老家看病都得自己掏錢,名義上父親拿着退休工資,實際家裡的收入比以前還減少了,母親手頭還沒有以前寬裕。父親就萌生了出去做木工的想法,去掙點額外的收入以貼補家用。現實畢竟是殘酷的,父親出去做了一天回家就感覺身體不适,母親就對父親說,算了,以為自己還年輕啊!莫出去做了,勞累了一輩子,在家裡休息多養養身體吧。可是父親幾十年每一天都是在忙忙碌碌中度過,突然閑下來,父親心裡總覺得有點慌,父親覺得盡自己的能力如果能夠掙得一份收入,那樣母親就會輕松一點。況且父親覺得自己還沒有到可以真正退休的時候。那段時間父親力所能及的幹些農活,田裡種上稻谷土裡種蔬菜,盡量節省家裡的開支。父親讀了很多老書,頭腦聰明,反應快,很善于以理服人。退休後,父親終于有點閑暇時間,在家裡沒事就寫寫祭文,父親做的祭文平實、感人。有一天父親拿出幾篇祭文給他的摯友白竹學校的老校長建偉伯伯看看,建偉伯伯一看到父親寫的祭文,頓時眼睛發亮,說,沒有想到你還有這個本事,真是呆在屋裡埋沒人才了。于是建偉伯伯極力推薦父親出山書寫祭文,父親因此得到了一份額外的收入,可以适當的貼補家用。父親退休後,我就沒有見到他的口袋裡有過餘錢,開始我以為是母親管嚴了,對父親是很不公平的,後來我才知道,其實是父親自己口袋裡不想裝錢,一是怕丟了,二是父親也沒有其他的開銷,所有的一切母親都安排好了。但母親不是這麼想的,每次出去,母親總會偷偷的在父親的口袋裡塞上幾張十塊的,母親說:男人出去身上怎麼能沒有錢。父親做事非常謙虛,每次和建偉伯伯等同仁出去,父親要求拿最低的份額,說自己是最晚來的,資曆尚淺,況且這份收入也是承蒙大家的照顧,父親的德行深得大家的贊賞,大家都願意和父親共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父親的祭文寫得好,也給大夥兒掙了面子,名氣大了後,方圓十裡的白喜事都想請父親這一班人去。這雖然是一件好事,父親的收入因此可以增加,但是父親的勞動強度自然也加大了,以父親的身體狀況隔三差五的出去一次還能扛得住,長期熬夜,父親的身體就吃不消了,父親每次主祭回來,都是神色憔悴,躺在床上一天都不想吃飯,隔不了幾天就得請花門樓的紅醫生來家裡給父親輸液。何況家裡還種着稻田。最辛苦的是到了冬季,天寒地凍,外面的風刮得樹葉唰唰作響,吹到臉上像刀割樣疼痛,父親身上就得裡三層外三層,最後還得加上一件大棉襖,頭上戴着能罩着耳朵和臉部的棉帽子,腳上除了穿上一雙裡面帶毛的皮鞋,還得帶上一雙棉鞋,手裡提着母親準備的小火箱,到了目的地,父親就将皮鞋脫下來,換上棉鞋,然後把雙腳踩到火箱上取暖。父親賺來的都是用自己的身體作賭注換來的辛苦錢。如果不是家庭經濟所迫,父親何來退休後卻不能享受安逸的生活,還要累死累活的把自己的最後一點餘熱貢獻給家裡的兒孫們,我常常在想,父親不就像一棵棕樹,活一年身上的葉片就被剝一年,一直剝到死了才罷休。母親看到父親長期這樣熬夜也不是個辦法,就考慮把家裡的稻田給别人種得了,可父親不同意,說主祭不是天天有,但飯是每天要吃的,不種田了就得花錢去買米,而且他也不是到了動不了的時候,拗不過父親,母親隻得繼續把田種着。由于稻種的優化,稻谷産量都提高了,農村普遍隻種單季稻了。盡管如此,種田對于身體多病的父親和母親來說勞動強度還是太大了,父親每次幹完田裡的活回來,總是腰酸背痛,母親在家裡預備了很多刮痧用的工具,每次父親不舒服了,母親就叫父親躺在床上,用刮痧的工具一遍遍的在父親的背部,肩膀和頸部刮着,一道道鮮紅的痧印在父親的身上被刮出來,刮完後父親就感覺到舒服多了。農忙季節,父親和母親還得去田裡割禾苗,打稻谷,收好稻草,把谷子曬幹,用麻繩把糧食吊到樓上的木倉裡,直到父親去世的前一年,家裡的稻田都是父親和母親親自在種。就算這麼辛勞,父親和母親從來沒有在我們子女面前訴過一句怨言,今天,當我抱怨生活不順命運不公時;當我為孩子的叛逆而心煩不已時;當我為遇到問題而怨天尤人時。我就想起父母當年的艱難。現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很多時候都感到自己太辛苦了。想想父母親在那麼艱難的環境下把我們扶養成人,我不知道父母親當年要承受多大的痛苦。
父親最後的歲月
2013年,父親突感身體不适,尿液中時不時帶有血,在老家經過鄉村醫生的診治後,時好時壞,母親當機立斷,不再允許父親去幹活了,事實上父親也幹不了了,外面的主祭,寫祭文母親也替父親推掉了。父親生病從來沒有這麼長時間,一般都是吃些藥,或者輸幾次液就會康複。此時的母親心裡也沒有底了。母親就把父親的情況和我說了。當時我在福州,聽到這個消息後,我匆匆忙忙處理掉生意後回到家裡,那時父親的病看上去已經比較嚴重了,隻是我們都沒有意識到父親和我們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我們三姐弟經過商量,力勸父親住院治療,經過我們的再三勸說,父親同意住院。父親曾經和我們說過,盡管身體多病,但父親從來沒有住過醫院,如果到了住院的那一天,也就沒得救了。父親進醫院後經過一系列全面檢查,父親的病情初步确診了,但是醫生還是沒有完全的把握,于是我們将父親的檢查報告帶到長沙湘雅醫院四叔的學生那裡,四叔的學生非常肯定的表示已經晚期,現代的醫學水平已經無能為力,勸我們放棄治療。我們三姐弟聽到這個消息,腦袋都懵了,都不願意相信這個結果。父親當時對于自己的病情一無所知,我們也不敢告訴他。對母親我們也是瞞着的。從父親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其實還沒有想到最壞的結果。我們三姐弟商量後由我對醫生說,隻要能讓父親覺得輕松點多貴的藥都可以用,我們不忍心讓他感覺到沒有希望了。當父親的身體症狀稍微改善點,父親執意要出院,熬不過父親,出院後,父親身體已經非常虛弱。每餐隻能喝些流汁性的東西,精神稍微好些時我就會把他扶到客房的靠椅上,上村下村,領裡鄰居空閑時就會到家裡來坐坐,也陪父親聊聊家常,這時候他就會暫時忘卻了病痛。父親的病情每天都在加重,下床的次數屈指可數,我把父親的病情告訴了姐姐和弟弟,姐姐和弟弟随後趕回家。父親從自己身體的變化也已經隐隐約約感覺自己來日不多,但父親一生堅強,就算病重,在我們姐弟們面前也表現出樂觀的精神。在父親出院回家後和病魔作鬥争的一個多月時間裡,父親帶給我們的都是堅強和對生活的無比信心,除了身體上承受着病痛的折磨,父親不再像以前那麼倔強了,我們子女說的話他都會聽進去,我感覺父親突然像個“乖巧”的孩子,我不知道父親此時是否卸下了身上所有的重擔,回首一生,始終牢記祖父祖母對他的重托;不負所托将整個大家庭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帶出困境;想起自己一生的苦難,家庭内外需要承受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壓力……。父親覺得好累,好累。彌留之際,父親将我們三姐弟叫到床前,用微弱的聲音鄭重囑托我們姐弟,他走後,要善待母親,無論什麼情況,都要讓母親的晚年幸福。我們姐弟含淚一一點頭,把父親最後的話語牢牢記在心裡。2013年6月27日晚,父親的病情突然惡化,意識全無,任憑我們姐弟怎麼呼喊,父親再也沒有回應我們。二叔走近用手指搭在我父親的脈搏上,沉默了片刻,說我父親的脈搏還在,直到淩晨四點左右,四叔和三叔的長子從縣城趕到家裡,整個家族的人都已經圍在父親的床沿邊,二叔再去摸父親的脈搏,他不說話隻搖頭,我們就知道,父親再也回不來了。也許是父親要等到所有的親人在身邊就會對生前所有的事情都放下了。父親來過這個世界,父親是平凡的,但他的一生卻充滿着色彩。我握着父親的手淚如雨下。父親走了,父親在生時,我對父親孝義不夠,愧對父親。現在,父親離我而去了,我身後的那座大山倒了,再也聽不到父親的教誨了。
父親!你還會回來嗎!
永遠的溫暖
後記
又是一個春暖花開的季節,敬愛的父親離開我們近十年了。無數個夜裡,父親的形象仍是“依稀往夢似曾見”,但父親在家庭中所表現出來的責任和擔當,讓我刻骨銘心。
父親的一生就是一部苦難史,從小幹着最苦最重的活,放牛、賣米糖、做雜活、随後,祖父祖母先後離世,父親二十三歲毫不猶豫的以長兄的責任和擔當和母親一起支撐起這個風雨飄搖的大家庭,在沒有任何外來援助的條件下獨自安葬祖父,扶養我的叔叔們長大,成家,父親一生曲折,多災多難,卻從不抱怨。如果世間的苦澀有三分,父親卻嘗了十分。從小隻知道向您索取,卻從來沒有對您說上一句謝謝!直到長大,成家,現在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才懂得您的不容易。父親,多想再次牽着您的雙手,感受您的溫暖,可是您已經不在了!
母親從小就幹着繁重的勞作。嫁給我父親後,家庭接二連三的出現變故,和我父親風雨同舟,幾十年如一日,毫無怨言照顧着大家庭中的每一個成員。随着歲月的流逝,現在回想起過往的時光,都是愛意和美好。在母親的教育和熏陶下,我們姐弟三個都很健康的成長,姐姐憑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學,成了教授,我和弟弟雖沒有大富大貴,也沒有什麼大的成就,卻也能憑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日子過得越來越好。我的母親隻是中國千萬家庭中的農村婦女的一個縮影。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感謝父母把我們養育成人,讓我們承歡膝下!
幾十年風雨曆程,幾十年滄桑巨變。我的父親和母親把自己的畢生都獻給了我們這個大家族。閱盡了世間滄桑,曆盡無數苦難和坎坷,為我們這個大家庭支撐起一片藍天,為兒女們鋪起一條幸福的康莊大道。幾十年風雨曆程,是父母愛的航行,幾十年優美的年輪,镌刻了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愛!和千千萬萬的父母親一樣。我的父母親平凡而又偉大,他們忍辱負重,勇于擔當,艱苦拼搏,自強不息的精神;與人為善,樂于助人的品德;遇到困難百折不勞,剛毅不屈的意志是父母親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财富。如果父親還健在,今年已經整整86歲了,母親比父親小一歲,至今仍然健在,在人生漫長的旅途中,無論你的年齡有多大,回家能有一碗熱騰騰的飯菜等着你,叫上一聲爸爸媽媽,該是怎樣的福氣!一個人,無論富貴,貧窮;無論職務高低,家中有着牽挂你的父母,那是怎樣的幸福!
願父親天堂安好!
祝母親健康長壽!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