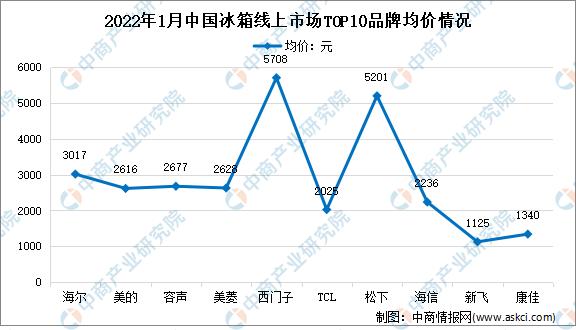□趙依
誠如阿來在新長篇《雲中記》開篇的自白,小說如莊重而悲憫的“安魂曲”,獻給“5·12”汶川地震中的死難者和那些消失的城鎮與村莊——文本叙事極富詩意,是“邊地書、博物志與史詩”,更是從近處曆史所生發的宏闊如空山的回響。
從題材上看,中國古代文學的每個時期都有獨具魅力的災害文學作品,如先秦的災害神話和故事傳說,兩漢魏晉的災害詩歌和散文,唐宋的災害詩歌,元明清的災害小說和哀民散曲等,其中不乏對自然災害的真實反映和對社會心理的切近描摹。若放眼世界,在神話傳說、史詩和宗教經典中類似“毀滅傳說”的災難主題比比皆是,古巴比倫的《季爾加米士史詩》、古希臘的《荷馬史詩》、柏拉圖的《克裡特阿斯》《提邁奧斯》等都同屬此類。在地震災害頻發的現代日本,村上春樹在《神的孩子全跳舞》中對自我文本方式的颠覆,對日本人日常生活的紋理和由地震引發的包括幸存者在内的人類精神危機的展示,在現代意義上的地震題材之小說風格及其象征性上都有開創。阿來的小說也在身為作家的社會責任中悄然發生新變,古老閉塞且一度自足的土地上,民族身份和傳統信仰與現代文明不可避免地發生錯位,悲劇和苦難的力量成為一種複雜又單純的旋律維系着生活的某種平靜表象,人們在這種常态中似乎還來不及、不願意去直面、回憶和思考——于是阿來覺得是時候了,現場展示、生命書寫、精神探索、命運感、曆史感,早已如小說結尾處的那“一隻藍色的精靈在悄然飛翔”……

“安魂”:記憶與延續
《雲中記》集中塑造了苯教非遺傳人阿巴這一人物形象——阿來将其作為主要的叙事策略——以時間及其節奏性為章的長篇文本結構中,小說細數了阿巴從移民村重回地震災區雲中村的半年時光,阿巴在遺迹中尋找舊人留存之物度日,以特有的“告訴”方法和“祭祀”儀式安撫、祭奠、超度災難中逝去的鄉親,不單是這些情節寫得細膩悲壯,與這一切關聯的萬物萬靈都被一股巨大的情感渦流席卷,而随着阿巴不斷深入災區、直面生死、思考靈魂與信仰,他最終以自我生命和全然純粹的靈魂獻祭深愛的故土——此之消亡走向彼之回歸,讀者在多重的命運選擇中體悟“安魂”的複雜深意,而這,也告慰生者。
筆者彼時身在成都,作為“5·12”汶川地震的親曆者,在《雲中記》開篇便能捕捉到阿來近年來頗受關注的非虛構寫作:作為區域地理象征的岷江水和如今作為新地标的移民村們,已經被更為宏闊的曆史感裹挾;“他叫了一聲山神的名字”——我始終銘記在最初的那一秒鐘是如何意識到這是地震的爆發;“當他們看到江邊公路上那些等待轉運災民的卡車時,一些人開始哭泣,像在歌唱”——後知後覺的悲傷再次為災難的巨大和突如其來做證,多少人如那顆老樹般甯可“死意已決”;再後來,相信所有讀者都曾在新聞裡看到,解放軍、醫療隊、救災物資和重建規劃……
阿來的“安魂”直面記憶和現實,非虛構筆法和細節的真實不乏史書實錄之感,這亦與小說圍繞藏地文化、安魂須仰萬籁相通。于是我們在小說裡“俯察品類之盛”又廣識“草木鳥獸蟲魚”以賦比興,連同諸多民族文化習俗,關于圈養還是跑山放養,關于飲酒,關于碰頭禮和“告訴”,關于抖開袖子袖管裡比劃手勢議價,這些筆者曾在四川阿壩親見的真實,一齊形成了文本融貫的文化氣質風貌。也正因了此種風貌,阿來獨有的幽默感才有的放矢:始終喊不對自己稱号的“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老子是漢族大哥”等細節透露的名實之辨和荒誕的英雄感;阿巴對作為“政府的人”的侄子的為難和體恤;雲中村人不會唱的《感恩的心》和加上的啞吧比劃動作;地震遺迹搖身一變成為騎馬上山看的風景和如今包括收費廁所在内的景區價格亂象……這些源自作家悲憫心的幽默感關涉無處安放的自我認知焦慮,存乎整體與局部、宏觀與微觀、政府關心的受災群體和各不相同的災民個體生命之間。
這場“安魂”,與阿來的曆史感和對當下的關懷相系,小說以民族血緣為紐帶建構文本穩固的倫理傳統,同時将以之為基礎的藏族鄉村生活中民族精神空間和文化心理結構中的裂變、陣痛和盤托出,“安魂”成為重要的曆史時刻和現實節點,對阿來而言也是人與鄉之間無法隔絕的血脈。由此,小說主人公阿巴的信仰在一己執念之外生發出堅實的合理性、正當性與必要性,小說的邊地書、博物志性質亦是對中國社會轉型的史載。不妨細數由己及衆的“安魂”層次:阿巴的自我回歸和以身殉鄉情、重拾舊日程和記憶重演——祭祀山神阿吾塔毗、雲中村招魂和安撫亡靈——以及生者各自生活的告慰和延續。總之,“不讓悲聲再起”,就需要精神枷鎖的逐層開釋,“天與地”“神與人”互相感知,我們從中看到了如《格薩爾王》般的藏族英雄個性化“重述”和現代性視野,關于生死靈魂處境的讨論在理想信仰與文化的場域中成為一場“相信”的哲學思考和信念轉化,這些同屬于阿來的生命理解系統,當阿巴踐行了這種應對苦難的精神,苦難者就會“複活”。

時間、節奏與重述
阿來寫作的起筆總是傾聽時間,頗多研究意趣:“那是個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聽見一群野畫眉在窗子外邊聲聲叫喚。”(《塵埃落定》);“那時家馬與野馬剛剛分開。”(《格薩爾王》);“那時是盛世。康乾盛世。”(《瞻對》);“早先,蘑菇是機村人對一切菌類的總稱。”(《蘑菇圈》);“海拔3300米。寄宿小學校的鐘聲響了。”(《三隻蟲草》);《空山》六個中篇的開頭——“那件事情過後好幾年,格拉長大了……”“多吉躍上那塊巨大的岩石,口中發出一聲長嘯,立即,山與樹,還有冰下的溪流立刻就肅靜了。”“達瑟,我将寫一個故事來想念你。”“剛剛解放,駝子就成了機村黨支部書記。因為他當過紅軍。”“拉加澤裡初來雙江口時,鎮上還沒有這麼多房子。”“機村人又聽見了一個新鮮的詞:博物館。”
《雲中記》的開篇也不例外:“阿巴一個人在山道上攀爬。”緊接着是極富畫面感的鏡頭式描寫,關于山川道路、關于藏地風貌、關于兩匹馬……插叙、預叙、倒叙等多重的重複性叙事,加之由“天”到“月”、由“月”及“天”的章節節奏控制,叙事密度調節着情感濃度,時而是全景鏡頭下的場景呈現,萬籁巨響,時而以時間讓渡叙事,鬥轉星移。
阿來獨特的叙事時間觀控制着叙事節奏和叙述時序,不完整和不确定的文本狀态通過重複叙事填補無限可能性,重述之魅就好比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中的三顧茅廬、六出祁山和九伐中原等,叙述者一遍遍烘托渲染,一方面深入刻畫着人物和事件,同時使叙事本身獲得解放,剛柔、動靜、頓續、疏密并構,兼避扁平與雜亂之弊,審美風範與情節元素随時對應,而時間的節奏性成就小說的音樂性和詩化,節奏本身又具有某種形式上的重複性。《雲中記》裡,法鈴、兩匹馬、雲中村尋訪等故事架構和細節鋪設打亂時序,通過不同場景下的重複性叙述牽連更為廣闊的叙事枝蔓,各自的叙事功能逐次遞進,叙述現實、重拾記憶,同時創造性地介入集體創傷。而重述帶來的統一中的變化、變化中的統一綜合為一種小說語言的散文化傾向,意象和聲和諧伸展,小說獲得精緻而複雜的聲音結構和文本形式。
所謂精緻,尤在細節。無論是“馬匹用力爬坡時右肩胛聳起,左肩胛落下”,還是鞍子木頭關節處的聲響以“咕吱咕吱”拟聲,以及荨麻、鸢尾、馬先蒿、金蓮花、龍膽、溲疏、鐵錢蓮、丁香、白桦、雲杉、杜鵑花樹等植物的指稱,又或是震前震後風物變化和繁複的畫面整體營造,都可以看出作家深厚的生活積累、日常洞見和語言功力。毫無疑問,小說在講述故事、再現經驗的叙事性基礎上,還是一種形式的建構和語言的創造,這也是長篇小說理應昌明的精神創造性和審美理想。我們從阿來的創作中可以明辨“學養”和“知識性寫作”在解決文學的藝術危機、價值危機等方面所具有的長期精神效果,而作家歸屬于自省與理論的共識對文學創作行為的自覺是審美創作必須依賴的資源,在任何時代都不可或缺。
《雲中記》頗緻力于畫面感及其真實性的建立,此即阿來對曆史性災難創傷的正視和呼籲:共同的“安魂曲”并不僅是局部或區域性的記憶重拾。阿來使世人再度面對那個悲慘的災難性時刻的前世今生,呼喚他們去努力尋求可能的解決之道,去留意、體悟他人的苦難——通過文學創作的藝術呈現抵達廣泛的深入的持續響應,阿來必須為讀者提供一幅幅可感可想可見的畫面去超越時間和曆史的目擊時刻——對災難的承認、再現與和解,構成譜寫“安魂曲”的創作動因與可能。

時代新人形象深化
阿來在小說裡呈現了一批正在成型中的時代新人形象,他們大多類似《三隻蟲草》裡的藏族少年桑吉,在社會轉型的宏大背景下不得不面臨生存、信仰和知識等複雜層面交織而來的困境。《雲中記》中,阿來以人物為叙事策略,并深化着對此類時代新人形象的文學探索。
盡管我們也讀到央金姑娘和祥巴等人物形象在重建各自震後生活時的短暫迷失,但他們到底不同于以往的文學頹敗青年形象,到底還是走在了成為有為青年的艱難征途上——而更難把握的青年形象是小說裡仁欽這樣的藏族幹部,一來,好人的性格、品質比較難以實現活靈活現的文學呈現,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相對單薄;二來,仁欽身上包含親情與職責、信仰與文化、義與利的矛盾及其所關聯的思與行的深度追索,這種新的複合型困境不同于桑吉類型,人物攜帶的情緒和所處的工作生活環境,還有政府救災重建工作等,相對來說都較為獨而新。
《雲中記》中的仁欽是回到雲中村的大學生村官,是共産黨員,一度因舅舅阿巴作為移民回流被停職。仁欽這一人物形象的創造性設定,可以視為阿來“文化認同-身份認同”雙重命題下的藝術形象捏合。
仁欽有幹部的素質和年輕人普遍共有的職場抱負,也受親緣關系、共情心理和民族文化影響對舅舅阿巴始終心懷慈悲。正因如此,阿來筆下的仁欽有血有肉,而人物形象一經真實地确立,小說後半部分關于景區亂收費的新媒體曝光事件的叙述就更加深入人心——這場成功的危機公關透視了青年幹部的個人成長、能力提升以及面臨生活的心性轉變,而成長背後對生活依然秉有的信心,以及如何負重前行,如何創造自己的信念和持守内心的價值,同樣是《雲中記》留給年輕讀者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同樣地,阿來的這部新長篇也為解決中國當代小說的困境提供着思路:當小說本身成為更加複雜的精神事務,我們依然需要作品中藏匿着的那個道德的我、理性的我、生命的我和真我。當文學創作不得不面對個人或集體經驗進行寫作,生活的邊界、藝術的邊緣乃至人類記憶的盡頭,文學還将呈現何物?我們是否應與阿來一樣,心生一種責任的操守。
作者簡介:趙依,1989年生于四川成都。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文學碩士,青年評論家、助理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魯迅文學院教研部教師。現為《人民文學》雜志社編輯。
【如果您有新聞線索,歡迎向我們報料,一經采納有費用酬謝。報料ihxdsb,3386405712】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