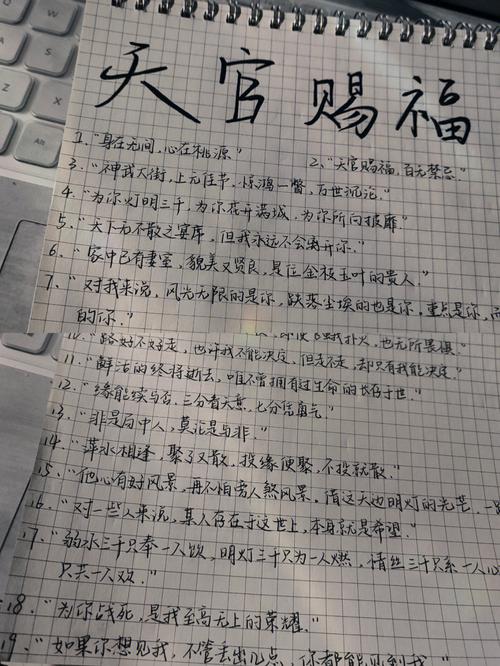在中國陶瓷史上,當陽峪窯是特殊的。一方面,絞胎瓷為中國陶瓷增加了一個新品種,開創了我國陶瓷胎變的先河;另一方面,當陽峪窯曾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在陶瓷界連一個确定的名稱也沒有。在國内,它又稱懷慶窯、河内窯、碌武窯等;在國外,因為窯址位于河南省修武縣,日本稱之為“修武窯”;因其南部距焦作市僅6公裡,英國稱之為“焦作窯”(葉喆民:《中國陶瓷史》,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3月第1版,第259頁)。
至少在20世紀30年代前,當陽峪窯在中外陶瓷研究界的視野裡還相對陌生。1933年英國人司瓦洛等先後考察當陽峪,獲得大量瓷片,當時他們因不知道地名而稱之為“瓷谷”(葉喆民:《中國陶瓷史》,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3月第1版,第259頁)。可能直到楊萬裡、葉喆民于1952年、1956年兩度考察并發現立于北宋崇甯四年(1105年)的窯神碑稱為“當陽峪窯”後(葉喆民:《中國陶瓷史》,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3月第1版,第259頁),它的窯名才被确定下來。窯名的飄移不定,從一個側面說明當陽峪窯被曆史掩埋太久。
曆史留下的遺憾,曆史也會選擇出重新書寫曆史的英雄。20世紀90年代,重新審視曆史傳統、重視曆史文化傳承的浪潮興起,催生一批優秀陶瓷藝術家承傳光大民族藝術血脈。柴戰柱就是這類藝術家中一顆引人注目的明星。他20多年如一日,癡迷于絞胎瓷藝術的探索,追逐着當陽峪窯的革命與複興之夢。

讓每件作品的造型都充滿韻律
陶瓷藝術是造型藝術。一件陶瓷藝術作品所塑造的物體形态,決定着觀賞者的“第一印象”,也決定着器物的“第一美感”。因此,優秀的陶瓷藝術作品,總是把造型作為基本的藝術語言,來表現藝術家所要表達的藝術審美追求。中國曆史上的名窯,沒有一個不在造型上下功夫,形成了自己的特殊風格。
居古代“五大名窯”之首的汝瓷是造型藝術的典範。常言道:“汝瓷無大件”,又道:“汝瓷無小器”,這看似矛盾的兩句評語,在相當程度上指的就是汝瓷造型的簡約。迄今為止,傳世的汝官瓷器不像其他官瓷有身高出尺、比較壯碩的器物,大抵為盤、碗、洗、爐、花盆等小型器物。汝官瓷造型簡潔,沒有多種造型的疊加,沒有誇大的撇足,沒有放大的敞口,沒有誇張的器柄,沒有變異的器頸,一切都是那樣簡單,要麼一圓香爐,要麼一口小碗,要麼一掌小碟。但造型越簡潔,做工越精緻,任何一件器物增之一分則嫌高,減之一分則嫌矮,擴之一分則嫌壯,縮之一分則嫌瘦,完全是在一種簡單至極、恰到好處的高低、寬窄比例搭配中體現出一種工藝的精巧,播放出一種優雅的旋律,顯現出一種自然、甯靜、深蘊的美感。
傳統絞胎瓷的造型是多樣的,但它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如碗、盤、盞、盆、缽、壺、注子、盒、唾盂、爐、熏爐、瓶、罐、枕、壇、缸、勺、燈、燭台、渣鬥等。建築構件也有磚、瓦、闆瓦、筒瓦、低溫色釉力士、鸱吻以及屋脊飾上的摩羯、卷尾獸、妙音鳥等。陳設品雖然有花瓶、花盆、鼓凳等,但不是主流,也在造型上缺乏藝境。

柴戰柱的絞胎瓷革命,首先是巅覆傳統的造型。他既吸取其他傳統陶瓷名窯的器型,也吸收青銅器的優美器型;既吸收中國古代其他藝術的營養,也從西方雕塑藝術中吸取精華;既注重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習慣,又注意吸收現代藝術的元素,根據當代人們的審美情趣,加以新的創造,從而開創了新的絞胎瓷的造型藝術。站在他的陶瓷藝術作品面前,看到的是一個綽約多姿、美不勝收的藝術世界。
《絲綢之路》呈倒鐘形造型,與古代類似的器型比,它更修長,像一朵綻放的喇叭花,洋溢着春天的氣息。《喜上梅梢》是一件棒槌瓶的造型,但與傳統器型相比,它的頸又短了些,撇口更大,與瓶腹相同,在器物的身姿上增加了奔放的力量。《遺韻》是梅瓶的造型,但與傳統的梅瓶比,它的肩部更平、更寬,而瓶胫并不像傳統梅瓶呈弧線收窄,而是從肩部均勻地緩緩斜下,足部收細,整個造型給人一種穩重而又挺立的感覺。《寒香》是一件球瓶型的作品,與傳統的球瓶相比,瓶腹并不是規則的圓型,而是上寬下窄的㮋圓,挺立的球柄上下并不均勻,而是略有撇口,這就使得作品在靜态中有一種動态感。《節節高》采用的是傳統帽筒的造型,但它又不是地道的傳統帽筒,好像竹節一般,在幾道竹節處有微微的起伏,于是,本來簡單、平直的造型有了律動,有了聲音,有了旋律。
當然,柴戰柱的陶瓷藝術革命不僅表現在對傳統陶瓷經典器型的改革上,而且表現在陶瓷藝術造型的創新上,或者說,通過器型的創新,增加陶瓷造型藝術的現代性。
《望春》是一幅瓷雕作品。整體造型像一個地球,似乎正在自轉,而一隻隻手向心而捧,手指彼此交叉,像一道防護網。整件作品既具像,又抽象,表現了作者“地球隻有低碳,人類才有綠色”的主題。
《和合》器型呈雞心狀,像一朵花蕾,含苞待放;又像四個人張開雙臂相擁。花蕊半啟着,像一個孩子的粉紅小嘴,在呼吸,在呼喚,在吟唱。中華民族是一個包容的民族,是崇尚和合文化的民族,和則協,合則諧,和合則生萬物,和合則樂萬邦。這件作品在簡單的造型裡,蘊藏着豐富的哲思。
《一分為二》是一件貌似“缺陷”而實則意義深邃的作品。一件水波紋似的青花瓶,從頂至足一分為二,但分而未裂,裂而未分,在底足處又連為一體。它像兩個即将合一的半圓,又像對半開放的荷花,這便是事物的辯證法,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分是因為要合,合是因為要分;根的團結堅實,是為了花葉繁茂;任何事物的最終圓滿,其實都是不圓滿構成的,或者說,不經過殘缺的苦痛,哪有圓滿的甜蜜碩果。正如柴戰柱在其作品集中所自注的:“不單聞其表,更為尋其質。詩情畫意融瓷内,絕處令人思”。這裡的“絕處”,就是它的造型所蘊含的象征意味。
總之,柴戰柱的絞胎瓷的造型,完全從傳統絞胎瓷的造型裡跳出來了。它的造型,或表現為一種線條律動的美,或體現出一種音樂般的韻律,或表現為一種奔放的想象,或内蘊着一種深沉的哲思。他的絞胎瓷造型是個性化的造型,他的絞胎瓷藝術是現代性藝術。他開辟了絞胎瓷造型藝術新的發展路徑。

讓每件作品都成為工藝的完美集成
中國古代瓷窯燦若群星。在競争、交流、融合的過程中,創造了各自獨特的工藝,如定窯、耀州窯的釉下刻劃花,吉州窯的樹葉貼印花,磁州窯的剔劃花、珍珠地紋,唐三彩的雕刻、堆塑,等等。正是這些獨具特色的工藝,在相當程度上形成了各個瓷窯的藝術風格,譜寫了多姿多彩的中國陶瓷史。
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斷深入,掩埋當陽峪窯的曆史迷霧被慢慢揭開。從有關資料看,曆史上的當陽峪窯是中國宋代瓷窯中風格變化最多、造型與裝飾品種最為豐富、做工特别精細的大規模窯場之一。當陽峪窯以剔劃繪畫著稱。根據當年所得地面殘存的有數瓷片看,有白釉、白地繪劃黑花、黑釉、醬(绛)釉、蜜黃釉、綠釉、赭黑地剔劃白花、紅黃綠色加彩以及珍珠地劃花等多種(葉喆民:《中國陶瓷史》,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3月第1版,第259頁~第260頁)。裝飾技法有刻、剔、劃、飛刀、凸線、模塑、模貼、模印、雕塑、镂空、填彩、釉上釉下繪等。有的典型制品精美異常。故宮博物院藏有兩件當陽峪窯“赭地剔劃白花紋罐”及其此類殘片,其白如玉,其黑似漆,是該窯的典型作品(葉喆民:《中國陶瓷史》,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3月第1版,第260頁)。
當然,當陽峪窯出類拔萃、獨樹一幟的産品還是絞胎瓷器。這種技法雖早在唐代鞏縣窯就已出現,但花紋比較簡單。當陽峪窯在此基礎上加以改進,制作出了鳥翅羽毛紋、編織席紋、行雲流水紋等,葉喆民稱:“技法高妙,獨步一時。(葉喆民:《中國陶瓷史》,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3月第1版,第263頁)”
“一個窯口有一個窯口的基團。”柴戰柱說:“釉是汝瓷的靈魂,絞胎是當陽峪窯的根脈。我們的使命,是在絞胎這個千年根脈上,生長綻放出新的花朵。”在他看來,當陽峪窯應該開放包容地面對整個陶瓷世界,面對其他各種藝術工藝,在守住絞胎這一根本性工藝的基礎上,大膽地實行拿來主義,進行絞胎瓷的工藝革命,讓每件作品都成為工藝創新的完美集成。
絲綢之路被英國著名曆史學家彼得.弗蘭科潘譽為“亞洲脊梁通道”(4(4)(英)(彼得.弗蘭科潘著,邵旭東、孫芳譯:《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第111頁。)。但“絲綢之路”漫長險阻。“無論是經過塔克拉瑪幹沙漠,還是跨越天山山脈或帕米爾高原,都必須穿涉險要地帶。從一個綠洲到下一個綠洲,路途異常艱辛。極端的高溫也是一個巨大考驗,也是巴克特裡亞駱駝如此彌足珍貴的原因:這些動物能忍受極其惡劣的氣候環境,對緻命性沙漠風暴的到來非常敏感。它們在預感到風暴來臨時會‘立即嚎叫着聚成一團’,商人和商隊見到後會馬上用氈布将自己的鼻口包裹起來。當然,駱駝在預測天氣方面也會出錯,人們在商路上經常可以看到大批的死亡駱駝和屍骨。(7(7)(英)(彼得.弗蘭科潘著,邵旭東、孫芳譯:《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第10頁。))”
柴戰柱的絞胎瓷作品《絲綢之路》正是一幅運用多種工藝、巧妙表現這一曆史主題的作品。絞胎拉出近于圓柱形的倒鐘式瓷尊,像一座高聳的山峰,褐、黃、綠、白等顔色材料協調而又變化多姿地絞合在一起,讓人仿佛看到朝霞升起或夕陽西下時沙漠戈壁中的綠洲、河流、氣霧。藝術家采用剔刻的方法,像環山公路一樣沿着瓷尊自下而上“凹挖”出一條盤旋道路。在“道路”中,再施以镂空的技法,刻畫出駱駝的身影。沙漠、綠州、河流、駱隊,構成一幅絲綢之路的曆史畫卷。站在這件作品前,不禁讓人想起唐代詩人張籍的《涼州詞》:“邊城暮雨雁飛低,蘆筍初生漸欲齊。無數鈴聲遙過碛,應馱白練到安西。”《絲綢之路》宛如一幅風景畫,向我們展現出一隊載着大批絲綢前往安西的駱駝隊,正行進在蒼茫的砂碛、河流與淺草之中;駝隊漸行漸遠,隻有悠悠駝鈴聲還在沙漠上空随風回蕩。
柴戰柱曾作《七律.雲台山紅石峽》:“懸崖峭壁億年盤,山水精髓聚太巒。幽瀑滴流穿石洞,九龍浪湧碧波潭。開山劍劈成一線,入海刀挖彙百泉。仙境紅塵遊客溢,閑庭信步走栅欄。”詩不僅寫出了雲台山的奇崛幽妙,而且表達了作者對雲台山勝景的醉心留戀。寫了詩似乎還不能滿足柴戰柱對雲台山的愛憐,他又創作了《紅石峽風光》這件圓腹撇口瓶。柴戰柱以絞胎拉出豆青色的瓶腹,以紅、白、豆青等多色絞胎拉出瓶頸、瓶口,一幅近景為浩瀚的水面、遠景為高天白雲的山水畫生動地展現在瓶身上。但柴戰柱并不滿足于這一風景。在湖水、遠山、白雲的背景下,他剔刻出近樹、湖岸、雙孔石橋和橋上的行人。由是,一幅浮雕出現了。這使畫面不僅更有層次感,而且更加富有自然氣息和觀賞意味。
《和合》瓶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我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成型的胎坯作為這件作品的底質,但它給人的印象是一塊塊用絞胎瓷片拼接、堆塑而成的。并不規則的多色絞胎彩線,穿插在一塊塊瓷片上,使每塊瓷片都有着大同小異的水鄉景色;瓷片相互疊加,不僅使瓶身有着變化的立體感,也使色彩變得迷離蕩漾起來;柴戰柱似乎還不滿足這種工藝的豐富性,又在每塊瓷片上壓上規則的縱向淺刻細線。于是,縱向刻印出的細線與橫向波動的絞胎色彩交織變幻,讓這件作品在晶瑩的瓷釉下更加楚楚動人,有了半透明的山水畫意境。
柴戰柱戲稱自己的絞胎瓷革命是“亂來的”。所謂“亂來”,就是技法探索沒有邊界,沒有條條框框,隻要有利于表現藝術主題,隻要有利于表現作品的藝術韻律,古今兄弟窯口的技巧,中外藝術表現手法,他都可以“拿來”。正是這種“亂來”,他的絞胎瓷作品除了絞胎這一傳統的制胎技巧外(這一技巧當然也革新變化了),其他的技法都不是傳統絞胎瓷的技法,而是柴戰柱自己創造的“柴氏”技法。

瓷器是“智巧”的藝術
由柴戰柱的絞胎瓷革命,我想起了瓷器的多種意義解讀。
在新石器時代,仰韶彩陶就成為中華民族原始藝術的代表。從此,陶瓷成為唯一與中華文明曆史進程相伴随的藝術品類和樣式。中國創造了瓷,也首先創造了陶瓷藝術。談到瓷器,中國人都會驕傲地說,十八世紀前,歐洲人還不會制造瓷器。随着大量精美的中國瓷器流入西方,西方便把“中國”與“瓷器”兩個詞等同起來。
其實,這還不足以說明中國瓷器對世界的影響。隋代慧苑法師曾探尋古梵文稱中國為“China”(初作“Cina”)的原義,他在《華嚴經音義》中說:“Cina,翻為思維。以其國人多所思慮,多所制作,故以為名。”這就是說,在古梵文裡,瓷器來自“多所思慮”即善于思考的民族,即文明的民族,或者說,“China”代表了思維能力、思維層次。
20世紀初,文僧蘇曼殊(1884~1918)通英、法、日、梵諸文。他認為“China”初指華夏。他研讀三千年前的古印度史詩《摩诃婆羅多》和《羅摩衍那》,發現“China”一詞最早出現在這兩部著作裡,其原義為“智巧”。他認為,這是三千四百年前印度婆羅多王朝時彼邦人士對黃河流域商朝所治國度的美稱。“智巧”與慧苑所說之“思維 ”内涵略有不同,想系詞義因時代而演變所緻(《瓷,中華文明的新象征》,《今日頭條》,2009年8月17日)。
我贊同蘇曼殊的解釋。瓷器是當時工業化的最高成果,代表着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水平和創造能力。同時,它集實用與藝術審美于一體,集造型藝術、色彩藝術、繪畫藝術、雕塑藝術、抽象藝術、表現藝術等多種藝術于一身,确實是中華民族當時工匠藝人工藝、審美“智巧”的集中表現和結晶。北宋崇甯四年(1105年),當陽峪窯曾立窯神碑,碑文說:“時惟當陽工巧,世利瓷器。埏埴者百餘家,資養者萬餘戶(葉喆民:《中國陶瓷史》,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3月第1版,第259頁)。”“惟當陽工巧”的贊譽與古梵文對中國瓷器“智巧”的解釋不謀而合。可以說,工藝的“智巧”,既是古代異域對華夏民族的贊譽,也是衡量陶瓷藝術的重要标尺,而柴戰柱的絞胎瓷革命,再次體現了中國陶瓷藝術家的“智巧”,體現了中國陶瓷藝術旺盛的、蓬勃發展的生命力。
文/胡柳波
東湖學院工商管理學院
更多精彩資訊請在應用市場下載“極目新聞”客戶端,未經授權請勿轉載,歡迎提供新聞線索,一經采納即付報酬。24小時報料熱線027-86777777。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