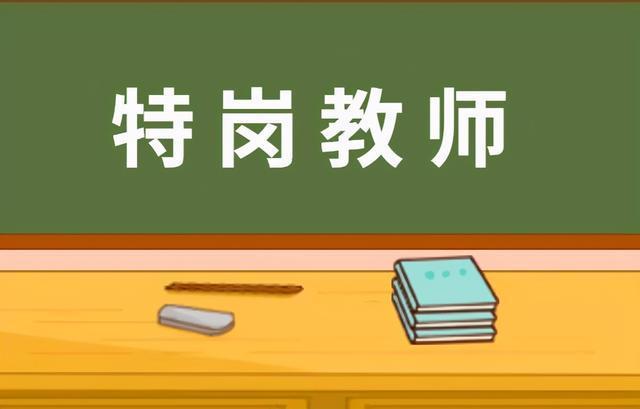本文轉自:陽光天明雅讀院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思想界圍繞資本主義的利弊展開了激烈争論。其中,有人為資本主義而辯護;有人對資本主義給予猛烈批判;也有态度暧昧的中間派。
争論的焦點在于,資本主義對家庭、宗教、國家政權、社會公平和道德規範是否産生不利影響?市場的興起究竟使人們的生活過得更好還是更壞?
這些争論者的立場多種多樣,觀點五花八門。其實,在曆史上,類似的思考和争論不絕如縷,這場争論不過是諸多曆史争論的延續而已。
因而,要理解當代資本主義及有關争論,就必須對資本主義進行思想史考察,厘清曆史上的不同思想家對資本主義興起及其利弊的各種思考。
▌敵視商業的思想傳統
資本主義是建立在人身自由和财産私有基礎上的社會體系,它的興起和發展雖然隻有三四百年的時間,但自古以來,并不缺乏有關财富、金錢和貪婪的各種思想。
穆勒指出,在西方前現代社會主要有三種思想傳統,一是源自古希臘的古典共和主義,二是基督教傳統,三是源自羅馬法的自然法學說。
古典共和主義和基督教傳統是前現代西方思想傳統的主流,羅馬法在12世紀的文藝複興中才逐漸得到重視。
在古典共和主義盛行的古希臘和基督教統治的中世紀,商業、财富、金錢、自私、貪婪在思想上都深受人們的懷疑,它們通常被視為是對美德或信仰的毒害。

在古希臘城邦中,人被視為是政治動物,美德主要指的是勇敢等有利于城邦公共事務的品質。
在古典共和主義思想看來,商業、貿易及對私利的追求将有損社會美德,危及城邦團結。
蘇格拉底曾言,“人們對于賺錢越是看重,他們就會對美德越發輕視。”亞裡士多德認為,對财富的自私追求,缺乏天然的内在約束,很容易走向貪婪狂。
而且,人類物質财富是固定不變的,某些人的獲利必然意味着他人的損失,因而經商不僅是自私的,而且在道德上是損人的,不利于城邦團結的。
其中,最受诟病的商業形式是以财生财或高利貸,因為高利貸的利息源自金錢而不是勞動。
基督教則宣揚慈愛和利他主義,更是鄙視金錢和私利。對于基督徒來說,“貪财乃萬惡之根”,“不可為自己在地上積累财寶”,“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
為了解釋商業的罪惡性,基督教也接受了古典假設,認為任何财富都源自他人的損失,都是不義之财。中世紀晚期,基督教對待商業的态度開始轉變,開始區分欺詐和經商、合法盈利和非法盈利(尤其是高利貸),私有财産和工作價值也得到接受。
但追求财富在總體上還是被視為是對靈魂救贖的威脅,通常是讓地位低下的猶太人去從事商業、貿易和高利貸,以避免基督徒去幹這種雖然必要但卻是堕落之事。因而基督教尤其将猶太人跟商人等同起來,将出賣耶稣的猶大被視為是“最卑鄙的商人”。
穆勒曾指出,資本主義崛起的最重要背景是中世紀末的宗教矛盾和宗教戰争。各種信仰沖突和宗教戰争使斯賓諾、格勞修斯、霍布斯、洛克等現代思想家認識到,共和主義提倡的勇敢美德和基督教的救贖信仰很可能是其問題所在,因而需要尋找新的思想基礎,以使具有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和平地生活。
源自羅馬法的自然法傳統便是重構社會秩序的重要思想資源。古典城邦和基督教會都具有集體性質和強制色彩,而民法傳統則遵循個人主義,國家為個人服務,而不是個人為了公共利益或救贖而犧牲自我。
跟共和主義和基督教對商業的輕視不同,民法傳統因強調私有财産和法律對自由的保護,而有利于商業貿易的發展。
自然法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布斯在《利維坦》一書中便是要證明,基督教信仰和勇敢美德都是不可靠的和好戰的,應該将人們引向溫和的道德與和平的生活。
基督教将虔誠和信任視為美德,霍布斯将其視為迷信和輕信;共和主義将對名譽和權力的熱情視為美德,而霍布斯将其視為戰争的根源。對霍布斯來說,真正的美德應該有利于生活的和諧、交流和幸福,需要行為的謹慎,而這在之前的基督教傳統和公民共和主義中都被低估了。

霍布斯
▌資本主義是一種更文明的社會秩序?
18世紀以來的諸多自由主義思想家便繼承了自然法學家對于社會秩序的重新闡發,試圖證明市場便是一種促進和平而非戰争的社會體制,商業社會是一種自由多元而又和平有序的美好生活。
他們的基本思想是,個人追求私利将有助于整體社會。人們通常從經濟角度認為,個人對私利的追求有助于增進社會的普遍富裕。
其實,17、18世紀的早期思想家主要是從政治和道德角度進行考慮的,他們更為強調的是市場活動的政治安全性和道德平和性。
因為市場經濟是“宗教狂熱的解藥”,跟宗教狂熱與投身政治相比,追求财富可以使人們“和平相處并感到滿足”,赫希曼将這一點概括為利益對激情的馴服。
于是,跟充滿宗教戰争的中世紀後期相比,商業社會就是一種更為文明的社會。這不僅因為利益上的相互競争和相互制衡而使人們避免了戰争,還因為市場制度對于人性的重新塑造。
市場不僅是經濟體系,也是一種紀律體制。它促進了分工與合作,使人們可以更加自制地和平相處,使人們可能顧及他人的需要而抑制甚至放棄自己的潛在激情。
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變成了一個商人,而商人的道德是謹慎、節制而非勇敢、沖動。于是,伏爾泰将證券交易所視為是“和平的集散地”,斯密将追求私利視為是人區别于動物的高貴特點,而對财富和金錢的自私追求在古典共和主義和基督教那裡都是被輕視和敵視的。
市場的和平性并不僅限于經濟領域,它還将擴展到宗教、政治等一切領域。伏爾泰或許是宗教市場理論的最早先驅,他認為宗教信仰自由和市場交換自由是一樣的,而在傳統的基督教思想看來,一緻信仰和共同價值才是政治穩定和社會團結的條件。
斯密指出,市場雖然不能造就少數高尚偉大的牧師和英雄,但它可使絕大多數人通過謹慎節制的和平方式實現欲望。
商業社會使沒有權勢和财富、缺乏智慧和美德的絕大多數人,可以過上和平而體面的生活。于是,斯密堅決反對地方貿易保護,希圖以個體的權利和契約為基礎,重建一個和平的世界開放市場體系。
早期自由主義思想家在對資本主義進行辯護中,也指出了資本主義的諸多問題。自斯密開始,商人對政治的利用、地方保護主義、勞動分工導緻人的片面化等問題就得到了關注。
但對他們來說,這些問題均可得到适當解決,尤其是政府、教育和知識分子在防止危險和确保市場秩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自由主義内部便存在着自由市場與國家幹預之間的内在張力。
斯密、哈耶克更傾向于自由市場,國家職僅需提供最低限度的法律保障,黑格爾、凱恩斯則更突出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的突出作用。
▌資本主義的非契約基礎
對于遭受市場之苦的人來說,自由主義者所描繪的美好圖景似乎過于将資本主義道德化和美化了。于是,面對市場的擴張,保守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開始譴責資本主義的不道德和罪惡。
作為現代保守主義的先驅,尤斯圖斯•默瑟爾将斯密所設想的和平的世界開放市場視為是資本主義對傳統制度的侵蝕。标準化的市場體系不僅摧毀了地方經濟,而且摧毀了多樣化的地方文化和傳統美德。
跟默瑟爾将保守主義跟資本主義完全對峙起來不同,同樣作為保守主義者的伯克則更傾向于商業社會。但他認為斯密等人忽視了商業社會的非契約基礎,市場源自于傳統的風俗習慣,而非個體的人為契約和理性設計。啟蒙知識分子根據理性原則去評判和重建社會制度,反而使一切都變得非法化了,法國大革命造成的無序混亂便是明證。

黑格爾
面對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個體與共同體之間的張力,黑格爾則試圖從哲學的高度進行“調和工程”。
受政治經濟學和保守主義雙重影響的黑格爾,思辨性地論證了基于個人私利的市場秩序與整合為共同體而非“社會”的美好願望之間所可能存在的一緻性。“黑格爾是褪去了面紗的伯克”,分析了社會體系背後的倫理原則,并認為現代人因為明白和接受了這些體系背後的倫理精神,而有利于邁向更高的共同體生活。
他跟默瑟爾一樣,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歸屬感,但跟默瑟爾不同的是,他不是守護傳統社會,而是向往一個更加自由更加包容的現代社會。
現代社會的巨大挑戰就在于,既使人們享有個體性和主體性,同時又将這些個體聯系起來,讓他們認同社會體系,從中找到真正的歸屬感。
新教倫理便是既允許自私自利又超越自私自利的一種方式。新教倫理比天主教倫理進步的地方就在于,它将精神力量從彼岸轉向了現世,從少數精英的高尚道德轉變為社會整體的倫理規範。這一點其實已經預示着韋伯對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親和性的經典論述。

此外,黑格爾反對自由主義者從契約角度對家庭、國家和行會的理解,他将它們視為是超越商業社會和自私自利的利他主義集體,而不是契約關系。
或許,在自由主義者看來,黑格爾在自私個體與利他共同體之間的平衡存在着巨大的風險,因為他将“上帝”和國家置于個體的自由交換之上。
當資本主義出現嚴重危機時,對共同體的渴求很可能會壓倒個體的自由和自私。于是,面對經濟危機和世界大戰所暴露的資本主義的無序性和無根性,弗萊爾等人開始更加懷念和依戀鄉村共同體,向往民族共同體。
這就使默瑟爾、伯克等人的溫和保守主義逐漸走向極端保守主義,企圖通過戰争和極權國家來實現共同體的複興,最終卻為法西斯主義鋪就了道路。
▌少數人的剝削與多數人的憎恨
無論是斯密等自由主義者,還是默瑟爾、伯克等保守主義者,其實都已經注意到資本主義的各種問題,比如從湧入城市但卻難以融入城市的農村流動人口、因技術更新而導緻的貧困或“人為的貧困”和勞動分化對人的負面影響。
對早期左翼知識分子來說,這些問題都體現了資本主義自身所不可能解決的根本矛盾,尤其是階級沖突問題。雖然深受黑格爾影響,但馬克思逐漸放棄了黑格爾的目标,他感到難以調和自私個體與商業社會,因而轉向更為激進的目标,也即推翻不人道的資本主義體制,重新建立使人全面發展的共産主義社會。
同樣是反資本主義,保守主義主要針對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文化弊端和道德罪惡,而馬克思主義則直指資本主義庸俗文化的經濟基礎,認為資本主義便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
資本主義的基礎是自私和貪婪,“将道德錯誤地用在不道德目的上的虛僞方式正是自由貿易體制的驕傲”。
伏爾泰曾将倫敦證券交易所視為是比法院更可敬的地方,而恩格斯卻将其視為是表現資本主義罪惡的最佳場所,因為那裡的每個人都是投機分子和賭徒。
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來看,賭博、投機、高利貸都是不勞而獲,都是不道德的。商業社會使這些投機商人發财的同時,卻通過摧垮先前的世襲地位、民族和宗教而使多數勞動者淪落到了商品的地位,法律上的自由掩蓋了他們被市場力量所奴役的命運。

這種資本主義的自由意味着一種新的奴隸制,勞動者自由得一無所有了,自由得隻能靠出賣勞動力、接受剝削來維持生存。
實際上,資本主義未能如馬克思所預料的那樣“自掘墳墓”,于是,後馬克思主義者需要解釋的一個最棘手的問題便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為何缺乏革命性。
盧卡奇認為,身處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受到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影響,革命者必須首先消除他們的虛假意識,才能使他們獲得真正的階級意識,從而爆發革命。
馬爾庫塞則進一步認為,資本主義是另一種極權主義,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導緻人的低能化和愚鈍化,造就的都是“單向度的人”。
為了應對左翼知識分子的階級理論,自由主義者也提出了針鋒相對的精英理論。
受尼采影響甚大的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的動力在于企業家的創新,競争和創新經常帶來怨恨,而社會主義納粹主義正代表着多數人對少數精英的怨恨。群衆的怨恨導緻企業家不敢投資和創新,導緻經濟的周期性蕭條和衰退。
更為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哈耶克也認為,納粹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市場中的失敗者通過武力和意識形态來謀取利益的絕望嘗試,即使資本主義的福利國家制度也是“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
▌資本主義文明下的個體命運
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講述了這樣一則寓言,一個“野心勃勃的窮孩子”,向往着富裕的生活,希望獲得宮殿般的房子和可供奴役的仆人,于是全身心地追求财富和地位,為了超越競争對手而不得不服務于那些他憎恨的人。
斯密雖然用這個寓言故事警示人們,不要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迷失内心的道德追求,但他還是有些過于相信和期待這個孩子能夠完全融入到商業社會之中。
誇張地講,近現代政治思想史似乎就是在不斷重寫着這一寓言,不斷探尋着這名孩子的可能命運:
或許,他會背着傳統和共同體的負擔,進入到資本主義世界,成為一名身心疲憊地追逐私利的 “商人”;或者,在資本主義世界中享受“共同體富裕”的同時,又口誅筆伐地抨擊資本主義的文化低劣和道德堕落;又或者,試圖推翻“吃人”的資本主義,激進地重建傳統共同體或邁向想象中的更美好的共同體。
但無論遭受何種不公平的結構限制,無論做出何種選擇,他的内心肯定都将是分裂的,掙紮的,痛苦的。在某種意義上,上述各種主義和思想的辯論,各種鬥争和戰争的發生,正是他内心掙紮的某種真實寫照。

人們對“資本主義”的各種誤解,是現代文明史上最大的冤家錯案,很多觀念之争一直延續到今天。
對它的許多讨論要麼有失偏頗、要麼極度張揚。無論觀點保守、激進的人都對它各執一詞,處于極強烈的話語對抗、甚至攻擊。
至于曆史上的重大思想課題,諸如傳統美德與商人倫理、古典智慧與近代普世價值、資本家與勞動者,由觀念的紛争演變出了無數次意識形态對抗、乃至災難。
歸根究底,很多讨論之所以無效,很多災難之所以出現,都是從未界定清楚到底何為資本主義。而最具解釋力定義,也就是劍橋資本主義史中提到的“開放秩序系統”,期間也伴随着種種跌宕、沖突,随着20世紀的曆史最終沉澱于人們的内心,從而化險為夷。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