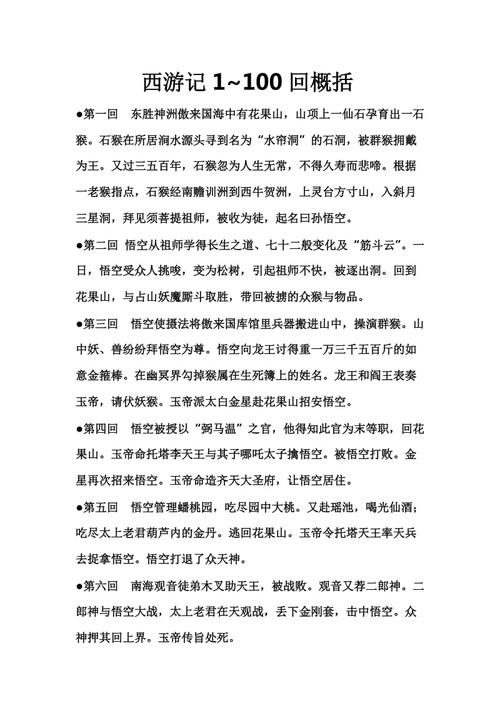作者:複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副教授,文學博士 龔金平
電影《美國女孩》的情節與主題,初看起來與文化沖突有關:上初中的芳儀,在美國洛杉矶度過了人生重要的成長歲月,突然被母親帶回陌生的台灣,卷入身份尴尬、文化不适、自我認同的危機之中。同時,母親身患癌症,父親又為掙錢養家疲于奔命,家庭氛圍壓抑而緊張,這加劇了她與父母之間的龃龉與對抗。那麼,影片要表現的,是身處文化差異和代際沖突漩渦中的少女,如何找到内心的安頓與釋然嗎?

電影《美國女孩》海報
大多數青春片中,都有代際沖突的戲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在追求個性、彰顯自我價值的過程中,必然會有許多莽撞、沖動、困惑的時刻,這與父母的理性、正統産生了某種程度的沖撞與決裂。因此,代際沖突大多數時候與兩代人的心理成熟程度、價值觀、思維方式的差異有關,偶爾也能延伸到時代變遷、社會轉型、文化模式等方面。《美國女孩》的野心顯然不滿足于對親子關系作單一維度的表達,因為影片為母女之間的隔閡與圓融,設置了文化融合、疫情肆虐、生老病死等背景,希冀在一個更為宏大的視野中,展現更為廣闊的成長話題與人生命題。
芳儀對母親的不滿在于,她原本擁有自由而舒展,快樂而恣意的生活。可以說,芳儀将美國的生活看成某種人生範本。這使得身處僵硬、刻闆的學校氛圍中的她,加倍地渴望原先的生活。芳儀更像一位旁觀者和親曆者,洞察着傳統教學模式中存在的不合理、不公平因素,進而呼籲更尊重個性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氛圍。那麼,影片的立意是為了抨擊中國傳統的教學方式和教學理念嗎?從芳儀的精神狀态來看,真正令她身心疲憊的,可能并不是在學校裡被孤立和被排擠的無助處境,而是母親身上的專制、陰郁、悲觀的氣息。
芳儀的母親罹患癌症之後,情緒低落,脾氣有些暴躁,又時常擔心兩個女兒和丈夫的未來,在家庭中制造了焦慮和恐懼的情緒。芳儀渴望一種平和、樂觀、大度、昂揚的人生态度,這種态度指向對自我的信心,對未來的憧憬,而非深陷在焦慮、悲觀、絕望中不可自拔,并對身邊的人施加不可名狀的精神壓力。由此,我們了解母女之間的沖突根源,乃是她們對“責任”“人生态度”的理解南轅北轍。母親之所以情緒不穩定,内心悲觀,不是因為她自私,恰恰是她深感責任重大才充滿不舍與不甘。芳儀則認為,一個人要為自己負責,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哪怕是家人。
芳儀對于母親的誤解還在于,母親偶爾的消沉或狂躁,并非全部源于身體的虛弱,還包括她對平淡無奇人生的意緒難平。以前,母親或許會因為照顧兩個女兒而得到價值體認,甚至設想人生會有更多的可能性,現在,面對惘惘中的死亡威脅,母親可能會突然意識到,她的一生有一種虛度的空無感。
母女之間的隔膜與抵觸,折射了不同文化形态所塑造的迥異價值觀。但是,母親精通英文,又在美國生活多年,她為何對美國文化完全絕緣?說到底,身處不同的人生坐标,面臨不同的人生處境,導緻了芳儀與母親在觀念和行動方面難以合拍。她們在如何面對人生低潮、思考自我的價值體認、界定自我與他人的責任疆域等方面,天差地别,并自我堅持。影片無意于對此進行善惡或是非判斷,而是冷靜地意識到各自的合理性,也清醒地燭照各自的局限,這才是人性與生活本身的複雜性與真實性。
影片的場景大多為家庭和學校,所呈現的也是一些日常性的生活細節、瑣碎紛争和庸常煩惱,勾勒出一個普通家庭在遭遇變故時的強作鎮定,以及父母面對青春期兒女的不知所措,還有青春期少女在校園生活中的不安與不适。影片不時渲染SARS疫情,想以更為宏大的幕布襯托普通人的生存焦慮與尋常憂愁。但是,對于普通人來說,世界的崩塌是那麼遙遠,眼前的紛擾才無比真切具體,也無比尖銳疼痛。
影片大量采用内景,并使用自然光效,整體情感基調昏暗和低沉。這襯托了人物的心情,也以一種不事張揚的方式,還原普通人生活的真實狀态。當然,作為一部影片,其影像語言的局促平淡,也因這種平實的攝影風格被放大。
影片回避了戲劇化的情節設置方式,拒絕用大起大落的情節變故,或者高度煽情的場景,來救贖生活庸常與瑣碎的永恒性,而是以平緩的叙事節奏,凡俗的生活場景和生活事件,帶領觀衆進入一個裂隙遍布的普通家庭,在文化沖突與代際沖突的煙霧彈掩護下,感悟面對人生失落、命運無常的一種豁達心胸與平靜心态。這是影片的動人之處,但也因此讓觀衆怅然若失,一方面觀衆在“日常性”的飽和攻擊中深感情節的蒼白寡淡,另一方面又覺得文化沖突與代際沖突終究是老生常談,由此而延伸至人生感悟,既顯牽強,也容易因淺嘗辄止而顯得尋常。同時,影片回避戲劇化的情節處理方式,固然彰顯了影片散文化的風格和原生态的生活質感,但作為一個完整的故事,人物的和解契機、人物内心沖突得以解決的緣由,仍然需要提供有感染力的情緒依托和邏輯擔保。當影片完全沉浸在日常性中,很容易讓觀衆産生一種錯覺:影片不過是在那些肉眼可見的摩擦中反複渲染,不停徘徊,最後因不知如何結尾而在不鹹不淡的狀态中強行結束故事。
影片最後,妹妹芳安被診斷隻是普通感冒,一家人像是劫後餘生,不由喜極而泣,家人之間冰釋前嫌,生活重歸溫馨而美好的模樣。看起來,妹妹的虛驚一場像是生活的一次貴重饋贈,或像一劑回春妙藥,治愈了這個家庭的諸多矛盾和裂痕。但是,這個結尾的突兀與空洞之處顯而易見,當影片執着地挖掘生活本身的不如意,其主題建構的邏輯也應該立足于人物自我的釋懷與超脫,而不能依賴外界的偶然與幸運。畢竟,人生最大的不幸,未必是遭遇意外厄運;人生最大的幸運,也非與苦難擦肩而過。人生真正的勇敢與幸福在于,能夠坦然面對生活的不測和命運的無常,接受自我、他人,以及人生本身的不完滿,并與這種不完滿和平相處。(龔金平)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