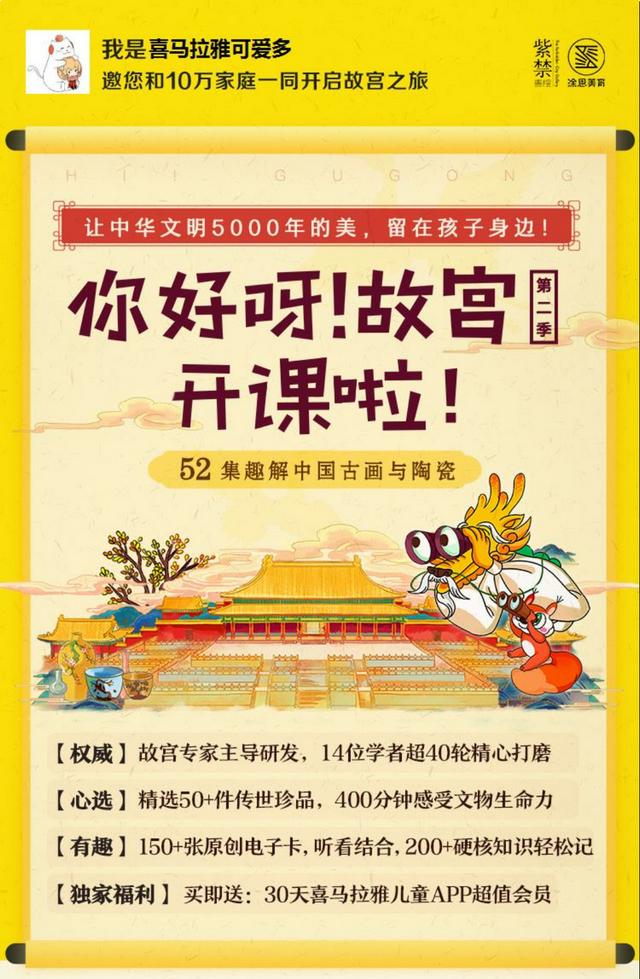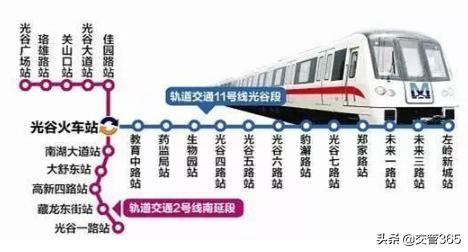肺動脈高壓病人年齡?許昌下雪了,城市明亮得像一座大公園冷風鑽進衣領和褲腳,站在室外,不出一分鐘滿身落白,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肺動脈高壓病人年齡?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許昌下雪了,城市明亮得像一座大公園。冷風鑽進衣領和褲腳,站在室外,不出一分鐘滿身落白。
8歲的小雅不敢輕易出門,不能打雪仗也不能堆雪人,每呼進一口冷空氣,都讓她感覺到脖子被人死死掐着,肺部傳來撕裂般的疼痛,唇部發紫,喘不上氣。每走幾步,都要停下來在原地緩上幾分鐘。
小雅在2014年6月被确診為特發性肺動脈高壓(IPAH),是肺動脈高壓(PAH)的一種。因靶向藥價格昂貴,家人為給小雅治病,已經花費了将近40萬元。而“偉哥”則是有效控制肺動脈高壓最便宜的藥物。
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介紹,肺動脈高壓是一種進行性、緻死性的疾病——不加以治療,可導緻肺血管阻力和肺動脈壓力的進行性升高,從而發展為右心室肥厚,心力衰竭甚至死亡。
PAH患者由于缺氧,指甲、臉頰、嘴唇呈現不同程度的藍紫色,稍稍活動便呼吸急促且無法正常行走。他們每個人都讨厭冬天,每熬過一個冬天就能多喘幾口氣。
輾轉武漢、北京、鄭州後,11月27日,小雅在媽媽王芳的陪伴下前往廣州檢查,仍然沒有找到确切病因。
11月28日,四種治療肺動脈高壓的藥物首次納入新版國家醫保目錄中,分别是波生坦、馬昔滕坦、利奧西呱和司來帕格。盡管各省市政策落地時間不一,但還是給PAH患者帶來了新的希望。
“媽媽我這裡不舒服,我好累”
“停藥等于窒息。”王芳說,小雅現在每天的藥品開銷在200元左右。
事情始于2014年上半年,小雅住了兩次院,第二次住院時發現心髒腫大,醫生建議她前往武漢亞洲心髒病醫院就診。第二天,一家人就坐上了前往武漢的火車。
路上聽着火車轟鳴的聲響,王芳琢磨着最壞的情況:既然是心髒有問題,開胸應該就能治好吧?
到達醫院後,醫生為小雅做了右心導管檢查,把一根細細的導管,從股靜脈(大腿根部)穿刺,沿着血管進入右心房、右心室,甚至送進肺動脈來測定數值。檢查後,小雅被确診為特發性肺動脈高壓(IPAH)。小雅的肺動脈平均壓(mPAP)高達116mmHg,超出常人近六倍。
小雅确診報告。受訪者供圖
北京安貞醫院小兒心髒内科副主任顧虹介紹,目前特發性肺動脈高壓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需終身治療、長期吃藥。2018年5月11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等5部門聯合制定了《第一批罕見病目錄》,特發性肺動脈高壓被收錄其中。
和所有肺動脈高壓患者一樣,小雅的心髒每時每刻都在超負荷運轉。
做個簡單的比喻,心髒像一個泵,負責全身血液抽調;而肺是一個輸氧機,在血液調度的過程中進行氧氣補給。當輸氧機的零部件出現問題,泵就會超負荷運轉,并逐漸衰竭。
還有心衰。小雅每走十幾米就要停下來歇一歇,每次出門都是被抱着、背着,或是用買洗衣粉贈送的藍色小車拖着。她常常坐着一動不動,拍着胸口說:“媽媽,我這裡不舒服,我好累。”
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表示,“在全球有超過5000萬(肺動脈高壓)患者,現有的治療手段還比較有限,這一特别喜歡攻擊年輕女性的疾病,有時需要通過肺移植來治療。”
他介紹,目前臨床應用于治療肺動脈高壓的靶向藥物有四大類,29種藥物。目前上市的所有靶向藥物均不能改善PAH患者的長期生存率,且大部分藥物沒有在我國上市。臨床上常用的藥品有波生坦、安立生坦、西地那非、他達那非等,後兩種被俗稱為“偉哥”。
王芳清楚地記得,當時一盒波生坦(56粒)售價19980元,小雅每月需要服用14粒,再加上其它輔助類藥物,每月需花費五六千元。
在小雅确診前,小雅的爺爺遭遇了一場車禍。沒有監控無法找到肇事者,為了治療,已将家中積蓄掏空。
在小雅确診的頭兩年裡,王芳也曾四處求醫問藥。
那段時間,王芳總感覺喘不上來氣,就像是有人使勁掐着自己的脖子。
下崗之前,她和丈夫在汽車配件廠工作,擔心是粉塵吸入過多對肺部造成損傷,便前往醫院做肺部ct、食道鋇餐、拍胸片等系列檢查。檢查結果均正常,她找不到病因。
西醫看不好就去看中醫,中醫看不好就去小診所裡看。哪怕是往脖子裡紮針,病狀也沒有好轉。
她害怕将來有一天,小雅會和其他病友一樣在家“等死”。
沒有勞動能力,PAH患者無法正常工作,因此無力承擔藥費。但不吃藥更不可能工作,由此陷入惡性循環,嚴重時連下樓散步都要抱着氧氣袋。
她常常在夢中驚醒。她夢到過抱着小雅輸液,當輸液瓶落最後一滴,小雅無力地說了一句“媽媽”,頭就耷拉下去了……
每一次從夢中驚醒,心情久久不能平複,她呆呆地望着窗外無法入睡,眼淚不自覺流下來。她想不通,為什麼這樣的事情會接二連三發生在自己身上。
每當王芳情緒崩潰時,丈夫總在一旁安慰她,告訴她堅強一點。直到小雅病情穩定下來,王芳才稍有好轉。
小雅喜歡畫畫,每一年她都會将壓歲錢交給媽媽,希望能攢着上畫畫班。但由于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要去北京複查,小雅的願望之前一直沒能實現。
“可以結婚,但絕不能懷孕”
“肺動脈高壓的病症太不典型了,沒有一個症狀可以直接判斷為肺動脈高壓。”醫生顧虹說,幼兒的症狀可能表現為突然臉色發白、吃奶費勁、咳嗽;上了學則表現為運動能力下降、暈厥。
她介紹,若是早期進行病因治療,患者或許可以恢複正常或在可控範圍内,但肺動脈高壓從發病到确診往往需要一到兩年,1/5患者超過兩年。
吃了十年“偉哥”、今年25歲的許小美(化名)有時會想,如果自己沒有患病,是不是可以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
家住河南周口農村的她,在出生三個月後被檢查出先天性心髒病。直到八歲,小美的嘴唇發紫得厲害,才到周口市中心醫院檢查。此時并未确診為肺動脈高壓,隻拿了些治療心衰的藥回去。
盡管醫生建議去市裡大醫院檢查,可父母未遵醫囑。之後的兩年,父母把孩子們交給姥姥後便外出打工。
從姥姥家到學校有三裡路,小美記得她總是遠遠地落在姐姐和弟弟後面,怎麼都跟不上,走走就要歇一歇。每到冬天,嘴唇因缺氧發紫得厲害,一吸進冷空氣,胸口立馬就收縮得疼。“我胸口很難受,不想走路不想回家,我甯願餓着也不想走回家。”小美回憶道。
直到她11歲時暈倒在了學校的樓梯上,才前往鄭州做檢查,被确診為由先天性心髒病引起的肺動脈高壓。
直到兩年後,小美才知道這病有多厲害。那時,醫生說病變已無法逆轉,錯過了手術治療的時機。一位醫生曾對她說,“你現在就是跑遍全世界也沒辦法,好好回去養着吧,吃好點,不要感冒。”聽到這樣的答複,小美灰心透頂,幾天不曾開口說話。
初二下學期,小美選擇了退學,再也沒回到課堂。
小美從此過上了與藥為伴的人生。這些年她一直反複看病住院,沒有經濟來源。家裡的地一年種兩季,得等到莊稼賣了才有收入。每次父親送錢過來時,她的心理壓力都很大。2016年,她每個月的藥費在兩三千元,“實在是拿不出錢了。”這一年,小美斷了半年藥。
斷藥後的小美連100米都走不了,經常咯血。父親見情況不對,便帶她去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就診。這一次,三種靶向藥聯合使用才暫時控制住了小美的病情,每個月藥費支出增至六七千元,父母不得不向親戚朋友借錢。
父母在醫院照顧小美,姐姐已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但為了籌錢給妹妹繼續治病和還債,姐姐放棄上大學,和弟弟一起打工去了。面對姐姐的決定,小美覺得愧疚遺憾又無可奈何。
出院時,醫生要求小美繼續三聯用藥。她覺得無法負擔,問醫生如果不吃藥能活幾年,醫生說好的話兩三年。
當時,小美已經訂婚了。交往前,小美便将自己的身體情況告知男孩。男孩沒有因病放棄她,男孩的父母也表示接受。
小美害怕爬樓梯,對PAH患者來說,每一階樓梯都像是一道搏命關口。
她記得,過去凡是遇到有樓梯的地方,都是那個男孩背着自己上去。男孩個子挺高,他家在三樓,每次小美去他家時,都是男孩背着小美。“他力氣可大了,能背着我一下子沖到三樓。”男孩的爸媽問以後怎麼辦,他總是回答:“我願意背。”
那次,男孩的父母來北京看望小美時曾向醫生咨詢,知道未來不可能要孩子後,态度就變了。
2019年初,第二季醫療紀錄片《人間世》放映後,其中孕婦吳瑩的故事引起了争議。患有先心病激發肺動脈高壓的她堅持生産,不幸離世。
“凡是有肺動脈高壓的婦女都禁止懷孕。”顧虹介紹,若是懷孕,患者死亡率高達50%~70%。每當有育齡女孩過來,顧虹都會問患者是否有男朋友,并囑咐孩子的父母,可以結婚,但絕不能懷孕。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呼吸與危重醫學科易群教授警示,“女性,尤其育齡期女性更易發生(PAH),女性發病率是男性的2~9倍。”
那次出院後,男孩沒有拗過父母的意願,慢慢跟小美斷了聯系。
“我會不會把家裡吃窮”
比起小雅和小美,家住呼和浩特、今年40歲的焦慶梅也許是幸運的。
她在22歲生完孩子後身體逐漸出現問題——30歲之前,她總覺得頭暈氣短,去醫院檢查說是心髒缺血和營養不良。她也曾暈倒,經曆多次搶救,直到2009年才确診為特發性肺動脈高壓。
過去的十五年,焦慶梅和丈夫開了間40多平方米的蔬果店,月收入4千元左右,但她每月藥費支出就占了3千元。
做果蔬生意起早貪黑,她的臉和手上都是凍瘡,一根手指頭腫得像兩根,每天回家後得整晚吸着氧半坐着睡覺。
焦慶梅床邊的制氧機,她每天睡覺時都需要吸氧一整晚。 受訪者供圖
确診後的這些年她認識了140多位病友,有時一個月或者一星期病逝的病友就有八九個。
“得這個病,随時都會離開。”焦慶梅每每獨處時都會想象自己離去時會是什麼樣子。
有一年冬天晚上,慶梅和丈夫在店裡工作,她突感不适,丈夫得待着看店,于是給父母打電話希望能過來帶她去醫院。慶梅看到頭發花白的父母走過來時,心裡想着“與其這麼痛苦,不如死了算了”。
她站在街上,哭着把父母趕得遠遠的,然後用盡全力使勁砸路邊的廣告牌,手砸腫了,過路人像看“神經病”一樣看着她。
父母含着淚站得遠遠地觀察着她的一舉一動,待她情緒穩定一些之後,走過去扶着她說:“孩子,我們回家,咱回家去養。”
這十年裡,焦慶梅的身體一直在走下坡路,曾多次暈倒。
她清晰地記得每一次暈倒時的感覺,“第一次感覺特别涼,渾身發抖。第二次暈倒時孩子在身邊,醒來的時候眼睛珠子要掉出來了,瞪得特别大,特别疼。我努力想要眨眨眼眼睛,告訴孩子沒事了,但肢體給不出任何動作。”每次暈倒,她起初都覺得是一個解脫,緩過來後又寬慰自己,活着或許也是一個安慰。
慶梅和父母住得很近,走路也不過五分鐘的距離,但這幾年她很少主動去看望父母,不是不想去,而是怕父母看到自己呼吸不暢更擔心。
她的父母均已70多歲,母親宮頸癌晚期,目前在醫院接受化療。慶梅每天在蔬果店裡做好飯後,丈夫騎着小電瓶車把飯送到醫院裡。父親的心髒前段時間剛做了第四個支架。她擔心若是自己出現什麼意外,父母會撐不住。
起初,醫生對慶梅說藥物幹預治療生存期可以往後延幾年。她覺得哪怕是三年都行,隻要能看到孩子上高中就好。
如今,她的孩子即将參加高考,有一次孩子回家後嗓子有些啞,慶梅問孩子怎麼了,孩子說學校的水太貴了,不舍得喝。老師也多次打來電話,告訴她孩子在學校不好好吃飯。孩子也曾認真地問她,“我會不會把家裡吃窮?”
自己會不會把家裡吃窮,這也是她的擔憂。
焦慶梅購買一盒靶向藥波生坦價格小票。受訪者供圖
北京愛稀客肺動脈高壓罕見病關愛中心副理事長李融介紹,患者平均每年按照醫囑充分用藥需要6~20萬元,不充分用藥也需要3~5萬元。
“80%的患者沒有充分用藥,有些患者充分用藥1~2年後用不起藥了,就減少了量。如果最後放棄用藥就會死亡。”李融說。
焦慶梅每天需要吃的藥。受訪者供圖
小雅在确診後,“搞錢”成了王芳一家的生活主題。為了掙錢,一家人每天就像陀螺一樣,不停地在轉。
每天清晨四五點,60多歲的奶奶就要起床去附近的腐竹廠裡上班,其餘的時間還需要和小雅爺爺一起打理農田。爺爺車禍後右眼失明,失去勞動能力,每天騎着一輛三輪車接送小雅。爺孫倆的午餐往往是方便面或是速凍餃子。
王芳則每天要趕到城裡的賣場工作,午休和下班後還要做兼職,回到家已是深夜。即使這樣,她一個月也隻能掙3400元。午飯她隻吃街邊6元一個的卷涼皮,多花一分錢就像是吃掉孩子的命。
許小美的父母同樣如此,為了給女兒治病,父母在距離家五六百裡地的地方承包了50畝地,後來慢慢增加到100多畝。種地是家裡唯一的經濟來源。
最開始的6年,小美父母用塑料和木棍在田野中間的荒地上撐起了一個棚子,沒有電,夏天就像蒸籠。之後的這些年,父母住在附近一家廢棄工廠的小平房裡,房子門口有兩個用來裝水的藍色化工塑料桶,生活用水需要從别處運回來。農忙時節兩人天微微亮就得起床,晚上10點才回來,很多時候一天都吃不上飯。
許小美父母平日居住在廢棄工廠小平房内。受訪者供圖
每次遇到小孩子,小美總是忍不住逗一逗。可疾病打破了她的人生計劃,和男孩分手後的兩年時間裡,她的情緒有些糟糕,她認為自己成了累贅。她曾設想,是不是自己離開後父母不用再這麼辛苦了?如果沒有生病是不是有機會上大學、是不是已經結婚了?
雖然近年來有些藥物的價格已降至患者可接受的範圍,但每個月足量用藥仍是一筆不小的費用。北京安貞醫院小兒心髒内科副主任顧虹在開藥時,總會詢問患者或家屬的工資,“(家人)明明知道有哪些藥可以救命,但就是用不起藥。”
救命藥“偉哥”
目前中國還沒有一個針對肺動脈高壓的正式的流行病學調查,因此無法獲知患者的人數規模、發病情況等重要信息。
肺動脈高壓靶向藥物表 愛稀客提供
西方國家已批準俗稱為“偉哥”的西地那非和他達那非用于成人PAH的治療。盡管在中國,“偉哥”類藥品的适應症隻注冊了治療男性勃起功能障礙(ED),暫無治療PAH的适應症,但由于其療效可靠、價格便宜,已成為我國PAH的一線治療藥物。
“偉哥是我們治療肺動脈高壓的第一選擇,是不可或缺的基礎用藥。”顧虹介紹道。
盡管“偉哥”類藥物在中國治療PAH已有很多年,但一直屬于超藥品說明書用藥(注:指藥品的相關情況未在藥品說明書記載範圍内的用法),“偉哥可以舒緩肺部血管利于血液循環,在使用前需要和家長簽知情同意書。”顧虹介紹。
起初,小雅使用的靶向藥物是波生坦,迫于經濟壓力,王芳不得不停用波生坦,在病友的推薦下換成了西地那非,後又改為他達那非與安立生坦的聯合用藥。
一盒安立生坦售價3580元,聯合用藥一個月藥費在6千左右。服用了四五盒之後,王芳又不得不将安立生坦停掉。盡管當時醫生要求加上,但實在是加不上了。“醫生知道我們這些病人的處境,看着孩子無奈地搖頭。”
除了在用藥上一退再退,複查的日期也在不斷往後推。
按照醫囑,小雅需每隔三個月去北京複查一次,每年做一次右心導管檢查。最初是三個月一次,後來是半年一次,今年到目前為止隻去了北京一次。最後一次做右心導管檢查還是在2017年1月17日。
去北京複查一次至少要1萬元,做右心導管則要3萬元,“未來如果不攢夠一萬元,就不去北京複查了”,王芳說。
今年618,王芳的朋友圈和病友群都在研究怎麼合理使用“滿減”,用更少的錢搶到更多的“偉哥”。這也是這五年來,她第一次嘗試在網上買藥,“實在是沒錢了,搶藥時心情很忐忑,但這個價格特别誘人。”最後她花了2000多買了幾盒他達那非,折合下來平均一片60元。
一天一片,藥很快就吃完了。
在許昌,一片他達那非售價為126元。王芳以為鄭州的售價或許會比許昌便宜,便在8月20日帶着小雅去鄭州購藥。沒料到的是,鄭州他達那非的售價和許昌的售價并無差異。那天,她本計劃一次性購入40盒,但藥店的庫存遠遠不夠。
在确診PAH後,許小美一直靠着西地那非續命。
每次去買藥,旁人都會投來異樣的眼光。“我們通常是10盒20盒買的,有人會問我為什麼吃偉哥,我就給他們宣傳。”小美說,也有朋友表示不解,她隻能無奈笑笑。
當冬天來臨,小美在大多數情況下嘴唇呈藍紫色。有好友看到她的嘴唇顔色,曾問小美“是不是中了蛇毒”。
去年十月,她成功申請了一個藥物援助項目,她免費獲得一年馬昔騰坦藥物援助,但每次取藥的過程對她來說既是求生,也是一次不小的挑戰。
每到取藥的日子,她要先聯系村裡的順風車司機。都是淩晨3點多起床,趕在9點前到達鄭州。
若不用複查,争取當天往返。複查的話,就在醫院附近的民宿裡将就一晚。民宿裡的房間隻夠放下一張床,隔着木闆能聽到隔壁的人說話。
“手機步數顯示超過2千步我就受不了了。”每一次取藥回來,小美第二天怎麼都睡不醒。
免費藥物援助即将到期,一盒馬昔滕坦售價9千多,她眼看難以為繼。小美決定再嘗試申請一年,“哪怕是幾個月也好”。
體面的生活
《中國肺高血壓診斷和治療指南2018》指出,2011年我國研究表明,IPAH 的1、3 年生存率分别為92.1%、75.1%,基本達到西方發達國家水平。
許小美的身體時好時壞,經常咯血。每一次咯血時她都感到恐懼,喉嚨裡一直往上翻,一咳嗽全是鮮血,胸口撕裂般地疼,躺下了就不想起來。她沒有固定的工作,平時一個人待在老家,為節省體力,出行全靠一輛小電動摩托車。
小美的主治醫師,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心血管外科主任醫師張建卿曾說,許小美還有最後的手術機會,若是半年内拖着不做手術,最終會走到心肺移植的那一步。
得知這個好消息後,小美忍不住在朋友圈和各個病友群裡說,“我有救了!”那段時間,她不僅帶着過往的檢查記錄奔波于各個醫院向醫生咨詢,還向曾做過同樣手術的病友确認術後效果。
一位醫生告訴她,并不是做了手術就一定能痊愈,肺動脈壓力若是降不下去會更嚴重,後續可能會面臨更高的治療費用。病友告訴她,手術之後比之前吃的藥更多了。
小美不想冒險,她不忍心再次看到家人傾家蕩産為她治病,等到了需要心肺移植才能活命時,她決定放棄并登記了器官捐獻。“我盡力看病,看到什麼程度就是什麼程度,死亡并不是結束,可能是新的開始。”小美說。
最近一次複查時,醫生建議焦慶梅考慮做肺移植。她也不願因為自己掏空家裡的積蓄,甯願少花一分錢,也想留給孩子。
她家樓下的服裝店裡有件紅色風衣,她經過時總忍不住看上幾眼。母親說要不買下來,她借口說穿紅色或許不好看。
2018年7月,複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在澎湃新聞采訪中指出,除了特發性肺動脈高壓外,由其他病因引起的肺動脈高壓十分常見,卻沒有任何一種藥物在國家醫保範圍内。如果(靶向藥)能夠納入醫保,可以讓更多患者有治療的機會,這些人最起碼能夠有體面的生活。
5個月後,内蒙古自治區醫保局正式發文将肺動脈高壓所有治療途徑的藥物納入醫保目錄,近年來,浙江、江蘇、湖南等省區已将個别治療肺動脈高壓藥物納入當地醫保目錄或大病保險支付名單。
11月28日,新版國家醫保藥品目錄中,又有70個藥品加入到醫保報銷的行列中來。其中4個治療肺動脈高壓的藥物首次納入醫保,分别是波生坦、馬昔滕坦、利奧西呱和司來帕格。
廣藥集團旗下白雲山制藥總廠副廠長王健松表示,未來有仿制國外已上市的标準用于肺動脈高壓20毫克劑量的西地那非的計劃。
焦慶梅(左二)在世界肺動脈高壓日參加活動。受訪者供圖
每到複查的日子,王芳會背一個雙肩包,裡面裝着衣服,胸口還有一個小包,裡面是證件和錢,手裡再拉着一個藍色的小車,小雅坐在上面。随着小雅慢慢長大,小車已經換了3輛。
小雅複查完回家的地鐵上,手裡的藍色小車是她平日裡的交通工具。 受訪者供圖
辦住院手續時,王芳通常會将小雅暫時安置在醫院走廊的椅子上。小雅擔心媽媽會把自己扔掉,總是要求媽媽把胸口的小包留下來。“有了這個小包,她覺得我一定會回來。”王芳說。
今年暑假,小雅終于參加了她夢寐以求的畫畫班,她對前來采訪的記者說道,“阿姨,我以後想當畫家。”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