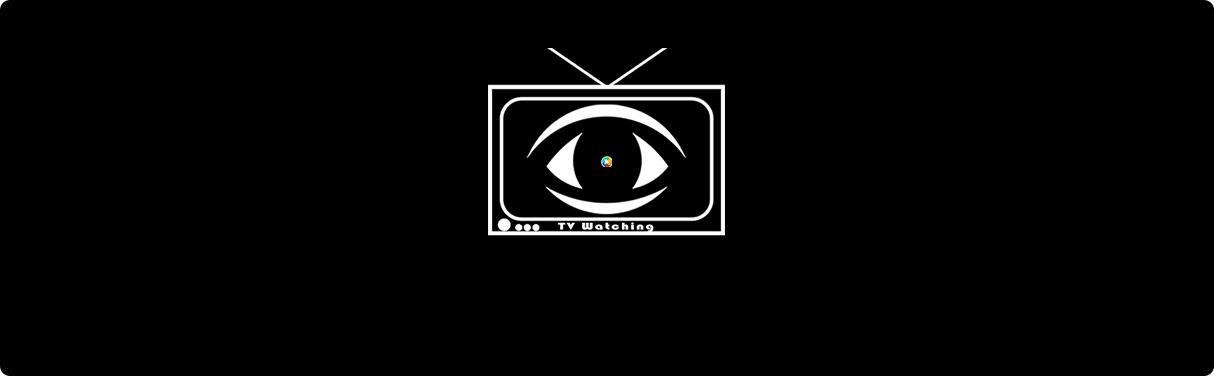劉勰《文心雕龍·隐秀》屬殘篇已是學界共識,另有四百餘字補文,經曆代學者考證,系明人僞托,故不為本文論述取用。因殘存文字有限,“隐秀”的内涵“诠明極艱”(黃侃語),縱有諸家勘釋,仍難定論,其中對“秀”的解讀是曆來争議的關鍵所在。
前人釋“秀”的差異及原因
前人對“秀”的解釋,可歸為三個層面。第一,以黃侃、範文瀾、周振甫等為代表,從修辭學角度着眼,認為“秀”即“秀句”,“像鶴立雞群,是一篇中的警句”。第二,以劉師培、詹锳、傅庚生等為代表,以風格論為立場,認為“秀”是有别于“隐”的文學、美學風格,體現為柔性的“秀美”特征。第三,以張少康、祖保泉、葉朗等為代表,從形象論切入,主張“隐秀”是創作文學意象的方式和原則,“秀”即為“秀象”。

以上三種觀點分别從不同視角切入《隐秀》篇文本,皆觸及“秀”的某些本質特征。客觀地講,“秀”屬于模糊概念,“有一定的自由度,以容納各種變形和千奇百怪的再定義”(宇文所安語)。而從文本屬性來看,殘篇《隐秀》為“開放的作品”,相較完整的閉合式文本,其内容具有更強的不确定性。因此,“秀”的意涵勢必呈現出多元性。事實上,前人已意識到“秀”及《隐秀》篇文本的特殊性,故堅持己見的同時也肯定部分異質觀點。例如,周振甫等在将“秀”認定為“精警格”的基礎上,也承認其涉及某些藝術表現的内容;詹锳等讨論“隐”“秀”風格時,主要針對“隐篇”“秀句”的文本樣态;張少康等在将“隐秀”作為“意象”書寫原則的同時,不得不引“秀句”說做補充。之所以承認“秀”的多義性,更多是闡述策略上的妥協,但如此闡釋往往忽視了“秀”的諸多意義間的聯系與區别,有時還會令觀點含混。
“秀”内涵的層次性
“秀”的内涵雖多樣,但細讀文本,不難發現,劉勰論述“秀”是沿着“釋名章義”“選文定篇”“敷理舉統”的嚴密邏輯展開的,絕非模棱兩可。因此,“秀”必然有明确且唯一的文本含義。但基于文本字面内容的本義不等同于作者本意。作者本意是指作者原本想要通過文本所表達的意圖。這種意圖潛藏于文字表面之下,同文本本義一起構成概念内在的張力。對“秀”内涵的重诂要充分重視文本本義與作者本意的共構性。
針對“秀”本義的考釋,首先要重視《隐秀》篇在《文心雕龍》中的位置。《文心雕龍》體大慮周,組織嚴密,《隐秀》篇的主旨必然服從于整部書理論體系的構建。其所在的創作論部分,《神思》《體性》等以下七篇是帶有總述性質的篇目,另有《聲律》至《附會》等十一篇分述語言技巧。《隐秀》位于分述篇目中間,因此其主旨應同相近篇目如《誇飾》《事類》等類似,是關于“隐”和“秀”兩種修辭手法的介紹。
其次要以《隐秀》篇的文本論述為重要依據。從對文本的忠實度上講,将“秀”理解為“秀句”最合理。“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是劉勰給“秀”下的定義,即“秀”是篇章畛域内最出衆的部分。《隐秀》篇文本中有兩處直接以“秀”論句,“篇章秀句,裁可百二”“秀句所以照文苑”,舉例“秀之為用”時,則援引了王瓒《雜詩》中的“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魏晉以來,文壇對佳句頗為關注。理論闡發方面,陳琳、陸機、陸雲、沈約等都曾以“片言”“警策”“妙句”“出語”言之。文學實踐方面,史書記載的相關事迹可印證當時煉字析句之盛。例如,《世說新語·文學》:“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既成,公與時賢共看,鹹嗟歎之。時王珣在坐,雲:‘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晉書·王坦之傳》:“坦之标章摘句。”《南齊書·文學傳論》:“張眎摘句褒貶。”因此,劉勰立專篇談“秀句”也是對魏晉以來文壇審美風尚的呼應。
劉勰使用“秀”這一概念的本意在《隐秀》篇殘文中無迹可尋,但通過他未照搬當時的術語以描述文章中的“超越常音”之句,而選用“秀”這個極具審美意味的詞彙也能窺測一二,其應有以“句”為依托标示“秀”的風格的意向。那麼,劉勰為何選擇“秀”來命句,“秀”又呈現出怎樣的美學特征?
以往研究對“秀”的美學表現的解讀傾向于陰柔美的論調,但“秀”作為劉勰褒贊的審美理想,若僅是柔婉媚态,豈不同他所批評的當世“風昧氣衰”“負聲無力”的文風相近?劉勰推崇“秀”,緣于其昭示的風格符合儒家詩教“雅”的取向。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的解釋,“秀”的本義為“禾黍”,除贊美植物外觀秀茂外,還有重實重質之意,引申至形容文學審美也應是對外在辭藻和内在思想的雙重肯定,正所謂“才情之嘉會也”。這與聖人文章“銜華而佩實”的特征具有一緻性。
南朝宋齊之間,原本清新雅麗的五言古調在南朝樂府民歌的影響下形成一種新體,以江淹、鮑照為發端。這種詩歌新風颠倒詞序,不避危仄,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中評價道:“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具體如鮑照之“君子彼想”,實應為“想彼君子”;江淹的“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則應為“孤臣墜涕,孽子危心”(孫德謙《六朝麗指》)。劉勰并不認可這種依靠造語驚奇博得讀者關注的做法,所以便以喻示着文質合一、窮力追新但不失雅麗之“秀”作為糾正險俗詩風的新風格。
至于“秀”代表的風格之剛柔,《文心雕龍·雜文》有“信獨拔而偉麗”同“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中的“獨拔”互文,可見在劉勰看來,“秀”應有前人所說的氣勢奪人、恢宏之剛性特征。但《文心雕龍·定勢》言:“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此原則雖為劉勰針對詩文整體體勢風格而言,但也适用于章中辭句。具有“秀”之風格的文本應不拘剛柔,包舉洪纖。所以,優柔如“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瘦硬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皆能為詩中秀拔之句。
“秀”與“隐”之間的複雜關系
至此,無論将《隐秀》篇中的“秀”理解為“秀句”還是“秀”的風格,其先決條件都将“秀”視為純粹獨立的概念。如果劉勰僅冀圖表達“秀”之風格,則完全可以“隐篇”“秀句”為題,進行更詳盡的論述。他解釋“秀”,與“隐”對舉,應該同《風骨》《情采》《比興》等類似,暗示了兩個概念彼此獨立但不對立。
以《隐秀》篇殘文中僅有的一段描述“隐”“秀”關系的文字為證,“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故文之英蕤,有秀有隐”。傅庚生解釋說:“‘源奧而派生’的自然以‘複義為工’,‘根盛而穎峻’的自然以‘卓絕為巧’。”所以,“隐”和“秀”的關系應為并立共生。二者看似彼此獨立,但實際上具有内在關系,“心術”和“文情”本質皆為内心情感,因此,“隐”“秀”具有同源性。“秀”雖以鮮明獨拔示人,但支持它“英華耀樹”的是潛藏于地下的茂盛的根,而這個根就是深隐的情。“秀”應是“秀出”與含蓄的結合。在“秀句”創作中,這種相生相諧的狀态十分明顯。如《詩經·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景寫情,融情于景,将個人對軍旅生活的無奈與辛酸以春季楊柳、冬季雨雪的景緻更叠表現出來。《古詩十九首》中隐沒情志的“秀句”,如“浮雲蔽白日”,李善注曰“以喻邪佞之毀忠良”,而“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則暗示遊子不忘故鄉之意。大量文本證明,劉勰對“秀”的認識具有其深刻性,這種有“秀”有“隐”的創作及表現原則應是《隐秀》篇所表達内容的精華所在。初唐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受劉勰“秀”論影響頗深。元兢在序言中評“落日飛鳥還,憂來不可極”兩句,說“扪心罕屬,而舉目增思,結意惟人,而緣情寄鳥,落日低照,即随望斷,暮禽還集,則憂共飛來”。顯然,他對于“落日”兩句的“秀”的理解也是從景中含情、情興意顯等方面去把握的。
因此,劉勰“隐秀”之“秀”的内涵是文本本義與作者本意“一體兩面”的結合,其本義為“秀句”,是對前人論述“章句修辭之學”傳統的繼承,以及對當時沉迷佳句創作與批評風氣的回應。同時“秀”也表達了一種“秀”之風格與“隐”“秀”相間的審美原則,是劉勰對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弊病及創作本質深刻反思後的思想結晶。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延馼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