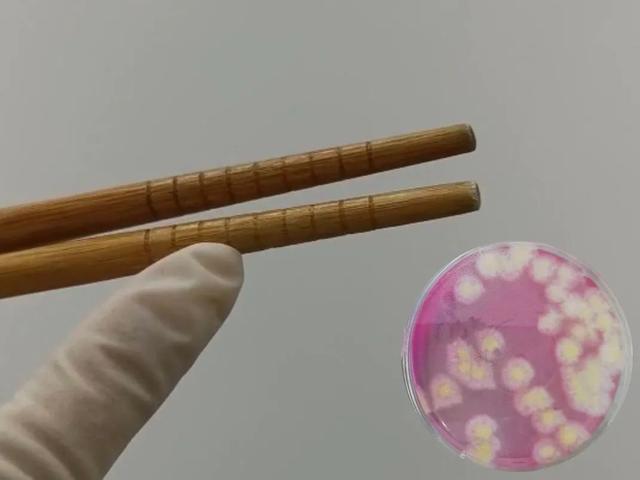《這才是你的世界!時間與空間的思想實驗》,簡易 著,漢唐陽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2年7月版。
人們滿足于單向展示,更别說和小孩對話
蕭三郎:《這才是你的世界!時間與空間的思想實驗》這本書從時間、空間到愛因斯坦、牛頓、伽利略……很多理論經過拆解,令人有恍然大悟之感。這本書的寫作出版,是你自己的想法,還是一種策劃?
簡易:這本書的寫作過程非常順暢,信筆而書,如泉湧,如暢飲,妙處難與君說。要說策劃,唯一動過念頭的可能是中英日文同步發行吧,可至今還懶得行動。
不過,最後寫成這模樣,還是有一點自己的想法的。這個想法可能出于一個誤覺。我已離開學術界,沒有拼業績成果的壓力,也不受學術著作規範的羁絆,可以放開了寫點不一樣的東西;然後就是經濟上,接近低度的财務自由,不為柴米油鹽所困,沒有文字扶貧的任務。這兩點一結合,讓我産生一種誤覺,似乎自己是個自由人,可以自由寫寫我所理解的這個世界。而我和大人交往往往有障礙,一是由于自己的性格缺陷,二是覺得大人沒治了,我隻想和未成年人說說話,于是就有了這本書。
蕭三郎:看完書自然就特别想了解作者的背景,你的個人教育、知識實踐能否給介紹一二?
簡易:我出生于中國,留學于日本(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工作于美國,現在接近無業遊民。接下來可能居無定所,不知所終,因為計劃疫情結束後出遊一兩年。不過,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永遠隻有閱讀和思考。
我不看電視,不刷媒體,不玩遊戲,很少應酬,很少說話,生活簡單,大把時間全砸在閱讀和思考上。已經多年不看虛構作品了,幾乎隻讀專著,經常一讀就到深夜兩三點,有時直接讀到天亮。體質上,好像熬夜也不傷身。每周定量閱讀,每周面壁冥思,幾十年如一日。
我的世界裡,沒有文科理科之分,沒有中外、東西之分,不受學科、語種、地域限制。書房裡,讀書專用的豎屏顯示器裡,名副其實的萬卷書,富得流油;住在一個山巅老破小裡,俯瞰大城,一覽衆山,有時就不免想得飄逸一點點──我的生活很無趣,不是人過的,不值得多說。
蕭三郎:《這才是你的世界!》全書通過馬克老師與安頓之子安得等的談話一一展開。“對話體”,無論中國儒家對話的《論語》體,印度的佛陀僧團,還是在西方的蘇格拉底的哲學園裡,師生們都習慣使用啟發性的對話來深入交流問題,探讨知識。你是不是有意在做某種形式的複活?
簡易:很高興你注意到我在對話體上的用心。采用對話體有很多考慮,其中一個妙處是,在對話體裡,單向通行的展示走不通,單向使力的推行也走不遠,因為對方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受力體,你很快就會失去着力點。你隻能見招拆招,不僅要看人說話,還要看場景說話,看氣氛說話,看話題說話,看進展說話,适時調整,如氣功裡的推手,雙人舞裡的流線,棋盤上的走勢。對話體可以瓦解霸道,吹散一些戾氣和陳腐的氣息。
往大處說,自古聖哲,多住在對話體裡,其中自有深意。不僅是你提到的那些思想史上的經典是對話體,你看伽利略的那本《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也是對話體。書中虛拟的三個人對話了四天,讨論的是當時最尖端,也是最尖銳的科學話題,而且是拿命在對話。因為那本書後來被列為禁書,作者因異端嫌疑被判終身軟禁,終身不許再寫書。據說,伽利略被逼違心地宣布認同教會的宇宙觀後,曾經喃喃自語道,“但是,地球依然在轉啊……”
今天,對話體的書已經不可能被當作學術著作或嚴肅作品對待,這無所謂。問題在它的反向上,你可以看到人們總是滿足于單向通行展示立場和觀點,灌輸教條和知識,沒有耐心和敬意去推動對話和合作,更别說尊重小孩,和小孩對話了。偶有朋友來訪,我都會請他們席地而坐,大家都降低一點,屈尊一點,試試看可不可以坐而論道。其中就有一種想法,讓大家一起進入你提到的那種論語、蘇格拉底、佛陀僧團、伽利略的氣氛中。如果全世界的要人有事都席地而坐,世界就會比我們看到的和善很多。
書中的對話,有不少是模仿我平常和小孩的對話,有些甚至就是實錄。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本書是一個父親寫給另一個父親的書。如果一個父親讀完後,模仿着開啟一場和自己子女的對話,也許他會發現這本書還是有幫助的。不僅僅是知識,還有對話的方式。若孩子也學會這種方式和别人對話,世界就會比我們看到的和善很多。
教育中,請不要花錢請人來摧毀自己的懷疑
蕭三郎:我之前是《新京報書評周刊》的主編,現在也關注教育前沿話題。我個人在參與編制一套中國中小學生的“項目式學習”(PBL)大型圖書。我們看到美國“密涅瓦大學”這種沒有校園的大學出現,企業家埃隆·馬斯克也提倡孩子們通過“項目式學習”獲得未來的人生入場券等。能否分享一下你的教育理念?
簡易:我們現在聊的這本書也是項目式學習的一個例子。我計劃是出版三部曲(《時空》《信息》《物質》),每一部都包含一個項目。經過步步升級,學以緻用。這在講時空的這本書中可能不太明顯,因為時空的課題太虛了,太大了,難以做出一個具體的成品,退而求其次,倒數第二章《秘密工程》就是這個項目成果了。下一本寫信息,書中将完成另一個項目,通過設計和編程做出一個IT産品,并争取做到每個讀者看完後都可以如法炮制。
你說的“沒有校園”,可能是一種解脫。更準确地說,應該是沒有固定的校園,流動校園也是一種對話,是學生與不同場所的對話。從師徒制、私塾制、神學院發展到今天,是一個從屬關系逐漸松散的過程。受教者與施教者以及場所可以是開放的關系,1對N的關系,可以像一個吃貨和一千家飯館的關系。
蕭三郎:數理邏輯、力學這些課都很難學,你是如何通過啟發式聊天讓你的兩個孩子在十三歲就全部掌握這些的?孩子們學得累不累?
簡易:這些年光顧着埋頭前行,不曾回頭看過。小女9歲時就知道自己四年後要上大學了,因為有哥哥的前例在那裡,她覺得隻需“複制 粘貼”就可以了。最後那個問号,我可以替他們先回答一句: 學得不累。因為我教得不累嘛,我們之間本來就不存在“上課”這個詞,也不存在“學習”這個詞。
蕭三郎:特别喜歡你書中有一句話:“好問題不一定有好答案,但好問題自有好解法。”當代人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會問問題。現實生活中、科學研究中以及面對人類的困境、現狀以及未來時,我們會發現其實沒有“标準答案”。你有什麼話要送給那些腦袋和思維習慣了“标準答案”的朋友嗎?
簡易:看看一些大學生在講座或會議上的提問吧,那可真是慘不忍睹。學問上,人生中,處處是問題,你連問題都問不好,還想要個好結果?而且,好問題不僅僅會帶出好解法,還會成為好的驅動力。你前面提到的“項目式學習”,在日本被稱為“問題解決型學習”或“課題解決型學習”,找到好問題或好課題,被放在第一步,這也正好印證了你對這代人的憂慮。
标準答案是用來質疑的,而不是用來背誦的。這和答案正确與否無關,而與批判性思維有關。
你提到的“現實生活中、科學研究中以及面對人類的困境、現狀以及未來”,都充滿着不确定性,我在書中也一再強調這一點。如果真有人能消除那些不确定性,能提供一套标準答案,他為什麼要洩密給你?
還要考慮進去的是“标準答案”的供應商,知識的供應商。請辨識,知識裡充滿了權力的暗器。如果你活在歐洲中世紀,就算爬上了社會食物鍊的上層,也隻能從教會那裡批發“标準答案”,然後販賣給對地心說半信半疑的學生。這不是教育,這是花錢請人來摧毀自己的懷疑,這是花錢請人來煮熟好問題的種子。
蕭三郎:《這才是你的世界!》是一本新穎的親子互動教育書。你自己如何定位你的文字?是否還有其他的寫作和出版計劃?
簡易:我寫的時候,不受任何條條框框的制約。讀者看完後,即使全忘了,但心有微瀾,腦有餘震,也就夠了。那說明他已經順利上岸,剛才那小船可以放掉了,或者已經登上高處,剛才那梯子可以抽掉了。至于那是什麼船,什麼梯,也許就不必再糾纏了。登高後望遠,視野、心态、品味、感悟、判斷力自會不同,他可能再也不願接受平庸的書了。
我下一本書的主題是信息,暫定書名是《這才是你的未來──人腦與電腦的信息進化與博弈》,希望能寫得更好一點。然後再寫一本關于物質和能量的書,最後構成《時空》《信息》《物質》三部曲。
注:封面題圖素材來自《外太空的莫紮特》劇照。
采寫/蕭三郎
編輯/張婷 申璐
校對/劉軍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