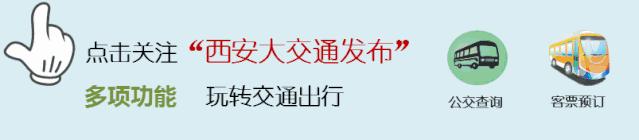我母親2017年去世,六年後也就是今年的七月份,父親結束了他無比痛苦的最後人生,追随母親去了。
父親母親都走了,小鄉村裡,我家的老房子更加顯得破舊不堪,孤零零後躲在鄉村的一角,隻有小院旁邊樹上的鳥兒叽叽喳喳的叫聲才證明這裡曾經住過人,曾經也有溫暖熱鬧的一家人。

我們兄妹四人,哥哥,我,妹妹,弟弟。哥哥大學畢業後在城市裡安了家,我和妹妹出嫁,雖說不太遠但離父母親小鄉村也有一百多裡地,等于是我弟弟在家裡守着老家。老父親下葬後的第三天,按照我們當地的風俗我們兄弟姐妹要各回各家,等到父親過五期的時候,我們再回來給老父親燒紙錢。
那天下午把父親送走回到老房子裡,我站在堂屋的窗前,看到老父親空蕩蕩的房間,空蕩蕩的床,和空蕩蕩的輪椅,又一次禁不住淚水。曾經用他一雙手養活了我們一大家子的父親,在他七十五歲的那年,在病痛的折磨下,無限痛苦的閉上了雙眼,從此撒手人寰了。他曾經心心念念的好日子,一天也沒有過;他曾經羨慕的平房到死也沒有住上,甚至在他臨終的床上的屋頂上擡頭就能看到的還有一兜塑料袋水,那是下大雨了房子漏水,家人們就用塑料袋襯在那裡,水便積在塑料袋裡了。
父親47年生人,應該是屬豬的吧,那個年代的人普遍都很苦,以農耕為主。那個時候沒有電,媽媽照樣紡花織布到深夜。不過那個時候我家條件還可以,爺爺比較能幹,就讓父親去讀書。父親很聰明,書讀的很好,聽爺爺說那個時候家裡窮,沒有紙和筆,父親就用樹枝在地上畫着寫。本來父親可以去部隊的,可是爺爺奶奶說就這一個兒子,不讓出去,讓父親在家幫他們幹活,以至于父親後來非常辛苦。
時光荏苒,爺爺奶奶相繼去逝,我們兄妹四人都已長大成家。
2014年冬天,父親一大早就騎車去建築工地幹活,一向身體很好的父親在建築工地幹活時突然感覺到頭疼,而且手還拿不住東西。那個時候“腦梗”這個名字我們還不熟悉,主要是父親母親一向節儉,以為是普通的感冒,他就騎車回家想着睡一覺就好了,第二天嚴重了才去醫院,醫生告知父親得了腦梗,因治療不及時可能會留下後遺症,那年父親才六十四歲。
我和哥哥連夜把昏迷不醒的父親轉到市裡第一人民醫院,經過治療,父親左邊還是留下了後遺症。出院後,父親回到了老家。遵醫囑,加強鍛煉,每天甩胳膊一千下,為了強化鍛煉,父親還手拿一隻小凳子甩胳膊,走多少路,父親都有自己的計劃。兩個月後,父親的胳膊能擡起來了,生活慢慢的能自理了。期間父親想着啥時候自己鍛煉的能去工地幹活掙錢就好了,還上當受騙的買了黑心人上門推薦的所謂“萬能藥”,我知道後還狠狠的把老父親說了一頓,因為我知道父親要想恢複的象正常人一樣,那簡直就是異想天開。父親一直小聲的說他也很後悔,白白扔了錢。現在想想為了區區一點錢我把生病的老父親訓了一頓,我也很後悔,但後悔有什麼用?現在寫出來不隻是為了譴責我自己,更是為了大家别向我學習,畢竟世上沒有賣後悔藥的。
時光就這樣悄無聲息的流淌着,轉眼到了2016年,這年的年尾,我那常年身體不好,犯高血壓的母親突然昏迷倒地,父親大聲呼救,最後被120車拉到了醫院。
母親在醫院裡住了20天,眼看馬上就是陽曆年了,我們把母親接回了家,從此母親就癱瘓了。我的苦命的雙親,一個癱瘓在床,一個半自理,而我們兄妹四人都要養家糊口,這可愁死人了。這個時候我那半自理的老父親說話了,他讓我們都回去,他來照顧母親。沒有辦法,我們隻好把吃的用的一切都準備好,讓他們隻顧自己吃飽就行,而且我弟媳離的近,她忙完以後也會從旁協助照顧父母的,而我們隻要有空就會回去看望雙親。每次回去母親都會問我她這種病啥時候才恢複好,啥時候能站起來走路。我對她說“醫生說了,得一年”。母親相信了,我知道我是在騙她,可她不知道就好。到了2017年的農曆4月28日這天,母親終于沒有等到能讓她站起來的那“一年”,便撒手人寰,與我們陰陽兩隔了。因為臨近端午節了,我本來打算過完端午節就去看她,她卻沒等到。聽父親說母親臨終前還在叫我的名字,說我咋這麼久沒去看她。現在想起來我真想打我自己。
母親走後過完五期,哥哥把父親接到了城裡,我也在這個城市。離的近了,我時常去看父親,他也會推着輪椅出去廣場走走,和人聊聊天,不過我知道父親大多數時候是孤獨的,因為兒女都忙。
父親在城裡住了三年,2020年五一放假,父親非要讓哥哥把他送回家,他可能感覺到自己年齡大了,不想在外面了。那個時候他還是能顧住自己的,隻是更加孤獨了,因為村裡的人都去打工了,就剩幾位老人還離的遠,我家老房子周圍的兩家人門都鎖了,一家人都出去打工了,老父親坐在門口,常常半天也看不到一個人。
今年的四月初,父親摔了一跤,他說腿發軟,站不起來,而且腿還腫的曆害,我知道他的病加重了。我弟弟連忙把父親送到醫院裡,輸水加營養,父親精神好多了,但就是吃的少,也站不起來了,隻能在床上了。這次父親犯病,都是我弟弟一個人在照顧,都沒給我和我哥打電話。他說,你們都回來也是那樣了,我一個人照顧就行了,别耽誤你們上班。我善良的弟弟,他把我們幾個人的父親一個人扛起來了。
這樣又過了兩個多月,我打電話問弟“父親這段時間咋樣”?弟說“不好,發燒了”。第二天一早我趕到家裡,父親在輸水,眼睛也看不清東西了,但他意思清楚,聽聲音知道是我。我看着父親消瘦臉龐,摸着他的額頭問“爸,你想我了嗎”? 父親說“想了”。
我說“想我咋不給我打電話”?
父親說“不會了”。
從那天開始,父親就沒有吃過一口飯,每天隻喝水。但他意識清楚。
又輸三天水,沒有起色,父親不讓輸了。但他開始煩燥起來,跟前不能離人,一離人他就叫,我便和弟弟一天24小時輪流值班,我白天他晚上,因為弟弟說怕晚上有啥突發情況我弄不了。父親睡覺很少了,睡一會他就醒。一會說頭痛,一會說牙痛,還有心裡不舒服,一會說要小便。我給他拿便壺接了半天,他也沒尿,但一直說難受。我給弟弟說了,弟弟說那是前列腺炎,他平時就有過一次,那次是他把父親弄到醫院裡醫生給插的導尿管,醫生還說要是再來晚會執腎憋壞的。這次可能是犯了。于是我弟趕緊去城裡的醫藥器械處買了導尿管,回來自己給父親插上,父親排了尿,好受了。我說弟弟,照顧父親久了連導尿管都會插了,弟說,實屬無奈。
父親依舊不吃一口飯,隻喝水,意思依舊清醒。他一會讓扶他坐起來,一會要躺下,他心裡已經沒有白天黑夜了。
就這樣過了一個星期,父親依舊是不吃飯,隻喝水,依舊是意識清醒。父親還會叫,說這裡不舒服那裡痛。我所做的隻能是喂他水,給他翻身。不過父親己經是時而清醒時而糊塗了,糊塗的時候他喊我不認識人的名字。清醒的時候他也感到很愧疚,說耽誤我們幾個上班掙錢了,人家都出去了,都怪他。
有一天父親說讓我給他洗洗頭,洗洗腳,然後他想到門口坐一會,看看我家的院子。我給他洗完後,我們幾個把他擡上輪椅推到門口,讓他往外看看,哥哥給他理了個發,父親喝了很多水。他說他夢見我媽了,還用手揪着自己的褲子說你看褲子着火了,我意識到父親離走不遠了。

父親躺到床上,還是那樣一個勁的叫,說自己不舒服。
第二天,我發現父親越來越難受,喝水越來越勤,有時張大嘴喘氣,大熱天四十度的高溫他都感覺不到熱,說話我也聽不清了。看着父親受罪,我無能為力,我有時也煩燥,甚至在七月七那天,我在心裡默默的想“爸爸你走吧,你去那邊找爺爺奶奶還有媽媽團圓去吧,你在這邊太受罪了”。我蠢透了,他是我的親爸爸,我怎能看他受罪就這樣想?這和撥他氧氣管有啥區别?
第三天,天氣依然很熱,院牆外樹上不知道什麼小鳥叫的特别厲害,我嫌吵,用小石頭投過去,停了一會還是叫個不停。這天的上午,父親已說不出話了,隻會示意他要喝水。我不停喂水給他,發現他咽水都困難了,嘴唇幹,我就用棉答醮水給他潤潤。午飯後,父親停止了呼吸。

父親走了,走完了他辛勞的一生,我從此無父無母,留下的隻有那個破敗的小院。但這小院承載了我年少時所有的美好記憶。小時候,爺爺趕集賣回來幾個糖果,我覺得那是世界上最甜的糖;過年的時候從小年開始一家人就開始忙活:母親先是把廚房打掃幹淨,接着蒸豆包馍,炸油條,包餃子,放鞭炮,我最期待的還是大年三十晚上爺爺給我們幾個發的二毛錢的壓歲錢。我把這珍貴的二毛錢壓歲錢放到媽媽給我做的新衣兜裡,用手捏了又捏,心想長大了我也要掙錢,給爺爺奶奶爸爸媽媽買好多東西。
時光的變遷讓我失去了親人,而我也由亭亭玉立的少女變成了中年大媽,這就是人世間的輪回吧。
父母走了,那個小院成了我的鄉愁!
現代著名詩人餘光中說:
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母親在這頭,我在那頭。
灬…
後來,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
我在外頭,母親在裡頭。
現在我體會到了。
如果你的雙親健在,請不要嫌棄他們太老,更不要嫌棄他們給的少。因為那一天的到來你不知道還有多久。

寫在最後:本文是自己的真實感受,原創。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