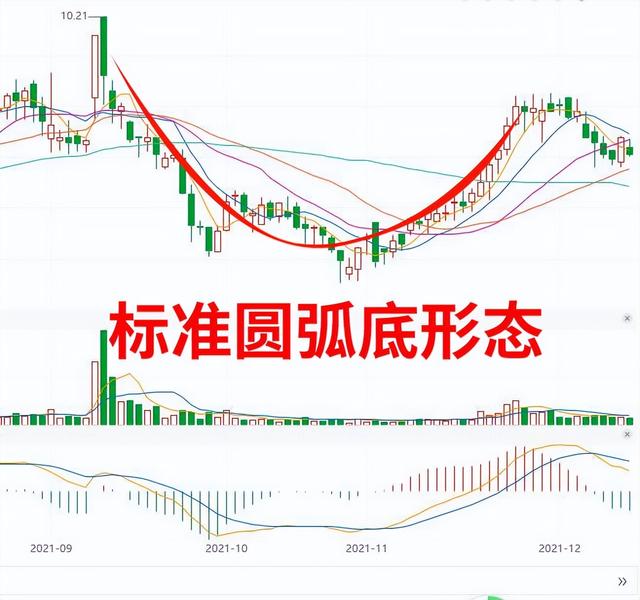四書本是五經的補充,為何後來地位反而超過五經?
“四書”之名始于宋朝,“五經”之名始于漢代。從春秋戰國至唐代,五經都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但到宋代,四書的影響力漸漸超過五經。
五經本是儒家最基本的經典,主要記載上古三代的禮樂制度。《史記》說“夫儒者以六藝(即六經)為法”,“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可見儒家是通過學習、效法三代的文化傳統而來。清代章學誠也說“六經皆史”。不過,漢武帝以前,儒家隻是諸子百家中的一派,五經并無特殊地位。直到漢武帝“獨尊儒術”,興辦太學,設置“五經博士”,把儒學經典的學習與政治挂鈎,五經才正式成為官學。要注意,漢代五經中的《禮》指《儀禮》,并非《禮記》。

圖片來自網絡
四書實際上是對五經的補充,作者分别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比五經要晚出得多。雖然《論語》和《孟子》在漢文帝時代就被列入官學,但這兩本書還不能稱為經。東漢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将《論語》列入“六藝略”,說明《論語》的地位提高了。《三國志》提到了“七經”,《論語》位列其中。唐文宗大和年間刻“十二經”,其中也有《論語》,但《孟子》的身份還是上不去。
中唐時期,為對抗佛道二教,韓愈擡出《大學》,李翺推崇《中庸》。晚唐皮日休認為《孟子》可與經學并列,應成為科舉必讀之書。五代後蜀孟昶命毋昭裔楷書《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論語》《孟子》十一經刻石,此後宋太宗又翻刻,《孟子》才稱經,并列于九經之中。此後二程表彰“四子書”。其中的兩本,《大學》《中庸》來自于《禮記》,而《禮記》一書早在唐代就立于學官,成為“九經”之一。但是,漢唐時期,《大學》《中庸》作為《禮記》中的兩篇,被視為先王禮樂方面的著作,與宋代以後被視為哲學著作是不同的。

圖片來自網絡
到了南宋,朱熹把《大學》《中庸》從《禮記》中抽出,分别注釋,于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間,與《論語》《孟子》合在一起,編成《四書章句集注》,從此四書的經學地位正式确立。
朱熹死後不久,朝廷便将他注釋的《四書章句集注》審定為官書,從此盛行起來。到元代延佑年間(1314——1320)恢複科舉考試,正式把出題範圍限制在朱子《四書章句集注》之内,明、清沿襲而衍出“八股文”考試制度,題目也多選自該書。明朝科舉考試的主要内容是:“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清朝幾乎完全一樣。表面上是考四書五經,實際上主要考四書。清朝自順治起,由皇帝頒布四書考題,而五經考題由主考官裁定。乾隆九年(1744)上谕:“從來科場取士,首重頭場四書文三篇,士子之通與不通,不出四書文之外。”原本對四書和五經的考核都在第一場考試,等到乾隆年間,五經轉為第二場考試,說明四書地位已完全在五經之上。

圖片來自網絡
為何四書的地位實現反超?究其根源,這與儒家與佛教、道教的競争有關。本來,儒學追求內聖外王之道,漢唐時代的經學側重于儒家的“外王”之道。随着佛教傳入,它的那套修心養性的學說将儒學的“內聖”之道遠遠抛在後面,加上道教(主要表現為玄學)的沖擊,作為官方思想的儒學越來越僵化,不足以同佛道二家抗衡,造成“儒門淡薄”的局面。為了應對佛道二家的挑戰,宋明理學家出入佛老,吸收佛道精緻的心性哲學,重構儒家的内聖體系。在這種情況下,以三代禮樂為基本内容的五經,顯然已經不能适應時代的需要;相比于五經,四書中有關道德修養和精神境界的内容,經過理學家的不斷發揮,成為抗衡佛道思想的有力武器。這也是四書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并最終超越五經的根本原因。從整個中國思想發展的角度看,四書地位的反超,實際是儒佛道三教競争的結果。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