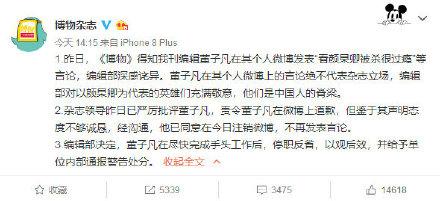莊 重
在綠樹掩映的弘一法師骨塔前,時光的力量已經滲透到旁邊巨大的山石上——每一個遊客都可以看到深深勒入石上的“悲欣交集”四個字。斜陽照在上邊,又是一年深秋了,這四個字在蕭瑟的松聲裡還會告訴我們一些什麼?每一年都有人往凹下的刻痕裡上漆,為了警醒世人。它的含意太飄渺了,一些場景被放置在過去時上,把玩之下隻能聽到遠來的風聲。前一段還有人為這四個字的涵義争論——佛門讓人争論的例子已經數不勝數,這些閃爍智慧之光的吉光片羽,讓人備感争論的徒勞。誰有能力揭示這一切,澄明這秘而不宣的内心軌迹呢,我是不能,也許你也不能。往事不曾消逝——一些紙本的記錄試圖給我們這種自信,隻是它也解脫不了時間的局囿,始終被一些片段萦繞着,成為故事。我想起來了,當時的情景也是在深秋,法師挺着病體,已知未來。他就要進入那個理想狀态的世界了。要來了紙筆,蘸滿墨,閑閑澹澹地落下。墨色在幹裂秋風裡粘稠了,不是十分滋潤。造型依舊是清癯修長,像他此時的一道影子。弟子們在旁屏息斂聲,四周死一般岑寂。法師清瘦的面容和深陷的雙目,流露出欣慰和平靜之光——所有的感受都簡化了,濃縮在這四個大字裡。當他把筆輕輕擱下時,暮色卷進了高牆。我通常把這種寂靜肅穆下的氛圍歸于莊重。這種場景讓人速長幾歲,懷揣沉重和莊嚴。
人生如果沒有經曆幾次莊重的場景,就總是懸浮無着。曲終人散,絕對是一個規律。
來到這個省會城市的初期,我住在城市邊緣的一位花農老房子裡,開始了沒有人管束的大學生活。主人往城裡跑了,老房子空曠而枯寂,如果我不自言自語,就成天沒有聲響。我忙着讀書寫字,不知道這個城市的走向,對這個城市的習俗渾然無覺。一個清晨,從銅管樂的吹奏聲中醒來,這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星期天,我伸着懶腰循聲走去,婉轉的《花兒與少年》在晨風裡飄蕩。接下來我吓了一大跳,原來是辦喪事——這是我第一次從側面見到這個城市對遠走的人的送别方式。後來,人陸續地到來,花圈慢慢地鋪排展開,長了起來。有一些人顯然是單位派來的,他們個人與死者毫無瓜葛,卻因着這個送行的任務熟悉起來。于是坐着喝茶抽煙、聊天說笑。他們盼着殡儀館的車子早些開來,結束後好忙乎自己的事兒。這樣的人多起來,氣氛就有些變。莊重的場合一旦不莊重了,對其他人來說是一種隐痛,也使場景滑稽起來,模糊了主題。在城市的年頭久了,最初的印象仍無法磨滅,在很多這樣的場景裡,參與者一臉茫然。好幾位書畫界的前輩過世了,我從未參與出殡,除了費時之外,自以為情感上産生不了和諧——屆時肯定又有人講段子,我要不要應和地微笑?古人雲:“死生亦大矣。”這是很有道理的。一個人出生了,與這個世界立了整個過程的契約,是一件莊重的大事。人不像樹,如果一個人忘了自己的年齡,恰巧又失去所有憑證,這個人的生長過程永遠是一個謎。一棵樹倒下的時候,内部昭示了它生前隐藏的秘密。人的内部沒有年輪,他的出生日就成了一種值得重視的記錄——滿月、周歲、每年的生日,儀式落滿了俗世的塵埃,卻鄭重其事地舉行着。一個人辭别這個世界,儀式的莊重是不亞于出生的。凄美的清明,春雨滋潤,空氣中布滿潮濕,無數的祭奠儀式,倘若不是應付了事,面對靈魂,内心淨化起來,一種藏之于内部的力量,撩開虛妄,落入沉實。但丁說得好啊,“我見到的幻象幾乎完全消失,從中誕生的芳香依然一點一滴落在我心中。”我想這就是一種轉換,一個人到來了,一個人遠去了,他們擦肩而過,都鄭重其事。辛亥革命後,還有不少男人背上拖這一條舊日的長辮子,沒有随滿清的消失而消失。跑得驚惶時,辮梢在脊背上舞蹈。這種飾物和具體的那個男人是一種什麼關系,對我來說真是一個難解的謎——就從這個細節說起吧,一個朝代一直停留在一個人的背上,肯定包含了他的想念和愛慕,不感到它的衰落或累贅。像辜鴻銘那樣,那條晃動的小辮子,實際上就是一種精神,他坦然而固執地堅守着一種情懷。時光讓所有的生命破綻百出,卻不能粉碎一個人對前朝的信念。後來的人擺出一幅副新時代的派頭,嘲笑這些人對往昔的眷戀,有誰深入到他們複雜的心靈内部?如果扔掉這些新潮評說,自己閉上眼睛想一想,這樣的人顯然在莊重地承諾着一種過去時的精神語言。保存傳統中不易察覺又容易消亡的細節,裡邊盛滿的秘密,肯定比那些想都沒想就順從地操起大剪子鉸掉長辮的人,更值得回味。
對于莊重的感受,是一個人給予我的。她就是我的二姨。自幼殘疾使她對生活倍加珍惜,在她有生的日子裡,她的善良、寬容和博愛讓鄰裡無不稱贊。尤其是遲暮的時光裡,我看到了一種民間精神的真實原型,感受到生命靈光在靜穆中的力量——包藏在矮小軀體裡的信心,每一天都快樂地跳動着。我認定這源于她一生不變的信仰——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早禱、晚禱,許多機會與主耶稣交通着。一種來自靈魂的言語,通過每日善的行為,無聲地彌漫開來。有時,我覺得她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裡。每一次用餐前,我見她閉目默禱,然後,徐徐用箸。她感謝上帝給予的一日三餐的美食,細嚼慢咽,莊重的神情下用心品嘗。其實,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城市居民生活的低谷,日子貧瘠粗砺,糧店憑票證供給的陳年老米。淘米時一片渾濁,入口時一股酸氣、黴味;配搭的玉米粉、洗去澱粉後如樹皮的地瓜片,令人難以下咽。她常年的胃痛加劇了,卻仍然吃得這麼香甜,如甘饴入口,點滴不曾遺漏。吃飯時不要說話——二姨如是說。這裡的道理是什麼呢?後來,我悟出來了,它不純是生理衛生意義上的,主要是心靈感應上的——安靜,有益于用心地品味造物主的賜予,心懷感恩。心真正地投入,莊重的神情就浮現了。施勒格兒是這麼斷言的:“神,我們是看不見的,然而,我們處處都能看見神一樣的東西。”一個人莊重的時候,蕪雜避退了,她看到的肯定深了下去,即便是沉默,聖潔已經穿越内心,加深了她對于遙遠天國的想念。
在我離開家鄉之前,一直讓這種莊重的神情熏染着,在遠離家鄉的日子裡,湧了出來。後來,在餐桌上,我大抵無話。對于在餐桌上逗嘴、鬥酒,甚至把氣氛煽動得熱鬧非凡,我一直難以适應。這當然也給主人難堪,不知我為何高興不起來。不妨說開,我最喜歡的還是獨自用餐,慢條斯理,從容不迫,我品嘗到了大地的芳香。布萊克說了:“從一粒細砂裡看出一個世界,一朵鮮花便是天堂……”這裡肯定潛伏着一些條件,不是任何人都那麼輕易用眼一瞥就可以到達。

一個人的筆尖,一點都沒有涉及到家鄉,一定是有隐情。在漫長的冬季裡,有時實在無聊,信筆寫下了許多文字,卻都遠離家鄉。至少可以說,我不願意把筆尖朝這個方向移動。我對家鄉的眷戀一直停留在十六歲以前,這個典雅兼有古風的小城。如果說它的韻味,是和洋溢在小城内的宗教氣息不能分開的,好像空氣,你要撩開純屬徒勞。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摩尼教,到處可見教堂或者寺院。晚間走着,可以聽到暮鼓沉沉響起,或者晚禱的鐘聲在小城上空蕩漾。至于民間私設的不知名的鬼神龛位,更是不計其數。宗教是莊重的緣起之一,敬天地、祭鬼神,懷抱虔誠之心,構成勒這個小城特有的氣息,更是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崇禮儀,尚詩書,有時候,你和一個坐着石階上乘涼的老者閑聊,他那帶着中原遺韻的地道閩南語,環環相扣地扯出一連串犄角旮旯轶事,讓人猜度這裡的每一個人都不可小看。當然,對人的熏陶不能忽略了南音。像一道潺湲溪流的南音,常常在傍晚時分,從粉牆紅瓦裡、亭榭水池邊、天井石壁浮雕上漫了出來——清澈,我想起這兩個字足以概括整個流程。尤其唱腔裡融入那一對精緻的碰鈴相擊時迸出的清脆聲響,像精神盛宴上高舉起的酒杯碰擊後發出的心靈震顫。舉止文雅起來,言談中帶着敬語。朱熹感慨,說“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對于小城人口的質量,給予了高度評價。弘一法師揮毫寫了下來。成為這個城市的一張名片。這樣的環境裡我慢慢長大,教堂給予我莊重的浸染,要遠遠早于學堂。一個人在台上布道,下邊的人聚精會神,心和目光投注到布道者斯文的動作裡。每一個禮拜天,有多少這樣的場景在小城上演,步履蹒跚的老人,牽着牙牙學語的孩童,徒步的,坐三輪車的,準時到達。應該承認,那時我聽不懂,也不敢問,隻是在不懂中端坐。走出來的時候,陽光格外燦爛,美好充滿了平和的内心。我的一個同學,愛打愛鬧無一刻停歇的男孩,一次被人追趕時,慌不擇路跑進了藏于小巷内的教堂。與鬧市僅一牆之隔,他狂跳的心被裡邊肅穆驚呆了——裡邊有幾個就是他的鄰居,成日絮絮叼叼不讓口舌休息的市井女人,正凝神傾聽,抿緊了善動的雙唇。直到唱聖詩的時候,她們才放開嗓門,大聲歌唱。許多年過去了,聯想到這種氛圍的背後,理應有自覺而獨立的信念灌注着,進來的人,懷抱靜氣;走出來時,滿懷的欣喜。
當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那場革命,徹底地颠覆這個小城的信念。
我回到這個生我并度過少年時代的小城,毫不誇張地說,已不是我希望的模樣和氣息了。
有好幾次,在香火旺盛的開元寺,我見到了“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它已經入木三分地懸挂在天王殿裡,此時,已成了對這個小城衰微風雅的一曲悠長挽歌。
還是引朱熹的話來展開,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莊重的高級形式就是敬。敬天地、敬社稷、敬鬼神、敬祖宗,都是有道理的。人不是獨立不倚的存在,連綿而下的遺傳、血緣使人與這個世界的前前後後充滿了聯系。在信仰隐退的時代,敬鬼神的多了起來。莊重的舉止,使自己的心得到妥帖的安頓。你看他們上香的動作、跪拜的雙膝、禮佛的眼神,還有蔔筮時傾聽回應的雙兒,不須有誰教會他們。這些舉止讓人看到虔誠,自己放在了一個卑微的位置裡。不過,生活中這樣的舉止畢竟太少,無任何敬畏、禁忌,輕浮、放蕩、粗野把更多時間與空間充塞了。在這個越來越娛樂化的世界裡,戲說正在迅速肢解着莊重,使人分不清是真或僞介入了我們的啟蒙教育。曆史被戲說,意味着真實的藏匿,子虛烏有的東西成了曆史主線上的重要情節。編造的效果是這麼富有視覺魅力,恩怨與情仇,離奇與刺激,像一把無形的鈎子,不消費力就把視線勾了過去。真正的史實是時間的信物,同時也是枯燥的、死闆的,甚至沒有什麼光澤和水分,晦暗幽深。書上表達得太精确了,像一面鏡子,可以照出當時的枝枝杈杈,由于真實,趣味隐遁、消解。更多不明史實的尋常百姓,自以為沒有什麼義務要理清這些陳年老帳,他們歡迎戲說,給自己庸常的生活添加一些樂趣——至于戲說背後的破壞如何修複,這個問題不免太深奧了。這和我看到小孩一口一個貪婪地吮吸果凍一樣,好吃,毫無營養。并且害了腸胃。不料,這個世界的審美觀和價值觀,坐到了陰影裡。

和懷舊的主題一樣,傷春、悲秋、閨怨、别離這些恒久的主題,也漸漸變得輕浮起來了。許多厚重的情節,時間長了,這麼大的空白使人言語起來陷入了猶豫,像一隻栖宿到邊緣的鳥,要飛到對岸不免膽怯。史冊上演時發出的黃鐘大呂之音,真的進入裡邊,讓人淚流滿面,不能自止。放下書本,夜幕降臨的時刻走到城市高處,在閃爍着豔麗的燈影裡,我看到一個城市在娛樂中漂浮無定。這個城市早年生長過許多慷慨激昂的人物,我對他們是懷有崇仰之情的,把這些英靈看成城市的骨骼。他們的曆程伴随着苦難與雄心,每一個人要被考證或闡釋,都可以帶出與之相伴的那段沉重的時光。可惜——沒有 噱頭。像他們的故居一般,此時大門禁閉黯淡無光,本該讓城市所銘刻的人,在娛樂聲色中,漸漸被遺忘了。一個時代不莊重了,戲說搞笑如潮水浸濕了我們的生活,日子肯定浮華起來。我們不知不覺地失去判斷所倚仗的可靠基礎,忠奸不分、善惡不論、是非不辨。我們割斷了與真實密切聯系的臍帶。時光如果像一盤不變質的磁帶可以倒卷就好了,讓我們看到一些凝重嚴峻的細節,包括每一個眉眼裡的憂慮。原先我以為,大學氛圍會是另一番氣象,圍牆之内,藏着怎樣純潔的憧憬?!那天,我正背過身子闆書,下邊是有一官半職又想掙個研究生學曆的小官僚們。我抄的是一段言辭跌宕的古代書論,眼前浮動出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一般的晉人行草,飛揚起來的思緒湮沒在江南深深庭院的安甯裡。也許通過這段提示,這些整日泡在八股公文裡的人,不會覺得中國古代的書法美學過于遙遠和抽象。事實是,靜谧被無端地打破了,有手機聲如蟋蟀振動鞘羽,傳遍了課堂每一個角落。手機的主人壓低聲音,似乎是對方求他擺平一件什麼事情。我沒有回過身來,脊梁傷泛起了寒意,自知臉色一定晦暗難看。在走路都慌裡慌張的快節奏南方,哪裡是安甯之所?是不是自己過分地追求唯美,以至附着了輕度的郁悶——這是我後來慢慢意識到的。環顧空空蕩蕩的教室,師道尊嚴的古老牆體在這種響聲裡剝蝕。心像一架很深的犁耙,要抽出來,讓自己輕松一些已經很難。
對世界的懷疑,往往從細節開始。
那麼,自問:你,在什麼時候顯得稍稍莊重一些呢?如果不問,也沒有人從這個層面,去注視這種細微如縷的精神現象,有時隻是瞬間,随之又漂移而去。我隻能說了,當拈起那杆長鋒羊毫,舔着硯台上豐潤的汁液,我的心靈世界被莊重充滿着。四周無聲,甚至一旁幫忙拉紙的人也被感覺化去,渾茫一片。頗有意味的是,人輕快起來,自信起來,行筆骎骎而走。由于我樂意相信,一個莊重起來的人,的确會與這片養育我們精神和肉體的廣袤自然,産生一種天籁自鳴般的感應。感應就是對不可言說的言說,我們可以感應一種無法說明的信息。并且不追究它的緣起——這些美麗的痕迹,與它邂逅純屬神示。
莊重,它所持有的莊嚴、深重的氣息,令今日的生命難以承受之重。太多的娛樂色彩,沖淡了我們生命中原有的厚實這一部分,阻止我們順利追求一些本質的東西。在初秋的樹幹上,我看到夏日遺留在上邊的三五蟬殼,風吹過來,微微作響。主人扔下它們遠去,此時恍若三五空屋。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