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旅版五年級閱讀短文?好像我們被分成了兩部分一方面存在着一個具有意識的“我”,同時充滿好奇和困惑,是一個陷在困局中的人在另一方面,還有一個“我”,這個“我”是自然——任性的肉體以及它身上并存着的美麗而令人沮喪的局限性——的一部分“我”把自己想象為一個理性的人,永遠在批評“我”的無理取鬧,因為“我”的激情使“我”陷入了麻煩,因為“我”非常容易受到痛苦且惱人的疾病的侵襲,因為“我”所擁有的身體器官會衰竭,并且,因為“我”的胃口永遠沒法被滿足——胃口就是被設計成這樣的,如果你試圖用一次最終的“暴食”來延緩它的欲求,你就會生病,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陝旅版五年級閱讀短文?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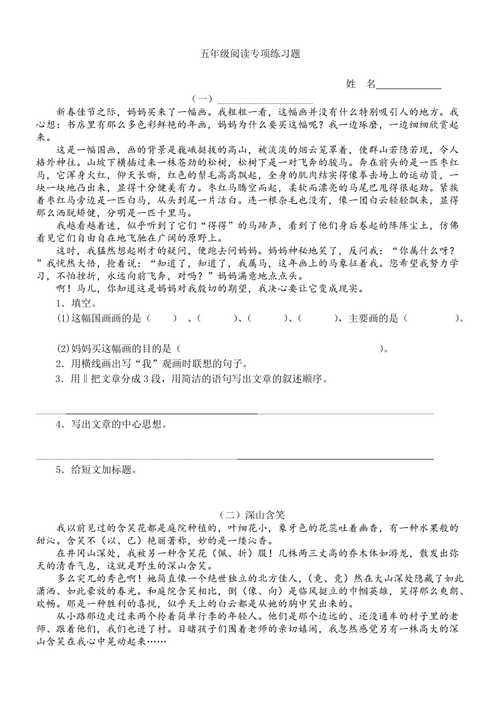
好像我們被分成了兩部分。一方面存在着一個具有意識的“我”,同時充滿好奇和困惑,是一個陷在困局中的人。在另一方面,還有一個“我”,這個“我”是自然——任性的肉體以及它身上并存着的美麗而令人沮喪的局限性——的一部分。“我”把自己想象為一個理性的人,永遠在批評“我”的無理取鬧,因為“我”的激情使“我”陷入了麻煩,因為“我”非常容易受到痛苦且惱人的疾病的侵襲,因為“我”所擁有的身體器官會衰竭,并且,因為“我”的胃口永遠沒法被滿足——胃口就是被設計成這樣的,如果你試圖用一次最終的“暴食”來延緩它的欲求,你就會生病。
或許關于“我”、關于自然和宇宙,最使人氣惱的一件事是它們永遠都不“好好待着”。
盡管這些畫面本身很美麗,但它們是在消失不見的過程中變得生動起來的。詩人拿走了它們身上那種雕塑和建築般的靜态穩定,還之以一種一旦聲音發出之後就會立即消失的音樂性。樓台、宮阙和廟宇變得充滿生氣,從它們内部過剩的生命力中分離出來。走過便是活着,停留和繼續則是死亡。
詩人們看到了這一真相:生活、變化、運動以及不安全感,隻是同一個東西的許多個名字。要說在哪兒能發現真相的話,那麼就是在這兒,真相就是美麗,因為運動和韻律都包含在所有值得人愛的事物的精髓裡。
那麼,“我”抗拒“我”的變化和周遭世界的變化,這難道不是一個奇怪的反複無常和一個不自然的自相矛盾嗎?因為變化不光隻是一種摧毀性的力量。每一種存在形式事實上都是一種運動的模式,每一個生物都像河流,如果不“流出”的話,也就絕不可能“流入”。生與死并不是兩種相反的力量;它們恰是看待同一力量的兩種方式,因為“運動”着的變化既是建設者也是破壞者。因為人體是運動、循環、呼吸和消化功能的複合體,所以它才能生存。因此,拒斥變化和試圖緊抓着生命就好像屏住呼吸一樣:如果你堅持得太久,就會害死自己。
在認為我們自己被劃分成了“我”和“我”時,我們很容易忘記,意識也正是因處于運動中才存在的。它是變動流(stream of change)中的一部分、一個産物,正如身體與整個自然界的關系那樣。如果你仔細地觀察,就會發現意識——你稱作“我”的那個東西——事實上是由持續變動中的經曆、感受、想法和感覺構成的一股流。然而因為這些經曆包含記憶,我們就有了“我”是一個固定不變的事物的印象,就好像它是一塊碑,由我們的生活在它上面書寫紀錄和檔案。
可是這塊“碑”也随着書寫的手指而移動,就像河水随着漣漪的波紋而流動一樣,以至于記憶就像一份寫在水上的檔案:它并非由不可磨滅的字符寫成,構成它的是一些動态的波浪——這些波浪是被我們稱為感受和事實的另外一些波浪所激起的。“我”和“我”之間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記憶造成的錯覺。事實上,“我”跟“我”具有同樣的性質,它是我們的“整體存在”的一部分,就如同頭是身體的一部分一樣。但如果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和“我”、頭和身體就會感到與對方“不和”。由于“我”不懂得自身也是變動流的一部分,就會試着要弄清楚世界和經驗的意義,試圖“解決問題”。
接下來我們便會面對一場意識和自然之間、對永恒的熱望和事物不斷變動的真相之間的戰争。這場戰争定然徹頭徹尾地徒勞和令人感覺挫敗,它是一個惡性重環,因為它是同一事物上的兩部分之間的沖突。它必然會越來越快地将思維和行動都引至一些哪兒也到達不了的怪圈裡。當我們無法認識到我們的生活本身正是變動,我們就把自己和自己對立起來,變得像傳說中被誤導的、試圖吃到自己尾巴的銜尾蛇。銜尾蛇是所有惡性循環的亘古不變的符号,象征着把我們的存在四分五裂、使一部分去征服另一部分的每一次嘗試。
不論我們如何掙紮,“解決問題”這一方式永遠不可能弄清楚變動有什麼意義。了解變動的含義的唯一方法是投身其中,随之移動,與之共舞。
如我們大多數人所知的那樣,宗教相當顯而易見地想要通過“解決問題”來理解生活。它試圖通過将世界與永恒不變的上帝聯系起來而賦予這個短暫且不持久的世界以意義,并将不朽的生命——在其中,個體成了擁有恒常不變的本質的神祇——視為自己要達到的目标。同樣地,宗教試圖通過把曆史和上帝——“他的話持續到永遠”——的固定律法聯系起來去理解曆史的旋流式運動。
這樣,我們借由把淺顯的道理跟固定不變的東西弄混淆,給自己制造了一個難題。我們認為理解生活的意義是不可能的,除非事件流(flow of events)能以某種方式被嵌入到一個有固定形式的框架中去。為了變得有意義,生活必須在固定的觀念和規律中易于被理解,并且相應地,這些觀念和規律必須契合于變動的景象背後那些不變且永恒的現實。但如果這就是“理解生活的意義”的意思,那就等于給我們自己設置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不斷的變動中制造恒常性。
在我們能夠找到一個更好的理解宇宙的方式以前,我們必須搞清楚“意義”和“恒常性”之間的這種混淆是怎麼産生的。
這個難題的根源在于我們已經發展出了如此快速和片面地思考的能力,以至于我們忘了思維和事件,文字和事物之間的恰當關系。有意識的思考已經走到前面去了,而且創造了它自己的世界。當它被發現與真實的世界相沖突,我們就會在“我”——有意識的思考者——和自然之間感到一種強烈的不和諧。這種片面發展并不是知識分子和“倚賴于大腦”的人所特有的,這些人隻是影響了我們整個文明的這一趨勢的極端特例。
被我們遺忘的是,思維和文字都是常俗,以及,過于認真地對待常俗是緻命的。常俗是一種社會性的便利,比如說,錢。錢消除了以物易物的不便之處。然而過分嚴肅地對待錢,将它和真正的财富弄混,就很荒唐,因為把它當作食物來吃或者當作衣服來穿都對你沒有好處。錢或多或少是靜态的,這是由于金、銀、堅韌的紙或銀行餘額都可以在很長時間内“保持原樣”。而真正的财富,比如食物,則是容易腐壞的。因此,一個社群有可能占有全世界所有的金子,但假如它的百姓不耕種作物,他們就會挨餓。
以多多少少有點類似的方式,思維、觀念和文字都是代表着真實事物的“錢币”。它們并非那些事物,而且盡管它們代表了那些事物,但在很多方面,它們和那些事物一點也不相一緻。跟錢與财富的關系一樣,思維與事物的關系也是這樣的:觀念和文字都或多或少是固定的,而真實的事物卻始終在變化。
用語言說出“我”,比指着你自己的身體要容易些,說“想吃”也比試圖表明嘴裡和胃裡的一種不明确的饑餓感要容易。說出“水”,比領着你的朋友走到井邊且做出相宜的動作更為方便。同樣方便的是,人們達成一緻,用一些相同的詞來示意相同的事物,并且将這些詞語保持不變,盡管我們用它們所示意的事物正處于不斷的變動當中。
起初,文字的力量一定顯得很神奇。确實,言語思維(verbal thinking)帶來的奇迹證實了這一印象。擺脫手勢語的麻煩之處,最初必定是一件奇妙無比的事:你可以發出一串簡短的聲音來召喚一位朋友——叫他的名字!這就無怪乎名字曾被認為是神通力量的神秘表現形式,無怪乎人們将他們的名字與靈魂密切聯系起來,甚至于利用名字來喚起某種精神力量。實際上,文字的力量是通過不止一種方式到達人的大腦的。“釋義”現在幾乎跟“理解”意味着同樣的事情。更為重要的是,文字使得人可以為他自己提供釋義——将他自身經驗的某個特定的部分标記為“我”。
這或許就是将名字看作靈魂的某種古代信仰的含義。因為釋義就是隔離,将一些形式的複合體(complex of forms)從生活流(stream of life)中分離出來,并且說:“這就是我。”當人可以命名自己并給他自身提供釋義的時候,他就感覺自己擁有了身份。因此就像文字是不會變動的一樣,相對于真實、流動的自然世界,他開始感覺到自己是獨立、靜止不變的。
一旦人開始感到自己是獨立的,他和自然之間的沖突就開始了。語言和思維都跟這個沖突相搏鬥,通過稱呼名字來召喚一個人的“魔法”被應用于整個宇宙。這種“魔法”的力量在神話和宗教中得到了命名和個性化,并被頻頻召喚。自然的進程變得易于理解,因為所有有規律的過程——比如星辰的輪轉和四季的變換——都可以跟文字相對應,并可以歸因于神祇或上帝的活動——神的永恒言辭。稍晚一些時候,科學運用了同樣的程序來研究宇宙中的規律,用更為不可思議的方式給這些規律命名、分類并使用它們。
但是由于固定化、明确化以及從其他事物中分離出來正是文字和思維的用處與性質,描述生活最重要的特點——它的變動和流動性——就變得極為困難。就像錢無法體現食物的易腐壞性和可食用性,文字和思維也沒法反映生活的朝氣與活力。行為和思維間的關系有點像一個跑動着的真人和用一系列“靜态照片”來呈現跑動過程的電影之間的區别。
每當我們想描述或考察任何移動着的物體,比如說一列火車,我們就會訴諸靜态照片這一慣例,聲稱這列火車在某時某刻處于某某位置。但這并不十分正确。你可以說一列火車“現在”位于某個特定的點,但是你說“現在”的時候花去了一些時間,在這段時間裡——不論這段時間有多短——火車仍然是運動着的。你隻能說這列開動着的火車在某一個特定的時刻位于(類似于停在這個地方)一個特定的點——假如這個時刻和這個點都無限小的話。可是無限小的點和固定的時刻從來都隻是想象中的,是數學理論中的事物而不是現實世界裡的。
對科學推演來說,把一個動作看待為一系列非常微細的迅猛動作或靜止最為方便。然而當我們将一個以這樣的慣例來描繪和測量的世界等同于我們的經驗世界時,困惑就産生了。除非一系列的靜态照片在我們的眼前迅速移動,否則它們并不能傳達出運動本質性的活力和美。釋義也好,描述也好,都遺漏了最為重要的東西。
對于推演、語言和邏輯這些目的來說,盡管上述的常規做法很有用,但當我們認為我們用的這種語言或我們賴以推理的這種邏輯真的能夠定義或解釋真實的“物質”世界,荒謬就發生了。人之挫敗一部分在于,他已經慣于期待由語言和思維來提供它們所無法提供的解釋。在這個意義上,想要讓生活變得“易于理解”即是想讓它成為生活之外的某種東西,就好像是更喜歡一部電影而非一個真正跑動着的人。而感到除非“我”能夠永恒否則生命就毫無意義,則像是不顧一切地跟一英寸墜入了愛河。
文字和度量單位并不能實現生活,它們僅僅象征了它。因此,所有由語言表述的對于宇宙的“解釋”都是循環論證的,并且沒有對最本質性的東西給出解釋和釋義。字典本身就是循環論證的,它用一些詞來給另外一些詞下定義。當字典在某些詞旁邊給出一幅圖片時,它就離生活近了一點。可是我們會注意到所有的字典圖片都跟名詞而非動詞聯系在一起。動詞“跑”的示意圖就必須得是像連環漫畫那樣的一系列靜态圖,因為文字和靜止的圖片既不能定義也不能解釋一個動作。
甚至連名詞也是約定俗成的常規。你不是通過把這個真實的、活着的“東西”跟“人”這個發音聯系在一起來定義它。當我們說“這(用手指指着)是一個人”的時候,我們指着的東西并不是“人”。要是更明确一些,我們應當說“這是‘人’這個發音所代表的”那麼,“這”是什麼?我們不知道。也就是說,我們無法用任何固有的方式來定義它,雖則在另一個意義上,它是作為我們的直接經驗而為我們所知的:它是沒有可被定義的開始和結束的一個流動的過程。僅僅是常俗在讓我們相信,我隻是被這層皮膚在空間裡所限定的這具身體,并且它也受到出生及死亡在時間上的限定。
在空間裡,我從哪兒開始,又在哪兒結束?我跟太陽和空氣的關系是我存在的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和我的心髒一樣重要。我在宇宙間廣闊的生命運動中隻不過是一個模塊或一個螺旋,那種運動在按照慣例被孤立出來的,被叫作“出生”的這件事之前無法計數的歲月裡就開始了,而且它還會在被稱為“死亡”的那件事之後久久持續。隻有文字和常俗可以把我們從完全無法加以釋義的事物——其實就是一切事物——中分離出來。
現在我們所擁有的這些都是有用的詞語,隻要我們把它們作為慣例來對待,像使用想象出來的經線和緯線那樣使用它們——經線和緯線是在地圖上标示出來的線,但事實上卻無法在地球上被找到。然而在實際生活中,我們都被文字蠱惑了。我們把文字混同于真實的世界,而且還試圖像停駐于文字世界中那樣住在真實的世界裡。後果是,當這二者并不匹配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惶恐且目瞪口呆了。越是想要住在文字的世界裡,我們便越覺得孤立、孤單,所有來自事物的歡樂和生動性也就越被僅僅交換為确定性和安全感。反過來說,越是不得不承認我們其實生活在真實的世界裡,我們就越感到對一切都無知、不确定且毫無安全感。
可是除非這兩個世界間的差異得到承認,否則,我們不可能有清明的頭腦。當科學所描述的宇宙和人類居住于其中的宇宙被搞混時,科學研究的範疇和目的便也被不幸地誤解了。科學所談論的是真實存在的宇宙的一個象征符号,這個符号的作用和錢的作用基本上一緻。它是一種便于節省時間的東西,可以被用于做出符合實際情況的計劃與安排。但是當錢和财富、現實和科學被混淆了的時候,這個符号就變成了一種負擔。
類似于此,正規的宗教教條描述的宇宙也僅僅是真實世界的一個象征符号,也同樣地是由語言的區分和依慣例所緻的區隔構造的。把“這個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區分開,就是制造一個約定俗成的分隔。想讓“這個人”永恒不朽就是想把文字變成現實,并堅稱一種常俗可以永久存在。我們渴望着事物身上那個從未存在過的永久性。科學“毀掉”了象征着世界的宗教符号,因為一旦象征符号被混同于現實,用來象征現實的不同方法便會顯得互相矛盾。
科學用來象征世界的方式比宗教的方式更适合于實用性的目的,可是這不意味着它比宗教的方式更正确。根據兔子的肉質或根據它們的毛來将它們分類,哪一種更合适?這取決于你想用這些兔子來做什麼事情。科學與宗教間的抵觸并未顯示出宗教是錯的而科學是對的,它顯示的是,所有的釋義系統都相對于各式各樣的目的,沒有一個系統能夠真正地“抓住”現實。而且由于宗教被誤用為一種抓取和占有生活之謎的方法,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揭露真相”是極其有必要的。
然而,在為了這樣或那樣的目的而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來象征宇宙的過程中,我們似乎丢掉了生活本身真實的歡樂以及意義。所有各種各樣的對宇宙的解釋都有着隐蔽的動機,它們更為關心未來,而非當下。宗教想确保一個超越死亡的未來,而科學想對死亡到來之前的生活做出擔保,并想延緩死亡。但是明天以及有關明天的計劃有可能一點意義也沒有,除非你充分地與當下的現實接觸,因為你生活在當下而且隻生活在當下。除了當下的現實,并不存在着其他的現實,因此,即使一個人可以永生,為了将來而活也意味着永遠地與生活失之交臂。
正是這個當下的現實,這個變動中的、充滿生氣的現在逃開了一切的解釋和描述。這裡有一個神秘的真實世界,文字和思維永遠都不能确切地把握住它。我們始終為了未來而活,因而與人生的這一源泉和中心漸行漸遠。結果就是,命名行為和思維行為中蘊含的所有魔力都隻不過變成了某種暫時性的“故障”。
技術的進步讓我們生活在一個忙碌的、發條般的對人類生理施暴的世界裡,它使我們專注于越來越快地追求一個未來而心無旁骛。人們發現深思熟慮的思考也無法抑制住人内心的野獸——一頭比任何野生動物都更加“兇殘”的猛獸,它被對幻象的追求激怒和惹惱了。對文辭、分類學以及機械化思維的專門精通,把人跟操縱着他身體的那些不可思議的本能力量隔離開了。此外,它還使人感到自己全然脫離了宇宙及自身的那個“我”。因此當一切哲學都消解于相對論,無法再用某種固有的方式理解宇宙,被孤立的“我”便感覺極度不安和恐慌,意識到真實的世界是對“我”的整個存在的一個直截了當的反駁。
當我們發現觀念和文字不能夠窺破終極的生活之謎,意識到真相——或上帝,如果你願意這麼稱呼它的話——無法被有限的頭腦所理解,這一窘境裡當然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唯一的新鮮之處在于,這個困境現在不再是個人化的而是社會化的;它被廣泛地感知到,而不是隻局限于少數人當中。幾乎每一種精神傳統都承認,要找到解決辦法,必得滿足這兩個條件:人必須放棄那個他感覺是“獨立的”“我”,而且必須面對這個現實——他不可能弄懂,亦即精确地解釋,終極事物。
這些傳統也承認,在這個解決辦法之上存在着“上帝的異象”,它不能形諸語言,它跟看到一個煥發着光彩的紳士坐在金色的寶座上或看到耀目光芒的一次确切的閃耀截然不同。這些傳統還指出,這種異象的出現,是恢複了我們曾擁有的東西,我們在過去是因沒有欣賞且不能欣賞它才“失去”它的。那麼這種異象就是我們對于這個無法加以解釋的事物——我們把它叫作人生、當下的現實、生活的大流或永恒的現在——所感到的清醒的意識,它是一種不含有與生活的分離感的意識。
在我為它命名的那一刻,它便不再是上帝;它是人、樹、綠色、黑色、紅色、柔軟、堅硬、長、短、原子、宇宙。一個人可以輕易地認同于任何指摘泛神論的神學家的觀點:這些文辭和常俗世界的居民、這些被感知為固定且有差異的實體的各色各樣的“東西”,不是上帝。然而假如你讓我向你證明上帝的存在,我會把太陽或一棵樹或一隻蟲子指給你看。可是如果你說:“那麼,你的意思是,上帝就是太陽、樹、蟲子以及所有其他的事物嗎?”我則不得不說,你完全沒有抓住要領。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