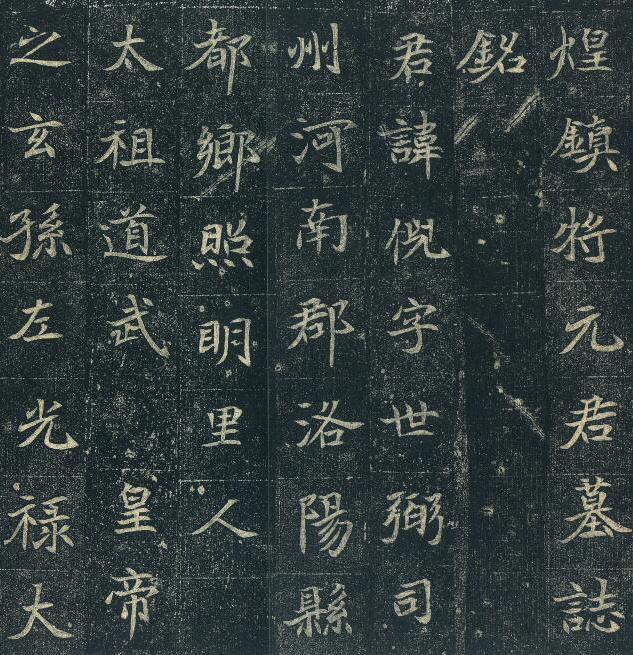在唐朝,才子文人大都不那麼孤傲,你有什麼樣的朋友圈,就會有什麼樣的人生。
而此中有兩人,有着最壯志的豪情,卻過着最悲慘的人生,亦成為了患難的至交,難得的知己。
杜甫和岑參,初識與相似,漸遠與不同,最終又憐惜于懂得,盛世沒有磨滅各自的初心,亂世沒有打斷他們的牽挂。
交往了一輩子,卻也遺憾了一輩子。
這世上,一時的朋友不難,一世的朋友不易。

因為共苦,所以相知
真正的友誼,并非由于雙方有意拉攏,是一種冥冥之中惺惺相惜,讓彼此不知不覺靠近。
杜甫岑參的相交,大概是第一次看見對方,就陡然一驚:他仿佛是這世界上的另一個我。
杜甫常驕傲地說:“詩是吾家事,吾祖詩冠古。”
這可不是吹牛,他們家族曆朝曆代人才輩出,尤其是杜甫的祖父杜審言,與陳子昂齊名,受武則天賞識,自诩:
論寫文章屈原和宋玉也隻能為他聽差,論書法王羲之也隻能望其項背。
岑參的家族更了不得,他出生于“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矣”的累世公卿之家,曾祖、伯祖、伯父都因文墨不凡而名動朝野,一門三相是真正的大唐榮耀。
站在仕途巅峰的前人仿佛已經劃定了後人的使命:繼承家族光榮的意志,背負東山再起的希望。
自小天資聰慧的杜甫和岑參背負着相同的使命,也走向了相同的道路——入仕做官,光耀門楣。

然而,杜甫和岑參都在20歲那年來到長安,四處獻書阙下,卻苦于無人舉薦。
現實告訴他們:長安城到處都是有才的人,而能與這世界規則對抗的,從來不是才華。
岑參輾轉10年才考上進士,守選三年熬到頭,才換得一個看管兵器的九品小官。
當他感歎“參年三十,未及一命”之時,比他大六歲的老杜更慘。
杜甫“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如果說第一次科舉還是年少輕怠,第二次則是遇到了百年難遇的大奸臣李林甫,其以一句“野無遺賢”,便讓全部參考的士子落選。
人就是這樣,見識過頂峰的輝煌,哪甘于腳下的平淡。他們不甘心,也不想再等待。
岑參突破着文人之弱選擇出塞,而杜甫忍耐了書生意氣選擇改變。
然而岑參飛沙走石趕赴塞外,卻依舊無人重用,第一次出塞就戛然而止在寂寂無為裡,出了個寂寞。
杜甫忍住肉麻為驸馬爺書寫“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也隻輾轉換得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
兩個出身不凡,才華不凡的人,在成家立業的坎節上,經曆着同樣的中年之難:
心中光芒萬丈,但現實無比窩囊。

相同的經曆,注定了兩人的行動交集又惺惺相惜。
當岑參回到長安,約老友們一同登樓賞景,談起人生和理想,在彼此眼中看見的是無可奈何的滄桑。
除了真心相待的老友,沒有人會在意失敗人的苦難。
正如杜甫在岑參出塞後寄詩上說,這世道不過是:“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
偌大的長安,不過多了幾個失意的文人,繁華的盛唐,卻容不下這些熱血的才子。

不能同甘,隻因三觀
都說,亂世出豪傑,時勢造英雄。
755年安祿山發動安史之亂,唐玄宗時代即将劃上句号。
此時的岑參正二度出塞,塞外的風、天山的雪、輪台的月讓岑參寫下了不少壯麗的詩篇,也重燃着他建功的熱血。
但沒想到,塞外尚未建功,卻等來了上司奉命回朝叛亂卻被賜死的噩耗,軍中不可一日無帥,他隻能匆忙班師回朝。
再回來,已是物是人非。
老友杜甫,從長安一路逃跑去追随新皇肅宗,見到肅宗時已是“麻鞋見天子,衣袖漏兩肘”,讓皇帝大為感動,被封為左拾遺,潦倒半生似乎終于等來自己遲到但并未缺席的成功。
“思君令人瘦”的杜甫,知老友歸來很是高興。
他看到岑參迷茫怅然,又深知他仍懷着建功報國,振興家業的理想,便極力向肅宗舉薦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

肅宗正欲招攬人才,讓岑參填補了右補阙的空缺。
拾遺、補阙,都是給皇帝提意見的言官,品階不高但地位還行,也算是近天子了。
杜甫很驕傲,這是他這輩子做過最大的官了。
他兢兢業業,憂國傷時,為國效力。
當兩京收複,皇位穩固,平叛形勢一片大好之時,這樣的朝局更需要文人的贊頌。
賈島寫下《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的頌詩,杜甫拉上岑參紛紛點贊、唱和。
對比賈島父子世代執掌帝王诏書,“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的殊榮,杜甫以“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點綴升平,岑參卻在這種應酬詩中寫道“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幹”。
真正見證過邊關戰亂和山河血淚,經曆過同僚被殺,奸倭當道,長安失守,皇帝出逃,岑參身在朝堂,但“劍”、“旗”、“星”、“露”仍在他心中,邊塞詩人與宮廷詩人之别,略見一斑。
他也曾如老友一般安身立命,做一個拿筆打仗的言官,畢竟“令初下,群臣進谏,門庭若市”,但“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
他内心無比空虛,對杜甫說:“聖朝無阙事,自覺谏書稀。”
不是無事可谏,而是朝堂上沒人願意再看見真實人間。
文辭才氣曾是岑參最驕傲的資本,如今隻能用來歌功頌德,他深悔:“早知逢世亂,少小謾讀書。悔不學彎弓,向東射狂胡。”
他心裡卻知道,自己回不去了,或許本不該回來。
在随老友寫完和詩的第二年,岑參就馬不停蹄地再次出京,任虢州長史。

杜甫見高适、岑參兩位老友皆離京遠去,寫下了自己不舍老友們的孤獨與凄涼:“海内知名士,雲端各異方。”
朝廷像座圍城,進去或出來,堅守或離開,每個人的選擇沒有對錯,是經曆改變了選擇,是心境選擇了各自的路。

殊途同歸,彼此釋懷
可是緣分就是這樣,有些人,分不開,有些情,斷不了。
真正的老友之間總有一種笃定和默契,縱然時光匆匆,道路不同,但人生漫漫總有緣分殊途同歸。
岑參走後不久,杜甫因卷入一起政治紛争,被肅宗嫌棄,棄之如草芥。
見識了官場黑暗又領略了人情的冷暖,他舉家如逃難般遷徙,落魄如乞丐,終于來到了成都。
在成都,有幾位故交照拂,他在浣花溪邊修建一草堂,暫得落腳之處。
此時的杜甫已經不願摻和官場的勾心鬥角,亦看淡體制内的功名利祿,隻願:
“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

兩位老友數十年未曾相見,也疏于書信聯系,可是心中一直挂念着彼此。
沒想到幾年後,命運的齒輪再次重合,岑參被貶嘉州(今四川樂山)刺史。
杜甫得知岑參即将來嘉州赴任,他渴望與老友在成都相見,寄信一首:
“不見故人十年馀,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顔色關塞遠,豈意出守江城居。”
盡管嘉州刺史是岑參這一生最大的官銜,但他早知道此時的自己上無權改政局,下無兵平割據,去了四川恐怕也隻是一個空架子。唯一的期待,大概也是與老友相逢。
沒想到天意弄人,岑參走到漢中時,蜀地發生叛亂,加之交通不便,他并沒有如期赴任,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才艱難地來到四川。
此時的四川在叛亂之後,賊寇當道,屍積江灣,野獸出沒,血流江河。
杜甫在成都的日子愈發艱難,又思鄉心切,已經乘船離開了成都,真正是“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天意弄人,岑參和杜甫都在蜀中待了許多年,卻陰差陽錯再也沒有機會見面。

四川,沒有成為他們最後相逢的地方,卻成為了他們再次靠近的契機。
他們都曾執着于奔赴功名,但現在隻見蜀地滿目瘡痍,民不聊生;他們曾立志效忠于朝廷,但朝局瞬息萬變,地方斂财傷民。
理想幻滅讓他們真正見識到一個連人命都不顧的朝代,也開始反思心中的光榮與夢想,是不是放錯了地方?
“早年迷進退,晚節悟行藏。”
岑參在四川也漸漸學着老友的樣子,将一生的執念放下。
“數公不可見,一别盡相忘” 也懷念着與老友們把酒言歡,暢聊人生的好時光。
功名不是真正的救贖,年紀的增長才知道現世安穩的重量。
769年冬,岑參在四川的一個小客棧孤獨去世,他終究成為了一個異鄉人。
第二年冬,杜甫在前往嶽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他終究成為了一個漂泊客。
兩個在晚年渴望北歸回家的人,終究未能如願以償。

這世上,隻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情誼都走不長遠。
杜甫與岑參正好相反,在人生最困難的時候,他們心靈相通,守望相助,而當人生安穩之時,卻與對方漸行漸遠。
其中自然有命運的造化弄人,更多的是,他們雖然相似但并不相同,時代變幻下每個人都有選擇自我的權利,各自忙亂的人生, 更有不願重複他人之路的執着。
但最後,共同的成長讓他們懂得,共苦讓彼此有患難的真情,不是一方的名聲、榮譽、快樂、财富附加的重量。
真正的友情,即便沒有參與對方的好時光,也會讓自己變得獨立堅強。
作者 | 北方有佳,怡然自樂小女博,觀察社會愛生活
圖片 |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