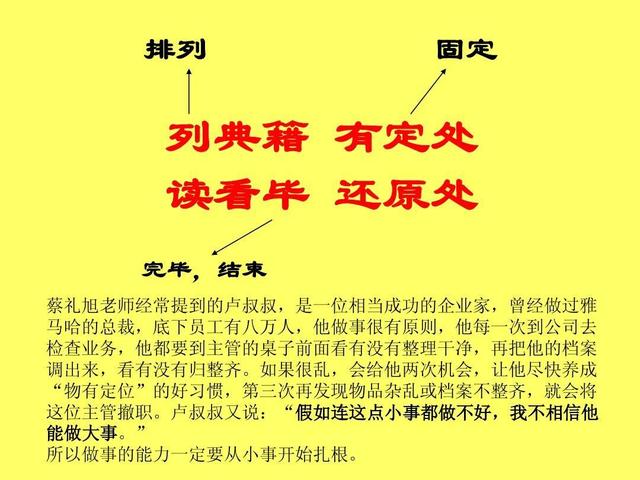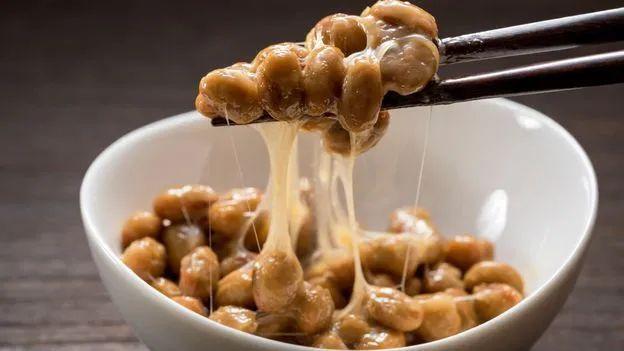滿地小樹枝?□ 楊占廠陽光熾盛的夏季,樹陰成了好地方,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滿地小樹枝?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 楊占廠
陽光熾盛的夏季,樹陰成了好地方。
不自覺地想起童年,很多美好的事情都發生在樹陰裡,午睡、讀書、打鬧、發呆。那時候的鄉村,樹是真多呀,比人多的多,它們更像是村莊的主人,在歲月的風塵裡站成永恒。
很多上了年紀的樹,都要比村莊裡最長壽的老者還要大,大幾十歲,大幾百歲。至今還清晰記得小學三年級時,我們圍着一棵三個成人合抱粗的大樹,老師說這是清朝栽下的。我們就覺得特别神奇,每次經過它都會肅然起敬,想象着這棵樹真是光榮和不易,經曆了大自然那麼多的滄海桑田,也見證了人世間那麼多的榮枯沉浮,穿越過閃電、旱澇、戰火、人禍,枝繁葉茂地站在我們面前。
每個村裡,每條道邊,每戶人家周圍,大樹随處可見。每逢夏季,樹陰滿地,偶有光影篩過密密的枝葉,映到土地上,被微風吹散成跳躍移動的金币。午後,這裡滿是納涼的人,這群人裡必然有老有少,沒有老人,少了故事,沒有小孩,少了樂趣。那些遠的近的、真的假的故事,在樹陰裡悠悠傳播,完成了多少孩童對于曆史、關于成長的最初啟蒙。
樹陰裡适合午睡,越熱的天越好。有錢人家放一把搖椅,普通人家拖一張蔑席,躺下,涼爽就四圍合來,古意也油然而生——幾百年前,幾千年前,我們的祖先也會這樣度過一個又一個炎夏。若有若無的風,和樹梢沙沙交談,驚飛鳥雀,讓瓦楞上的貓、過道裡的狗暫停打鬧,除此,萬籁俱寂,心神俱安,人們陷入不容分說的沉沉睡意裡。
等到中學時的少年,我更喜歡在樹陰裡看書,不是課本上的習題,是那些閑書,看累了就把書覆在臉上,想那些遠遠近近的心事,當時以為之後的每個夏天都會像這樣漫長而無所事事。
夏天就是這樣,如此的熱烈蓬勃,又如此的讓人心生慵懶閑逸。這一陣子,和孩子一起研讀宋人的詩詞,覺得那個朝代的人們真是愛生活會生活。宋朝大家關于夏天的文字裡,“樹陰”不厭其煩地浮現其間。
首先是秦觀,在農曆三月三十這天給春夏過渡定了調子,“芳菲歇去何須恨,夏木陰陰正可人。”春天的似錦繁花終要落去,好在夏天的綠樹濃陰緊接着就來怡人悅人。空中烈日炎炎,庭外樹陰淡淡,宋朝的大人物,跟今天的人們并無分别,都先美美地睡一覺(由此看來,中國的午睡文化真是源遠流長)。其中寫的最有感覺的,是蘇舜欽的這句,“樹陰滿地日當午,夢覺流莺時一聲。”能以鳥鳴聲為鬧鐘喚醒的睡眠,真是太幸福了。那麼睡醒了,幹什麼呢,楊萬裡說,“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提到楊萬裡,再聯想到樹陰,《小池》頓時閃進腦海,“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雖然人盡皆知,但它們的上一句是:樹陰照水愛晴柔。
晴夏,清流,樹陰,照水。多美好的意境,美到明明都是靜态的卻以一個“愛”字散發出了蓬勃的生命動力。
王安石也寫過樹陰,但是官居高位卻又變法遇阻的他,總是顯得心事重重。“草色浮雲漠漠,樹陰落日潭潭”——郁郁不得志的神态溢于言表。同樣是在遊玩中看到樹陰,南宋的曾幾就歡快得多,江南五月,乘船,遊溪,登山,飲樂,移步換景,興盡而歸,“綠陰不減來時路,添得黃鹂四五聲。”
這樣的句子,在夏天讀出來,不僅口舌生津,打心底也能沁出爽爽的涼意來。所以,快回到童年,不,回到古代涼快一下吧,無須成本,隻要:一片樹陰,一顆閑心。
(作者單位:江蘇省連雲港市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檢察院)
來源: 法治日報——法制網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