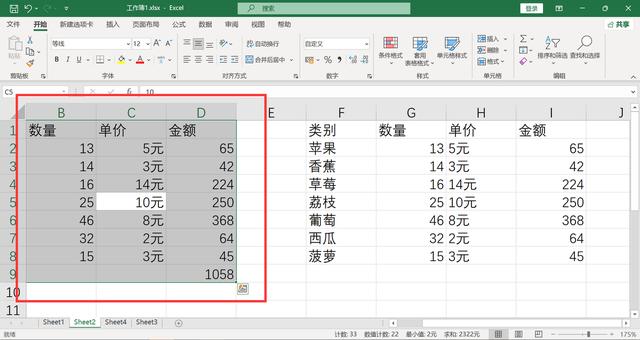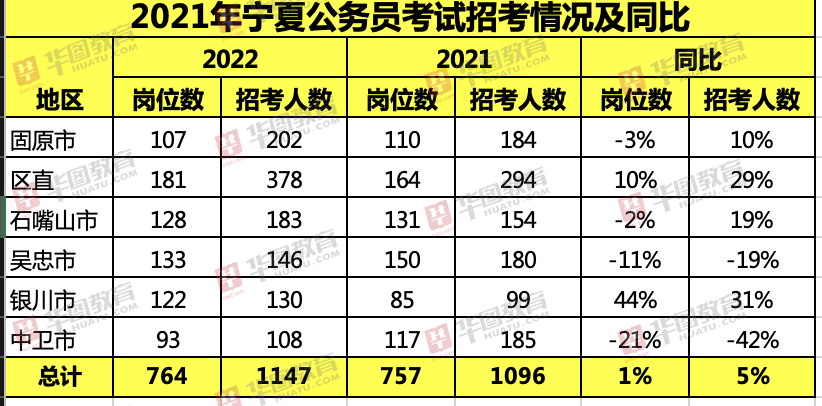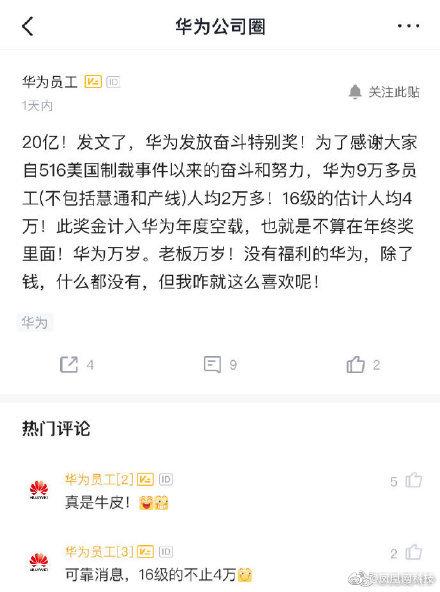農村農民工作記憶?第十節、“機會”之一“小劉,電話通知你今天上午不要遠離,上面來人”,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農村農民工作記憶?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第十節、“機會”之一
“小劉,電話通知你今天上午不要遠離,上面來人。”
老站長講。
“是局裡來人嗎?”
“沒說是哪裡的。”
“是局裡電話嗎?”
“不像。”
“是哪裡的電話啊?”
“好像是區裡,沒有聽清楚。”
這個老站長,接聽電話不問是什麼人打來,隻是傳達内容。
今天是背集,如上午不下鄉,這樣一天就沒有事幹。恰好可以把自行車保養擦一擦,前後輪卸掉,清洗清洗,将缸瓦、鋼珠子拿出來清洗,加一點新黃油進去,這樣,一個上午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手拿鉄扳手,把車輪子卸掉,把腳蹬圓盤、自行車前後輪的軸承、缸瓦打開,摳出裡面的鋼珠子,兩手沾滿黑乎乎的黃油,這時,看見一行三人來到水利站院裡。
“劉站長在家嗎?”
領頭的是區委組織委員,周組委。
這周組委輕易是不上門的。他平時待人和顔悅色,說話輕聲細語,好像怕吓住誰的魂似的。
“這就是劉戡,劉站長。八一年安徽水利電力學校畢業,八三年元月來我區工作,表現、反映都不錯。”
周組委向另外兩個拎着“熊貓牌”塑料小提包的兩個人介紹。
“我們是縣委組織部的,今天是代表組織來找你談話。”
我一聽他們是縣委組織部的,立即把我吓了一跳。心中突突怦怦跳個不停,心情緊張起來。
我想,我沒有犯什麼事啊?是不是綠洲的地頭蛇告我什麼了?不應該啊?
“到屋裡坐吧?”老站長端着自己喝的一杯白開水走上來。
我們來到老站長屋内。
“我們是縣委組織部的,今天是代表組織來找你談話。”
那個戴藍色粘帽子,個頭敦實的領頭又重複剛才說的那句話。
這時,我的心情已經平靜了下來。我想應該沒有什麼了不起,談就談吧,有什麼就說什麼吧。
“你是楊橋區的,七裡公社的,現在是七裡鄉的?”
顯然,這個人一時也沒有适應下來,竟将現在的七裡鄉還稱為原來的七裡公社。
“是的。”
“那我們是老鄉。你父親是不是原來七裡公社學校的劉校長、劉主任?”
“可能是的,幾年前我父親也在那裡教過書。”
“他現在身體好吧,現在到哪裡教書去了?”
“我父親最近幾年老是換地方,從七裡調到董莊,又從董莊調動到甯樓,又從甯樓調動到現在的八十裡店中學教初中畢業班。”
“那好,我們原來在七裡一起教書,我是民辦教師,後來招幹到區裡,又到縣委組織部。”
聽這人的口氣,這個老鄉應是我父親原來的同事,這次代表組織部來找我談話應該不是什麼壞事,我心裡坦然了許多。
我父親,一直和他的頂頭上司關系處理不好,一直擔任小學教導主任,教小學語文。人家是讓他在工作上拉套的,給領導出成績的。但他總是提出不同意見,總是說人家瞎指揮,總是說人家違背教學規律,總是說人家是草包,說人家是“不讀書、不看報、什麼學問也沒有”的大草包。是背着手,低着頭,整天想歪點子“算計”教師的高手。說人家隻會拍馬溜須拉關系“整人”的小人。所以他總是吃力不讨好,在領導面前一輩子沒有混好。
來到家鄉,大公社(現在是區)也是和那個公社文教辦幹事關系處理不好。表面上說,還是有老親戚的關系,但是,面和心不和。
所以,他的工作三天兩頭被調動。越調,離家鄉越遠。
越遠,那個教育幹事對他的影響也越大,讓他不得安甯。
可以得到安慰的是,我父親總是和地方群衆、學生家長關系搞得好,學生對他好。
所以,那個區教育幹事拿他沒有辦法,最後也隻能任他去吧。
隻是到最後國家實行教師評職稱的時候沒有他的份。
說是“分配名額”,倒不如說“買賣名額”更貼切。 說是名額有限,讓父親不要和年輕人争名額,那職稱名額都是那教育幹事(後來稱為教辦室主任)手中的砝碼金塊子,我父親哪能會為哪“五鬥米”折腰!
父親為了和年輕教師處好工作關系,也不能和幾個年輕人相争那稀缺的中級職稱名額,也不中那個“挑撥離間”計。
當職稱與工資挂鈎時,吃大虧的當然是我可憐的父親。
當他手拎着縣教育局發的三十年教齡紀念的“熊貓”牌黑色塑料包時,他仍然是一個小教初級職稱的教師,工齡上去了,工資沒有上去。一個參加工作沒幾年,“評”上中級職稱的青年教師工資很快就超過他。
我勸過父親:“你和人家說點好話又累不住人,說點好聽的話又不費本。”
父親講:“說那些好聽奉承人的話,是假話,是違心的話,我說不好,說了我心中難受。”
“那些不好聽的話不說不行嗎?”
“都是真話,反應實際問題,不說,更難受。”
目睹父輩的遭遇,我為父親鳴不平。
揚言:“我一輩子也不當教師,并教育後代也不能當教師。”
但是娶老婆還是要娶教師的,還是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而我的父親則是很樂觀的,他很推崇武訓。講武訓是個教育家,他讨飯籌資辦學,有教無類,平民教育。《武訓傳》電影拍得很好,很可惜,電影公開放映後就受批判了。他計劃退休後辦一所私立學校,從小學到中學,可以辦到大學哈。
他那躊躇滿志的心情溢于言表。
父親的工作得到七裡鄉政府的認同,在父親從教三十六周年的時候,他在七裡鄉政府入了黨。
父親将近六十歲的時候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産黨員,為“忠誠黨的教育事業”而繼續奮鬥。在他年輕的時期就積極入黨,申請書年年寫了一大摞,總是在外調材料中被家庭出身中農成份,其實是下中農,及當過三天僞甲長的爺爺,交不出“銀子”,被保長打後撂挑子。為此而拉下,為此父親想不通,害得一度患上癫痫病。
“是這樣,你們區推薦你參加本屆鄉政府換屆選舉,你是預備鄉長候選人。”
“那不行,我不幹!我水利局的事幹得好好的,為什麼要到鄉政府當鄉長?”
“現在基層幹部要年輕化、知識化、革命化、專業化,組織上要從基層選派一批一線優秀的‘四化’幹部進行重點培養,你就是其中之一。”
這話說的是好聽,但是我的生活、工作剛剛穩定,就要換環境,我一時适應不了。
況且,我現在管理的是全區的水利工作,比那一個小鄉的工作好,工作單純。
我是這樣想的,沒有說出口。
“我的那個同學黎文煥,局裡安排他到區裡當專職水利副區長兼職水利站的站長,他就不幹,他不想離開水利局到行政上去。”
“實際上,小鄉的鄉長和副區長都是一個級别的,都是副科級,但是鄉長是實職,副區長是虛職,鄉長需要人大選出、任命、走程序,發展前途大一些。副區長就是副區長,是直接任命的。是協助區長工作的。”
“我回去和我父親商議一下再答複吧?”
“好的,你今天就回去和劉老師商議商議,明天上午到區裡直接找周組委,我們明天下午考察結束彙總。”
“當什麼‘鄉長’!咱村西頭的劉老保不就是‘鄉保長’嗎?那時他還挎有盒子槍呢,你爺爺頭上的疤痕就是他用槍把子砸的。”
我父親恰好在家。
此時,我父親已在楊橋八十裡店中學教書,隔三差五回來背馍,就像我在楊橋中學讀書回家背馍一樣。
不一樣的是父親是教書的。
“那當還是不當?明天上午就要回話的。”
“不當!”
父親斬釘截鐵地說。
“你想想,你當那個鄉長有什麼用?每天騎個自行車下鄉處理事情,費神費力,那麼辛苦?搞不好群衆罵,上級罵!咱們家老墳裡可沒有挨罵的地方。”
“你好好搞你的技術,修橋鋪路,積德行善,是老百姓歡迎的事業。以後還可以給人建房子,有吃有喝,又受人尊重,多好啊!”
“不管是哪一朝,那一代,教書、看病、修橋鋪路都是需要的,都不會被打倒的。”
“技術是越老越值錢,特别是醫生越老越值錢,不然我就讓你學醫生了,怕你沒有那個耐心幹不了。”
“你們現在多好!你搞技術,李曉白教書,多好!我已經滿足了,安穩過日子吧,不要折騰了!”
“回來啦?”
我爺爺拄一把小鐵鍁從外面蹒跚的走回來。
我爺爺的這把小鐵鍁是我在冷江水利站時給他買的,可以當拐棍,可以鏟糞,可以鏟土,還可以趕豬上糞堆,是一個多用途的工具兼勞保用品。
“不年,不節,半晚上回來幹啥哩?李曉白沒有回來?”
爺爺問。
爺爺很是關心他這個孫媳婦的。
我從包内拿出一條蚌埠卷煙廠生産的“團結”牌香煙給爺爺,告訴他自己吸,不要讓人,包括我的父親。
爺爺講:“讓誰吸?你給我買的,都是我自己吸。”
爺爺打開一包,從中抽出一支給父親,父親愣瞪一下,翻眼看我一眼,然後雙手小心的接下了爺爺的恩賜,掏出打火機先給爺爺點上。
那是因為我父親的煙瘾太大了,他一天要吸煙兩包同樣是蚌埠卷煙廠生産的“大鐵橋”牌香煙。但兩盒“大鐵橋”,不值一盒大“團結”的價錢。
此時,我已經開始勸父親戒煙,讓他把吸煙的量減下來,把焦黃的牙齒修正過來。也可以把煙的質量提上去,把數量降下來。比如大鐵橋的兩盒,換成團結的一盒。
此時,父親的牙齒已經開始掉了,門前已經是豁牙了,有同事已經開始叫他“老豁牙”。
我又安排父親把吸煙的錢省下來,變成鑲牙的錢。同時,又從口袋裡掏出僅有的五元錢給父親做支持鑲牙的補助經費。
父親連看也不看,讓我母親把錢收起來。
此時,我感覺我口袋裡的錢太少了,要是有五十塊錢就好多了。
此時,父親的工資一個月也就是五十多元一點,我四十多元一點。
此時,幾個弟弟妹妹跟随父親上學,我們的大家庭還是很缺錢的。
“你回來幹啥,不好好上班?”
爺爺繼續問。
父親把我剛才的情況向爺爺彙報了一遍。
“不好,不要幹,幹那弄啥?”
“我已經知足了,你回來給我買煙、買酒,我已經知足了。”
這一次沒有給爺爺買酒。
爺爺知足的吸着我給他買得紙煙,小心翼翼的、慢慢的、吐着煙霧,他想讓那團結牌香煙的餘香味在嘴裡盡量的多停留一會兒。
爺爺将那剩下的團結牌香煙,放在他睡覺的蘆葦杆床頭前,并用他的一件衣服壓好。
這張小實木床,緊靠我家堂屋當門東山牆邊,原來床櫈上面鋪墊的是高粱節,現在又加上蘆葦杆,是我和二弟從小和他一起睡覺的床,現在二弟長大了,離開了那張床,開始和我以前一樣,頂一張蘆葦蓆,夾一個小棉被,與村裡無房睡覺的同夥一起在村裡打遊擊。
爺爺将他的黃銅水煙袋、黃火紙媒子、烏黒色的打火石和吸水煙袋點火用的草木灰焙制的麻稭杆放在了床頭下的另一邊。
此時,大妹妹從田間幹活回來,滿臉的汗水,曬得通紅通紅的小臉蛋,一頭來不得整理的亂發,但看上去還是很有青春活力,很是精神,那十多畝的承包地沒有把她累跨。
大妹妹辍學了。
我的手在口袋裡亂翻,想從口袋裡翻出鈔票來,哪怕是一張一元的也好,五角、一角的都行,但是連小硬币也沒有。
“俺哥,你幹啥,你想給我錢嗎?你要是有錢就給咱大鑲呀吧,你看他的呀已經不能吃東西了。”
我手停下,不摸口袋了,心中更不是滋味。
“下次我回來給你買搽臉的化妝品,這次就不講了。”
天快黑了,我推出自行車準備回綠洲。
這裡距離綠洲有六十華裡。
“明天再回就耽誤事麼?你現在回去到綠洲都半夜了啊?”母親講。
“我今晚先到冷江,在冷江水利站住一晚,明天一早就到綠洲了。”
“那給你先做一點飯,爐一個馍吃後再走。”
母親堅持說。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