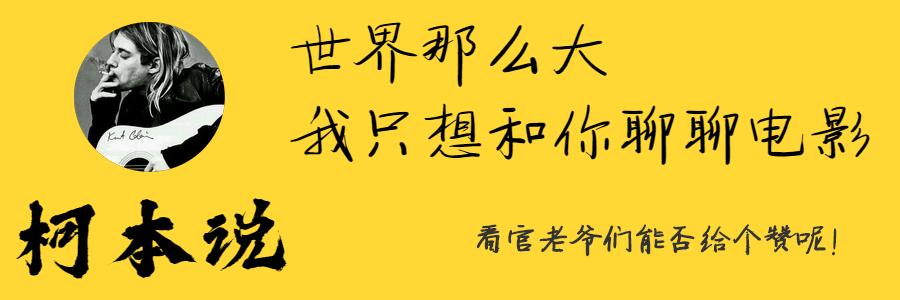在中國曆史上,巫師并非隻指代同一個群體,這個稱謂包含了各種不同功能的非專業宗教人士,一般而言,這些人可以使用超自然的法術或儀式來治療被鬼神憑依的病人,老百姓稱他們為“巫”或“觋”。在有些情況下,那些被冠以“左道”或“妖僧”稱謂的宗教異端人員所做之事也和“巫”高度接近。宋代時,這些巫師曾廣泛存在于全國的鄉村和邊緣地帶,帶有十分強烈的荒蠻、原始印記,其中,南方地區的“職業化”巫師尤其神秘、複雜。

宋代 大傩圖
“巫”作為一種職業
在宋代著名的志怪筆記《夷堅志》中,洪邁向我們展示了一幅南方地方信仰的大緻藍圖:
大江之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異,多依岩石樹木為叢祠,村村有之。二浙江東曰五通,江西閩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獨腳五通,名雖不同,其實則一。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南方風俗的多樣化特征以及跨地區地方神信仰的存在。雖然地方神的類型多種多樣,很難找到一種固定的模式,然而主持各種祭祀儀式的巫師無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根據《周禮》的分類,中國傳統的鬼神被分成“天神”、“地袛”、“人鬼”、“物”(物怪、物魅、精怪)四大類。在宋代以前,曆代政府的祭祀對象往往隻限于前三大類,但是在兩宋時期,不少巫師的祭祀對象變成了物魅、精怪。加上兩宋瘟疫頻頻爆發,無論是道教還是巫師所代表的“民間宗教”都相當尊崇“瘟神”。宋代的巫者還會祭祀一些來曆不明或是事迹無法考證的地方神。
宋代巫師信仰最受矚目的儀式是迎神賽會。信衆用儀仗鼓樂和雜戲迎神出廟,周遊街巷,以求消災賜福。基本上,這和佛道二教利用社日或神明誕辰所舉行的宗教活動,在儀式的功能和結構上并無太大不同。
這些“新風”的出現,也讓宋代巫師往往收入不菲,如《嶺外代答》第十卷記載:
裡巷大罐,結竹粘紙,為轎馬、旗幟、器械,祭之于郊,家出一雞。既祭,人懼而散,巫獨攜數百雞以歸,因歲祠之。巫定例雲,與祭者不得肺,故巫歲有大獲,在欽為尤甚。
在祭祀結束後,祭壇上的供物一部分會歸為巫師所有,或為衆巫師瓜分,或将之分給與祭者,但在上面的材料中,巫師事先規定與祭者不得分享祭品,因此獨得了一筆相當可觀的财富。鑒于主持祭儀、溝通神靈是巫師的日常工作,這些供物也就構成了巫師主要和相對穩定的收入來源。
大多數巫師遊離于“士農工商”的傳統社會結構之外,他們不需從政、務農、做工或是長途奔波,隻需頻繁主持祭儀、為人攘災求福,即能如《夷堅志》所載的鄧城巫一般“藉此自給,無饑乏之慮”。這樣的生存方式在農耕社會無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吸引了很多中下層民衆投入到民間巫術活動中去。
此外,這一時期巫師與佛教信仰已經發生了一些交集,在一些志怪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會用佛教咒語降妖除魔的巫師,比如《夷堅志》所載:福州有巫,能持穢迹咒行法,為人治祟甚驗,俗稱大悲巫。這是巫師主動吸收佛教持咒驅魔法術的結果,也是民間宗教試圖借助正統佛教信仰将自己合法化的努力。而這種儀式雜合情況的出現,很可能是宋代巫師社會對于政府壓迫的直接反應。宋代朝廷頒布的禁巫诏令之多,範圍之廣,時間之久,都遠遠超過任何一朝。但是也正因為宋代政府屢頒禁巫的法令,我們似乎可以側面解讀為當時“巫風炙烈”的明證。

南宋 李嵩 骷髅幻戲圖
男女巫師的職能分工
男女有别,男女巫師的職能也有着很大差異。
在宋代許多志怪小說中,女巫作為召魂者和驅魔者的角色反複出現。在《茅亭客話》中,一個名叫孫知微的處士與一位據說是當時的知名女巫展開了一段相當奇妙的對話:
女巫曰:“鬼有數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而自與人交言。若是薄相者,氣劣神悴,假某傳言,皆在乎一時之所遇,非某能知之也。今與求一鬼,請處士親問之。”
知微曰:“鬼何所求?”
女巫曰:“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能辨之。”
知微曰:“嘗聞人死為冥吏追捕,案籍罪福,有生為天者,有生為人者,有生為畜者,有受罪苦經劫者。今聞世間人鬼各半,得非謬乎?”
女巫曰:“不然。冥途與人世無異,苟或平生不為不道事,行無過矩,有桎梏及身者乎?”今見有王三郎在冥中,足知鬼神事,處士有疑,請自問之。“
……
知微曰:“今冥中所重者罪在是何等?”
應者曰:“殺生與負心爾。所景奉者,浮圖教也。”
這裡,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女巫的兩種職能:第一,女巫可以通過法術召喚鬼神,并且可以被鬼神憑依;第二,女巫被認為可以預測人的命運。在上述對話中,女巫告訴孫知微她并不了解鬼神的實際情況,鬼神隻是通過她的聲音來與生人溝通,所以,女巫通常被認為是無意識的。
作為靈媒似乎是女巫主要的工作内容,她們可以通過靈魂旅行來與異世界的鬼神、祖先以及其他超自然力量進行溝通,也能被來自冥界的死者憑依從而讓死者與其生人親屬溝通。在《夷堅志》的一條志怪故事中,官府甚至聘請了一位女巫來召喚受害人的鬼魂,查證一樁疑難案件的真兇:
邑有女巫,能通鬼神事。遣詢之,方及門,巫舉止言語如葉平生,大恸曰:“為我謝二尉,我以宿業不幸死,今已得兇人,更數日就擒,無所憾,獨念母老且貧,吾囊中所貯,可及百千,望為火吾骸,收遺骨及餘赀與母,則存沒受賜矣。”尉悉如所戒,後五日,果得盜。
如前所述,靈媒是女巫的專屬,而主持驅魔儀式似乎被認為是男巫的工作職能。宋代的巫師和道教的法師、佛教的僧侶一樣,也是頗具威力的驅魔者,當家屬邀請巫師來治療他們被鬼神憑依的親人時,巫師需要召喚超自然的其他鬼神來憑依他本人的身體,以獲得屬于這些鬼神的威力。在這種情況下,男巫并不僅僅是鬼神的載體,更具備控制和役使鬼神的能力,他們占據着主導權。從一個生動的案例,我們能直觀地看到男巫所具有的強大法力:
永嘉薛季宣,字士隆,左司郎中徽言之子也。隆興二年秋,比鄰沈氏母病,宣遣子沄與何氏二甥問之。其家方命巫沈安之治鬼,沄與二甥皆見神将,著戎服,長數寸,見于茶托上,飲食言語,與人不殊。得沈氏亡妾,挾與偕去,追沈母之魂,頃刻而至。形如生,身化為流光,入母頂,疾為稍間。沄歸,誇語薛族,神其事。
比起男巫的這種強力功能,許多情況下,女巫經常隻是作為一種超自然的媒介,她們的力量不足以“使鬼神”,而僅僅隻是作為載體“通鬼神”。很明顯,女巫在運用她們的超自然力量時被放在了一個被動的位置。
唐宋時代發生的社會大變革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女巫不被認為和男巫具有同樣的力量。伴随着文人地位的提高,優雅的士大夫階層首先形成并引領了以嬌弱為主導的審美風尚。腰細驚風、搖搖欲倒的女性形象深深滿足了文人對自己男性氣概的想象,也直接推動了纏足之風在整個社會的興起。因此巫師世界也受到了這種社會整體性變革的影響。而根據楊劍利的研究,“巫”與“觋”的分化帶來了氏族由母系向父系制的轉型,随之确立了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級。這種原始的分化構成了宋代巫師分工進一步細化的大前提。

南宋 金處士 地獄十王圖
“巫”與政府的互動
如前文所述,宋朝的巫師需求大、收入高、能力強,似乎是一個很有前途的職業。然而在政府看來,巫師們所主持的民間宗教活動“皆祀典之所不載”,官員們将其視為是需要根除的“淫祀”。宋朝的巫師們其實并不好過。
《名公書判清明集》記載,當時非法的地方神崇拜已然成為了審判巫師的罪名:
黃六師者,乃敢執迷不悟,首犯約束。觀其所犯,皆祀典之所不載,有所謂通天三娘,有所謂孟公使者,有所謂黃三郎,有所謂太白公,名稱怪誕,無非麗魅魍魉之物。且從輕杖一百,編管鄰州。其烏龜大王廟,帖縣日下拆毀,所追到木鬼戲面等,并當廳劈碎,市曹焚燒。
上古中國建立了所謂“絕地天通”的宗教傳統。這種信仰的基本特征是将人與神加以區隔,雙方互為禁忌,隻在自己的領域内活動,即《書·呂刑》所說的“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官方認為隻有壟斷祭祀的權力,才能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所以一直對各種地方神信仰加以限制。
但是,作為國家行為的大型祭祀難以滿足地方民衆治病祈福、祭拜祖先的需求,民衆希望能夠直接與神靈溝通,因此民間信仰得以大量湧現。然而民間宗教并不像儒釋道三教那樣直接以“神道設教”的方式與封建政權共謀,而隻能暗中流傳于民間,“執左道以亂政”、“假于鬼神、時日、蔔筮以疑衆”(廖剛《乞禁妖教劄子》),長期以來,民間信仰與正統教化處于有所區隔又相互滲透的互動關系中。民間信仰對公共秩序保持着潛在的威脅,其極端者甚至會如後來的摩尼教、白蓮教那樣,以反對當前政權的形式浮現出來,為起義提供合法性基礎。這正是政府嚴格限制“淫祀”的原因之所在。
在這樣的社會語境之下,宋代巫師處在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們必須艱難地在獲得承認與違法犯禁的夾縫中生存,小心翼翼地遊走在律令的邊界周圍;而另一方面,兩宋疆域大部處于南方,因為瘟疫的橫行、醫療衛生條件的落後與當地民風的趨向,如學者所言,民衆“笃信巫鬼,病不求醫”的地步:“廣南風土不佳,人多死于瘴疠,其俗又好巫鬼,疾病不進藥餌,惟與巫祝從事,至死而後已。方書、藥材未始見也。”(《獨醒雜志》)他們的活動在民間又具有深厚的心理基礎。
因此我們看到,以摩尼教“吃菜事魔”之事為例,在紹興四年出現了《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所載“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的局面,巫師作為“淫祀”的操辦者,也是民間信仰的承載與傳播者,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間宗教與政府的糾葛構成了宋代巫師基本的生存環境。

宋代 李唐 村醫圖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