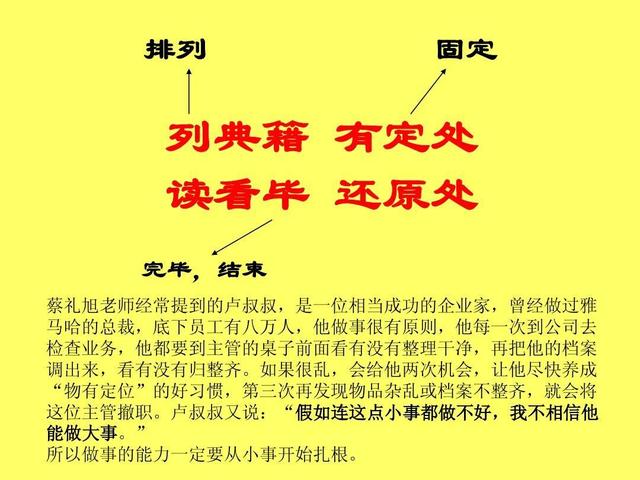離騷屈原的形象分析?作者:李菲 韓偉屈原像一位仗劍浪迹江湖的悲情俠客,用自己的激情和生命書寫傳世《離騷》,成就了《詩經》之後第二座高峰;蘇轼則是一位不食人間煙火的大羅神仙,憑借罕有的曠世之才,創造了另一座文學高峰,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離騷屈原的形象分析?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作者:李菲 韓偉
屈原像一位仗劍浪迹江湖的悲情俠客,用自己的激情和生命書寫傳世《離騷》,成就了《詩經》之後第二座高峰;蘇轼則是一位不食人間煙火的大羅神仙,憑借罕有的曠世之才,創造了另一座文學高峰。
蘇轼與屈原生活的年代雖相隔千年,但二人有着諸多相似的境遇。他們抱有經世之才,懷揣治國安民的崇高理想;他們才華橫溢,情思卓絕;他們品性高潔,耿介不阿;他們同樣曾在朝為官、身居高位,卻遭小人讒言離間而被流放被貶谪,身心俱受摧折。從文學創作來看,他們都具有強大的創新力和鮮明的主體自覺性,敢于彰顯自我。《離騷》的出現,标志着文人創作的真正覺醒,使文學真正邁入了“個體自覺”的時代。屈原之後,文學主體性精神并沒有得到進一步高揚,無論是儒家思想的内斂中庸品格,還是道家思想的超越性,都在一定程度上掩抑了個體精神的鋒芒。而蘇轼的出現,特别是他的詞創作,一改以往小詞“代言體”的審美追求,高舉自我的個性大旗,鮮明的“自我形象”得到了彰顯,而這可以說是對屈原藝術精神的繼承和發展。蘇轼在詩文作品中不止一次表達了對屈原的景仰和追慕之情,寫過《屈原塔》《屈原廟賦》。朱熹在《楚辭集注》中評價《屈原廟賦》:“是為有發于原之心,而其詞氣亦若有冥會者。”精準地指出了屈、蘇二人心靈的契合以及藝術精神上的承續和呼應。
屈原的《離騷》與蘇轼的詞,都展現出了鮮明的“自我形象”,這種“自我形象”的塑造無疑帶有生活的真實印記,但并非是生活的簡單實錄,而是融入了詩人的人生理想與追求,是其人格精神與藝術精神的外化。兩人作品中的“自我形象”有諸多相通共鳴之處,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性格品性的陶塑,二者又存在諸多差異。
屈原作為楚國貴族,一心想振興楚國,《史記》本傳記載:“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号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無奈的是,懷王并非知人善任之君,後來聽信一些奸佞之臣的讒言,棄屈原而不用。到了頃襄王,則幹脆把屈原放逐到江南。屈原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因此,政治上的失意對他來說,就不僅僅是地位與名利的喪失,而是整個人生理想、人生信念的崩塌,這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心靈創傷,從而氤氲出一種無可把捉的孤苦悲愁之感,彌漫在《離騷》整個作品中。“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對光陰流逝的感慨,實則是人生理想破滅後的喟歎;“長太息以掩涕兮”“忳郁邑餘侘傺兮”“曾歔欷餘郁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沾餘襟之浪浪”,則是聲淚俱下凄凄慘慘的哀鳴。
蘇轼因詩獲罪,被貶黃州之後便不在詩歌中放縱自我,這在他與朋友的往來書信中多有提及。而在當時多“绮羅香澤之态”與“閨門淫媟之語”的小詞,恰好成了他寄寓情感、抒發自我的不二選擇。蘇詞中也常常彌漫着失意的傷感、無助的寂寥,比如《蔔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缥缈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對這首詞的主旨說法不一,有說為王姓女子而作,有說為溫都監女作,總體來看,詩中應有政治寄托,隻是這種孤寂之情表達得更為含蓄蘊藉、空靈飛動,不似《離騷》那般噴薄而出。蘇詞中對時光流逝、人生無常也頗多感慨,比如“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西江月·黃州中秋》),“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滿庭芳》),“笑勞生一夢,三見重九,又還重九”(《醉蓬萊》),等等。這些感慨蘊含着悲涼的心緒,但又能在更深的根基處化解一切對立與沖突,将一切愁苦化作淡淡的輕煙随風而逝,從而進入一種物我兩忘的澄明之境,擺脫一切煩擾羁絆,而不似屈原那樣苦苦掙紮和自我煎熬。
《離騷》中的“自我形象”除了悲苦失意,更突出的是怨憤、不屈,乃至迷狂。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中說:“屈原的偉大恰恰就在于他始終以社會的命運和曆史的命運為自己的命運,就在他的價值自居的人格精神。”所謂價值自居就是把某種超越個體的更高的價值追求内化為自身的感性生命,把無限寓于有限,在這種價值擔當中,個體完成了對自身的超越。所以屈原對楚王和奸臣充滿了怨憤的情緒,并對其進行大膽的批判和嚴厲的斥責。他批判楚王的昏庸:“荃不察餘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初既與餘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他斥責群臣的讒佞與貪婪:“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他甚至不惜與整個世界為敵,向一切流俗之輩開火:“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對屈原來說,這種怨憤不是個人政治失意的情緒發洩,也不是對陷害自己的小人的仇恨,而是對自己所追求的美政理想的維護,對人生價值的堅守,因而才能在失意的逆境中不為勢利所誘,“甯溘死以流亡兮,餘不忍為此态也。鸷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離騷》中最主要的“求女”情節,其實正是尋求出路、反抗時世的具體表現。詩人為了實現美政理想,忽而上天,忽而下地,與巫蔔溝通,與神靈對話,幾乎陷入了一種不可自拔的迷狂境界,直至最後“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将從彭鹹之所居”。據王逸注,彭鹹乃殷賢大夫,谏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如果此說可信,那屈原顯然是不惜以死明志,這是用個體生命發出的最激烈的抗争宣言。
蘇轼滿懷治世理想,入仕後卻屢遭小人排擠,多次被貶。他詞作中的“自我形象”也時時流露出隐隐的怨憤之氣,比如《漁家傲·贈曹光州》:“作郡浮光雖似箭。君莫厭。也應勝我三年貶。”對友人的勸慰實則蘊含着自己的心曲。《浣溪沙》:“雪裡餐氈例姓蘇。”調侃之中不能說沒有怨氣的鼓蕩。但與屈原不同的是,蘇轼沒有選擇劍拔弩張式的抗争,而是于當下的生活中尋求生命本真的意義,個人的寵辱、政治的得失全都在煙霞霧霭、清風明月的審美境界中化解于無形。對國君,他既無詈罵也無怨怼。“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铗悲歌。”(《滿庭芳》)“道遠誰雲會,罪大天能蓋。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可觊,舊學終難改。”(《千秋歲·次韻少遊》)對君王仍是一片深情,但同時也表明了自己的操守。蘇詞中的“自我形象”更多的其實是灑脫曠達,是面對風雨來襲的坦然淡定,如《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詞人借冒雨徐行,表現了雖處逆境屢遭挫折而不畏懼不頹喪的曠達胸懷。有此胸懷,自然“覺從前皆非今是”“我今忘我兼忘世”,在物我兩忘中達到更高的境界。
作為豪放詞的開拓者,蘇詞中的“自我形象”自然也有一些雄豪的氣息在,“且趁閑身未老,盡放我、些子疏狂。百年裡,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滿庭芳》)一個“渾”字将悲憤之情化為磊落之氣。而在《江城子·密州出獵》中則直接進行自我刻畫:“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這是何等氣概,雄姿英發,豪放威武,這種狂放與《離騷》中的迷狂是大不相同的。班固《離騷序》評屈原:“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論語》雲:“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班固的評價顯然是批判屈原狂蕩行為的不妥。蘇轼之狂,則更多的是一種意氣風發,正如《十拍子》所寫:“身外徜來都似夢,醉裡無何即是鄉。……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這種狂放不是糾結焦慮不知出路所在的迷狂,而是超越個人境遇的偃蹇困頓,跳出生活之外反觀生活的淡定灑脫,這也正是宋王朝知識分子所熱衷追求的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綜上所論,《離騷》與蘇轼詞中無疑都塑造了鮮明的“自我形象”,詩人的主體性得到了充分的呈現,二者因為相似的境遇,二人的“自我形象”有諸多同聲相應之處,但總體來看,一個悲苦、怨憤、迷狂,一個孤寂、曠達、雄豪。二人的作品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兩座寶庫,給後人以無盡滋養。
(作者李菲系沈陽建築大學副教授;韓偉系遼甯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