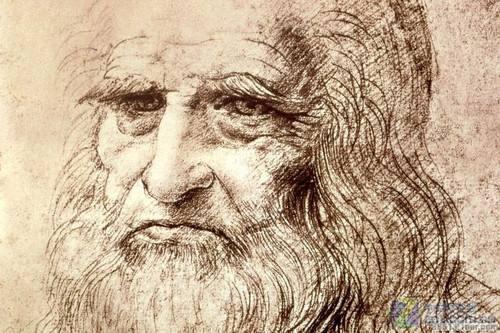“前面有兩頭,母子豚,盯一會兒就出來了。”49歲的江西都昌縣江豚救護隊隊長占柏山站在甲闆上,手指船前方的水域,提醒船上的隊員留意江豚的動态。
随風浮動的湖面,等待着江豚出水的瞬間。一頭江豚冒出一顆灰色的腦袋,打破湖面的平靜,又迅速沉入水下。這頭江豚消失後,又一頭江豚露出水面。“這是兩頭江豚,後面的那頭個頭小,是一對母子豚”。占柏山解釋。
在鄱陽湖上生活了49年,占柏山對江豚再熟悉不過。從漁民到江豚守護者,他與江豚也有着49年的情感。
2021年2月,經國務院批準,長江江豚由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升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被稱為“水中大熊貓”。據央視新聞報道,今年5月監測發現,鄱陽湖的長江江豚數量已增加至700餘頭。
然而今年7月以來,鄱陽湖水位迅速下降,提前進入枯水期,江豚面臨擱淺等一系列危險。占柏山和江豚救護隊員每天在湖面24小時巡查,在水面和灘塗之間守護江豚的安全。

9月7日,江西都昌縣大咀頭附近水域,一頭江豚露出水面,岸邊有許多垂釣愛好者。以往同期,釣者站立的地方還在水下。旱情導緻的水位下降及鄱陽湖十年禁漁吸引了許多江豚在此覓食。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攝
一天遇到近二十頭江豚
進入枯水期的鄱陽湖,湖面已經收縮成一條河。駕船行駛在湖中,才能更清楚地感受到鄱陽湖的幹旱狀況。
船前右側的湖岸隐沒在一片灰撲撲的土地外,左側的灘塗在往年的九月裡還沒在寬闊的湖面下,現在已經成了一片灰色荒漠,零星的幾隻白鹭站在水邊覓食,偶爾四處張望。
今年7月以來,鄱陽湖地區遭遇幹旱天氣,湖水水位迅速下降,威脅着江豚的生存環境。
“水位下降、湖面變窄,江豚進入主航道活動,增加受傷的可能。”占柏山說,為了避免影響江豚,他們的巡邏船隻盡量沿着湖邊行駛。同時,控制巡邏船的行駛速度,避免誤撞江豚。
據江豚救護隊員占大旭介紹,鄱陽湖裡多湖汊地形,湖水後退太快,江豚不能及時遊回深水區,會擱淺在湖汊地區。“船到不了的灘塗地帶,我們就徒步巡護。”
江豚救護隊每天出船巡查湖面都昌鄱陽湖水域,驅逐在禁釣區域的釣魚者。湖邊有以前留下的廢棄蝦籠和垃圾,救護隊員都會帶到湖區外處理。同行的還有2位漁政執法人員,将每天的巡查情況填入巡查登記表中。
9月3日,江豚救護隊的船沿着湖面巡護一天,隊員遇到近二十頭江豚。占柏山介紹說,随着水位下降,江豚集中在挖沙形成的深水區域。往年的9月份,鄱陽湖還處在豐水期,江豚活動的範圍會更大。
江豚躍出水面的畫面雖令人欣喜,占柏山的注意力還在湖水水位下降後顯出的灘塗上。巡護船行過灘塗時,占柏山把雙筒望遠鏡挂在脖子上,望向遠方。“能在水裡跳來跳去的基本都是健康的,巡護主要看有沒有江豚擱淺在灘塗上。”

9月7日,都昌江豚救護隊隊長占柏山跳下漁船與隊員們一起清理幹湖床上的垃圾。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攝
“江豚多,說明湖裡魚多”
席地坐在鄱陽湖邊,看着鄱陽湖的水面,占柏山講述着小時候對江豚的記憶。
占柏山出生在鄱陽湖上,從小跟着父母在船上長大,搖着木船槳在鄱陽湖上擊水而行。
跟着父母出船捕魚,小時候的占柏山看到江豚遊到船邊,以為是一條大魚。回憶起第一次看到江豚的場景,49歲的占柏山語調中還透着兒時的懵懂和激動。父親告訴他,那不是魚,是“江豬”(江豚的俗稱)。
灰白色的皮膚,圓滾滾的頭部,江豚時常出沒在漁船附近。江豚親人、性情活潑,被稱為長江水域“微笑的天使”。占柏山說,在老漁民的心目中,江豚并非吉祥之物。漁民使用傳統的木漁船,船體小扛風能力差,經常被掀翻在風浪之中。江豚出沒,意味着風浪将來,在經驗豐富的漁民心中,是不宜出船的信号。
兒時的占柏山還意識不到風浪的危險,對遊到船邊玩耍的江豚心存憐愛,“跟養的狗和貓一樣,它會遊到船邊玩,距離不到一米。”
占柏山在湖上生活,沒有進過學校讀書,生活經驗幾乎都來自老漁民的教導。在漁民看來,灰白色的江豚還透着“邪惡”,打魚時撈到江豚要放回湖中,避免厄運臨頭。漁民的迷信,使得江豚反而得以躲開捕殺。
占柏山說,江豚雖然常在湖中出沒,但從未聽說過漁民捕殺或者售賣江豚。
但占柏山告訴新京報記者,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鄱陽湖漁民使用柴油動力漁船,湖面上的挖沙船也開始增多,湖面上經常響起往來船隻上機器的轟鳴聲。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鄱陽湖的水質也一度惡化。占柏山回憶,漁民到湖中捕魚,曾習慣取湖水在船上煮飯。後來就沒有人再用湖水,出船時都帶上幹淨的飲用水。水質的惡化,也會造成江豚感染皮膚病,灰白色的光滑皮膚上出現斑點和潰爛。
漁民的生活已經不似從前,占柏山出船到湖中捕魚,就很少再看到江豚的身影。“可能是發動機的聲音吓走了江豚,也可能江豚數量确實少了。”
根據國家漁業部門的普查數據,江豚數量确實銳減。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江豚還有3000多頭。到了2006年,長江淡水豚類考察發現,長江流域剩下的江豚隻有1800頭左右。2012年的調查數據顯示,長江江豚隻剩下1040頭。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國家漁業部門進行普查,鄱陽湖湖區魚類共有158種。此後的近二十年間,鄱陽湖魚類減少了30餘種。鲥魚、胭脂魚等瀕臨滅絕,湖區魚群數量也在減少,江豚的種群數量随之下降。
“江豚多,說明湖裡的魚多。沒有了江豚,說明湖裡的魚也少了。”多年的捕魚經驗讓占柏山意識到,江豚的數量變化與漁民的收入存在着某種聯系。

9月7日,忙碌了一上午的占柏山與隊員們在巡護船上吃飯。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攝
從漁民到江豚救護者
2009年,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到鄱陽湖區科研,需要經驗豐富的漁民帶路。因常年在鄱陽湖上捕魚,熟知當地的水域環境,占柏山當上了協助科研的志願者。
對江豚的憐愛,第一次戰勝了迷信。“老人覺得江豚影響運氣,我不在乎。專家都在保護江豚,我也應該去。”但占柏山明顯感覺到,剛參加江豚救護時,一些漁民朋友并不理解。
占柏山有着一雙粗糙的手,但指甲短到不能再短。這是因為所有參加救護江豚的隊員,必須把指甲全部剪掉,避免劃傷江豚。
占柏山的手機裡,還保留着第一次抱着江豚的照片。江豚躺在濕淋淋的擔架上,占柏山穿着橡膠防水服,對着鏡頭露出牙齒微笑。
江豚一天進食八九公斤魚,一旦被困在淺灘,很容易陷入食物匮乏的境地。救護隊員得到江豚受傷或擱淺的信息後,要及時趕到現場救助。

9月7日,江西都昌縣,江豚救護隊員站在船頭尋找露出水面的河道垃圾。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攝
講述救助江豚的過程時,占柏山語氣中透着小心翼翼,“所有的人這時候都不能說話,船上和水中的隊員隻能用手勢交流,聲音太大會驚到江豚。”
救護人員會使用超過江豚活躍範圍一倍的漁網,把江豚收攏到靠近岸邊十幾米的位置。占柏山提醒說,江豚的皮膚嫩滑,拉網時漁網不能觸碰江豚,不然會劃傷江豚。
靠岸後,救護隊員下水,改用密如帆布的漁網固定江豚,再用鋪滿海綿的擔架擡出江豚,轉移到醫院或深水區。占柏山伸開左臂上托,右臂向前做出從下往上的環抱動作。“就像抱小孩一樣,一條胳膊托着頭,一條胳膊固定住尾巴。”
結束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志願者服務後,占柏山徹底轉變了心态,“外地的專家都到鄱陽湖保護江豚,作為本地漁民,沒有什麼理由不去保護。”
漁民雖然經常遇到江豚,但缺乏保護意識,看到擱淺或受傷的江豚也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滅。“很多漁民迷信,不願意去動江豚。”
參與江豚救護後,占柏山也會向社會和漁民朋友普及江豚知識,希望他們發現擱淺或受傷的江豚後,聯系漁政或江豚救護隊。
2019年,鄱陽湖實施全面禁捕後,都昌縣漁政執法部門回收漁船2850艘,銷毀網具179.92萬公斤,全縣9611名漁民上岸轉産轉業。都昌縣挑選4條回收未拆解的鋼制船隻,統一标識,作為日常護漁和江豚救護的巡護船隻。挑選6名江豚救護隊員進行江豚巡護和救護。占柏山也“洗腳上岸”,卸去漁民身份,專職做江豚救護隊員。
在都昌縣漁政執法大隊工作人員詹定鹂看來,占柏山等江豚救護隊員都曾是經驗豐富的漁民,并且學習專業的江豚救護知識,熟悉江豚的習性。救護隊員發現擱淺或受傷的江豚需及時上報,根據江豚的身體狀況,把江豚轉運到深水區或送往醫院救治。
在詹定鹂的辦公室櫃子上,存放着一副救護江豚專用擔架,以備緊急救護江豚使用。為了避免江豚在轉運途中受傷,擔架上專門開了兩個孔,固定江豚的鳍。

9月7日,江西都昌縣,為了保障水源安全,漁政幹部駕船來到觀湖水廠附近水域,勸說釣魚愛好者離開。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攝
24小時巡護
對江豚的保護,已經深入到當地人的日常生活。
2020年12月28日,鄱陽湖畔的都昌縣湖濱小學,挂牌成為江西省第一所“保護江豚示範學校”。校内設立江豚文化長廊和江豚教室,宣傳江豚相關知識,呼籲學生提高生态環保意識,從小保護江豚。
據湖濱小學教師葉春梅介紹,學校通過開設江豚科普知識等特色課程,讓孩子們從小接受生态文化、濕地和江豚保護等知識教育。每年的開學第一課,江豚相關知識内容都是必備的闆塊。
湖濱小學專門設置的江豚教室内,淺藍色的色彩配合魚形吊燈,把教室打造成一個水底世界,牆壁上彩繪的長江江豚分布圖、江豚形狀的書櫃增加了教室的江豚元素。葉春梅介紹說,每年的兒童節和江豚保護日,學校都組織學生到江豚教室上課,邀請江豚保護專家和志願者為孩子講述江豚的故事。繪本中的江豚淘淘的故事,也常被學生用作寫作文的素材。
書櫃上擺放的江豚彩繪中,一頭深藍色的江豚模型上,塗着“3000 ”字樣。江豚教室的彩繪牆上也畫着這串數字,這是因為以前江豚有3000多頭。在手繪環節,一位學生在自己的江豚上寫上了這串數字,“孩子也是希望江豚越來越多,能像以前那麼多。”
湖濱小學還會組織學生到湖面上,跟江豚救護隊員一起巡護江豚,聽占柏山講述江豚救護故事。
葉春梅說,學生從書本上和電視上看到江豚,與實地觀察江豚的感受是不同的,“看到湖裡的江豚,孩子能感受到江豚鮮活的生命”。
占柏山有三個孩子,從小都在學校上學,假期跟着占柏山出船捕魚。孩子對江豚更加親切,每次在湖面遠遠地看到江豚都很激動。今年,占柏山最小的兒子已經22歲,開始和父親一起擔負着江豚救護工作。
鄱陽湖十年禁捕後,湖中的魚、蚌和候鳥也逐漸增多。占柏山明顯感覺到,近兩年,湖區可觀測到的江豚數量在變多,“幾乎每天都能在湖上看到江豚”。據央視新聞報道,今年5月監測發現,鄱陽湖的長江江豚數量已增加至700餘頭。

9月7日,江豚救護隊員用力拉起沉在淤泥裡的垃圾,這是江豚救護隊員日常的工作。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攝
占柏山稱,禁捕前,湖面漁船來來往往,螺旋槳和漁網常會傷及江豚。“禁捕後,受傷的江豚明顯比前幾年少很多”。
如今,持續的幹旱讓江豚面臨又一次考驗。詹定鹂擔心,幹旱天氣若持續,鄱陽湖冬季的水位有可能達到曆史最低點。水質惡化、食物資源短缺,江豚擱淺或被困的可能性增加。人類活動密集,對江豚構成的威脅将進一步加重。
在詹定鹂提供的應急預案中,對江豚保護有一系列的舉措,建立智慧化監測預警系統、加強沙坑等重點水域巡護、加強對母子豚的重點關注等。都昌縣在全縣重點水域鄉鎮組建了17支護漁隊,263名護漁隊員,24小時全天候巡查湖面,加強江豚的保護宣傳和救助。
提及江豚可能遭遇的危機,詹定鹂仍緊蹙眉頭。“不能人為幹涉太多,但又要有效保護”,在他看來,在加強湖區巡護的同時,還要大力宣傳江豚保護,動員更多群衆參與到保護保護的行動中來。
新京報記者 聶輝 編輯 袁國禮 校對 劉軍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