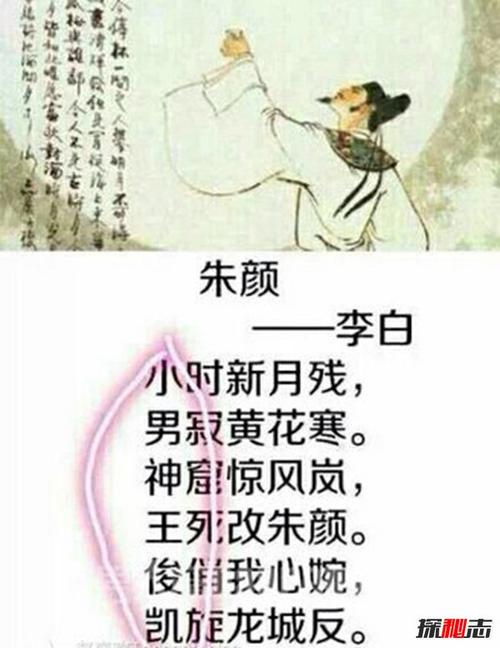我的U盤不見了?“我的U盤不見了”她一邊收拾着一團糟的桌面,一邊這麼說她沒看着我,我看着她,突然覺得她很忙,我想等她忙完,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我的U盤不見了?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我的U盤不見了。”
她一邊收拾着一團糟的桌面,一邊這麼說。她沒看着我,我看着她,突然覺得她很忙,我想等她忙完。
“我快要死了。”
她終于一臉冷漠地看着我并且告訴我她要死了。冷漠得好像要死的不是她,而是一個無關緊要而且該死的陌生人。
雖然她一無絕症二無抑郁三無仇家。雖然她把自己保護得很好,無論從生理從心理還是從人際方面都沒有任何能置她死地的東西。但我相信她真的快要死了,完全是因為她是預言家。
什麼是預言家?就是那種預測你什麼時候會出車禍,或者是某一條船會在某個海域沉沒的人。他們是上帝的通信員,告訴你上帝為你安排了什麼,睜眼閉眼做個夢都是許多人的福禍生死。
當然,以上的都是你們的想象。她能預言的隻限在她身邊生活的甲乙丙丁們或者是有着血緣這種無聊的東西作為牽挂的親人們。預言也不詳細,沒有準确的時間和地點,隻有人物和模糊的事件。模糊的類似于你将會從某條樓梯滾下。她和你們想象中的預言家隻有一個相同之處,就是所有預言都不是好事,都會實現。
這些從我認識她的第一天就知道了。
那是三年前吧,我和她坐在公園的長椅上。
她對我說“活該”的時候,她曾經的室友正被擡上救護車。原因是失足摔倒并一頭撞到了樹上。
活該,是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然後,我成了她的室友。
“也許你可以先哭哭。”她扔了一包紙巾過來。
“哭不出來,我餓了。”我接住了紙巾。哭不出來,但我做了另一件在她死後該做的事。哭和回憶,都是别人死後你該做的。
“我們去吃烤肉吧!”
“嗯。”
得到我的回答,她似乎很高興,一路上叽叽喳喳地說個不停。要不是看在她快死的份上,我發誓我一定會一腳把她踹進下水道的。
到了烤肉攤,我才知道她才不是來吃烤肉的,她是來喝酒的。一杯接着一杯,黃色冒泡的、透明得像白開水的,她都是仰起頭一口氣喝下。
我沒有阻止她,其實我在等着她醉,等着她說一些關于她的死。最後,她醉了,卻安靜地沉睡過去。
接下來的幾天,她都很早出門很晚回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裡,她不說我不問。雖然我們很有默契地不提那個要命的預言,但是我很想知道她到底會在什麼時候死去,怎麼死去。
或者是我想和她同步,一起完成她死前該做的,想做的事。
于是,我跟蹤了她。
她在閑逛。呃,也許吧。
看上去很像閑逛,然後偶遇舊友,然後重聚,最後離别。一切都自然得不像話,多年不聯系的好友在街上偶遇,然後吃個飯,聊聊天。要不是知道她要死了,我也許會為朋友重逢鼓掌。破綻隻在于三天内,她“偶遇”了七個朋友。
“再見了。”
她對着她的朋友說。
“嗯,再見。以後多聯系。”
“好。”她揮着再見的手和朋友說好,看着朋友離開,然後轉身走向坐在角落裡的我。
“回家吧。”
被抓個正着的我大氣都不敢出,隻敢默默地跟着她。
我心裡噼裡啪啦地打起了算盤,要是她沖我發火,那麼她還可以活一段時日,要是......
好吧,沒有要是了。
她一臉平靜的看着我,舉起酒杯,喝下。
别問酒是哪裡來的,當然是買的。而我,當然是期待着和她一起醉。
這裡是吐露心聲的好地方。不用忍受燒烤攤的油煙,不用忍受隔壁桌的噪音,不用忍受人來人往的擁擠。這裡隻有我和她,還有一張桌子,十幾瓶酒。
這裡是我們的家,或者房子吧。
一切都好,我隻要裝睡......
她死了。
在我睡着之後,她獨自出門。在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推開一個小孩,然後以抛物線的優美姿态奔向空中,落回地面,摔成一朵花和一堆泥。
最後是什麼樣都不重要,反正她現在是罐子裡的一堆粉末,埋在了烈士陵園。
死就死,還留了一堆麻煩事。
比如,那筆巨大地留給她七年未出現的父母的保險金;比如,多年未見的朋友們在收到她準備的禮物後的痛哭流淚;比如,挂在門外的那些寫着“英雄”的牌匾,錦旗,數不清的四面八方的采訪。
還有留給我的是這間隻有一張桌子的客廳和兩個房間的房子,和一個預言。
唯一不麻煩的是這個房子裡有足夠的食物讓我撐到人們散去對“英雄”的熱情。我才不願意對着鏡頭和話筒,淌一把鼻涕,抹一把眼淚。
兩周後,世界平靜了,我想,我可以戴着頭盔去祭拜她了。
當你看到我從烈士陵園的小山坡上滾下來的時候,你就會明白戴頭盔遠比帶紙錢有意義多了。
沒錯,這是她的預言。
她說,我要走了,房子留給你,祭拜我的時候記得戴頭盔,我會很樂意看到你戴着頭盔滾下山坡的。最後,再見!
那時我努力地閉着眼睛,忍住我起來揍她或抱她的沖動。可是所有預言都不可以避免。于是我閉着眼睛聽着她開門、關門和下樓梯的聲音,直到安靜了。就這樣吧,像她明知道我在裝睡一樣,像我明知道卻不睜眼一樣......
她說,我的U盤不見了。
對呢,那個花了我兩周時間才找的U盤,裡面隻有一個地址。
我想,我需要從坡底爬起來,去那裡看看。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