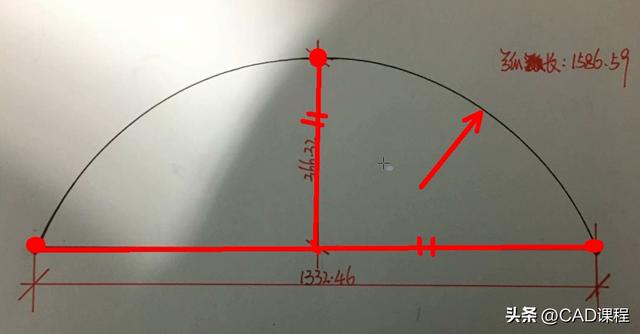皇上十日裡有八日閑時便來安檀的宓秀宮待着,有時便是一整天待在這裡,晨起直接去早朝,便是把宓秀宮當做寝宮一般。後宮衆妃雖是見慣了這樣的場景,但難免意不平了,安檀自然能夠洞察這樣的情況,便也不能自安,也時常勸誡奕澈去旁的嫔妃那裡,隻是奕澈仍是來宓秀宮的多。
安檀恩寵之盛連在王府中備受寵愛的昭貴姬亦受了冷落,昭貴姬是個忍不住的,幾日晨省對安檀大有意見,出言諷刺不說,還沒的把旁人扯進來。安檀見形勢不妙,便對奕澈道:“皇子帝姬對父皇難免思念,澈郎不顧着母妃,總要顧念着孩子的心意。”
奕澈也逐漸明白宮中女子的心思,看得出安檀的為難。便連着幾日去了其他嫔妃宮裡。
這一夜江海勝來傳話皇上擺駕合歡宮了,請懿妃娘娘早些歇息。安檀點了頭算是應了,打賞了江海勝便早早卸了妝容睡下,獨自在床上靠着,如玉見安檀怏怏的,便上前來給安檀的腳爐添了些熱水道:“娘娘這是想念皇上了。”
安檀偏過頭看如玉,無不委屈道:“我是很想他的。隻是如玉,我不得不勸他去别處,他幾日不來了,你說他會不會惱我?”
“怎麼會呢,”如玉笑道,“自古宮裡的女人就是這樣,皇上自幼在宮中長大,自然知道集寵愛于一身,何嘗不是集怨于一身?皇上疼愛娘娘,便要平息後宮非議,怎麼會惱了娘娘呢?”
安檀點了點頭,如玉扶着安檀躺下道:“娘娘快睡吧,皇上今天去貞慎夫人那裡了,也得讓和慧帝姬和二皇子見見父皇不是?娘娘隻管安心就是了。”
安檀點點頭便沉沉睡下。夜夢幽長,殿裡的銅爐燒的極暖,身上搭着輕薄的羽絨衾還熱的額頭冒汗,安檀翻了個身輕聲叮咛。
忽聽窗外淩淩雨聲淅淅瀝瀝響的不聽,安檀身上稍稍起了寒,卻抵了殿内的燥熱。似乎有雨淋淋灑在安檀身上。安檀仰起頭看到細密的雨絲悄無聲息的落在身上手上,是江南!隻有江南,才有這樣溫暖的雨。安檀以手遮住前額,眼簾漸漸清晰,歡喜着漫步在河邊,卻看河中船上朦胧雨下有一個月白身影長身玉立,負手執着折扇,身形不動,卻不停的遠離着岸邊。
“澈郎!”安檀看清了那人,不由高聲驚呼。那人不應,安檀這便着了慌,往河中沖去,“澈郎!”安檀的裙擺沾了水,連雲鍛的料子極重,安檀跨着步子依舊走去。
奕澈似乎才聽見安檀的驚呼,緩緩的轉過身來,他伸着手:“檀兒…别過來,這裡太深了。”安檀隻能看到奕澈疼惜的目光,隻是一味的往前走,企圖靠近奕澈。
“澈郎…”安檀逐漸感覺身子已經由不得自己,水越來越深,幾乎漫上了她的胸口,她的腳步仍然停不了。奕澈臉上溫柔的疼惜突然變得冰冷而決絕,吓得安檀一怔,“再走的深了,我…朕也救不了你!”奕澈聲音變得凄厲尖銳,安檀大驚,伸手捂住捂住雙耳,腳下卻一絆,冰冷的河水浸在身上。
安檀不會凫水,急忙掙紮,卻越掙紮沉得越深,直到水掩住了面孔。“啊——”安檀驚聲尖叫,膝蓋一彎,跪了下來。
安檀急于求救,拼命揚起首來,卻驟然間看見雍王府的雨花閣,一聲驚雷劈開天空,安檀跪坐在地上,任由瓢潑大雨灑在身上,安檀看見侍女手裡端着一盆盆的血,潑在地上。安檀卻被人按着用,一盆腥臭的熱血劈頭而下!
安檀怕極了,掙脫了人拼命跪走着去奮力敲砸雨花閣的大門:“澈郎!澈郎!救救檀兒!”
門吱呀一聲打開,一席雪白的中衣刺得安檀眼睛疼,那中衣卻汩汩冒着猩紅色的血,血的腥臭和粘膩無處不在,雪白和紅色詭異的湧動。安檀顫抖着順着血看去,卻看到顧之湄蒼白着臉,額頭上都是豆大的汗珠,她的手上滿是鮮血!她伸着手掐向安檀的脖子——
“柳安檀!若我的孩子有事,我必不會饒了你!”
安檀胡亂的揮着手,“不是我!不是我!是你自己不當心!為什麼怪在我身上!為什麼……”顧之湄的手已經掐住安檀的脖子,安檀掙紮着,摸見手邊雕花瓷枕,抓起來就向顧之湄的頭砸去!
“嘩啦”一聲,瓷枕摔的粉碎,安檀猛坐起來,面上挂着淚珠。如玉推門跑進來,“娘娘!娘娘怎麼了?”說罷坐在床邊摟住安檀。
安檀渾身顫抖着,隻盯着如玉一句話說不出,突然抱着如玉嘤嘤哭起來。
如玉見安檀這般心裡明白,不再問。遙想安檀四年前入王府,一年前出了那件事,便時常噩夢纏身。安檀亦多方請太醫醫治,但太醫道這是心結,旁人治不了的。今日想必是皇上去了貞慎夫人處,安檀一時心結難解,故而夢魇。
如玉心底歎氣,安撫着安檀道:“娘娘無事了,隻是夢魇罷了,娘娘不必當真。”頓了一下才道:“往事都過去了,如今的日子都好過了。”
“都好過了麼?”安檀埋首在如玉懷中,悶悶的啜泣,“我隻覺得這樣的日子愈發難過。愈發提心吊膽,茫茫無邊……”
如玉靜默,良久安檀止了哭,如玉才端着熱茶侍奉安檀喝下道:“娘娘心裡知道。那些事就該放下了,既然宮闱深不見底,就要打起一萬分的精神防着那些心懷鬼胎的人——娘娘是知道的。”
安檀哭訴着:“是她!是她!我次次夢魇都是她!我不過是去看她,是她自己不當心傷了孩子,是她自己不當心才早産!更何況…更何況那個孩子安然無恙!可她偏偏賴在我身上…”安檀哭得悲切,“明明不是我,為什麼我就要為了她的孽障脫簪戴罪!為什麼他們都在為那個孽障的出生歡慶,我卻要跪在雨花閣前一整夜直到暈厥也無人問津!”
如玉眉目含憤,咬牙道:“她們就是趁着王爺不在作踐娘娘!”如玉扶起安檀,“娘娘!娘娘不能這樣,熬壞了身子豈不是隧了她們的願!”
安檀恍若未聞,喃喃:“她還封了夫人,不就是仗着那個孩子!”安檀握緊了拳,直握的關節發白,“我怎會讓她得意!”安檀閉着眼,淚水不斷從緊逼的眼中流出,染濕了安檀精緻的面容。
如玉見安檀流淚不已,卻已下定決心,當即不再多說,靜坐着陪伴安檀。
被這夢魇一攪,便過去了半宿。安檀一旦如夢便不易醒來,便也不敢再睡,便拉着如玉二人說話,直到天際泛白。
按例今日應當去給貞慎夫人請安,安檀昨日一夜不曾安睡,精神實在不濟。如玉勸道:“娘娘今日不如告了假好生歇歇,也不必去合歡宮瞧人臉色了。”
“無妨,”安檀輕按着額頭搖搖頭道,“皇上昨日才去了合歡宮,我今日便告假,怕是要落人話柄。梳妝吧。”
安檀性格倔強,如玉拗不過,便為安檀梳理着如墨雲鬓,看着安檀蜷曲的手,替她輕輕展開來,溫聲:“娘娘心中一生惱便手指蜷曲,娘娘當心鳳體,往後的日子還長,對貞慎夫人,不值當的。”
安檀平了眉頭,深深吐了一口氣,手指緩緩舒展開來,輕聲道:“本宮知道分寸。”
葉桃為安檀選了玄色蘇緞萬字羅裙,上以深黛遍鏽芍藥,自上而下花葉漸漸稀疏,至擺便隻為素色,下墜米珠,細碎流轉,外披藏青色寬袖窄腰青鸾疊戲花樣,領間圍一大氅,端華大氣又不失華麗,安檀盯着銅鏡中綽約貴重的人影,淡淡着吩咐備轎。
轎子搖搖晃晃,轎夫行動迅速如一,轎裡坐着貴人,無人敢多話。安檀坐在轎中思忖,不一會兒便到了合歡宮,安檀的軟轎在門口一停,不消如玉言語,便有小宮女福了禮進了内間通傳。
如玉在一旁悄聲道:“合歡宮的丫頭瞧見倒是十分有眼色。”
安檀應了一聲不掀轎簾子,聲音從轎子裡傳來,“誰當寵,誰得意,自然被奴才們口耳相傳。更何況她顧之湄是什麼人,怎會讓奴才有一絲松懈。”
片刻便有宮女兒恭恭敬敬迎了安檀的轎子入内,安檀扶着如玉的手下轎,悠悠轉轉走進華音殿,不過幾步路的時間,便含了明媚的笑意。
安檀生的明豔絕倫,素來見人便是不笑,也讓人忍不住多看兩眼。如今笑意叢生,愈發含了三分媚、七分俏,愈發讓人挪不開眼。
安檀側身跨進殿門便笑道:“姐姐好閑暇,比不得妹妹跑上跑下的四處請安。”
遙想當日在王府中平起平坐同為側妃,入着紅牆卻要瞧人臉色,安檀不由抿唇,到底今時不同往日。待如玉伺候解下大氅,安檀才捧着縷金雕花手爐福身道:“參見夫人。”
貞慎夫人着了家常深碧如意雲紋對襟宮裝,與安檀玄色外裳想比,更多了幾分平易近人。顧之湄緩緩彌散開輕淡笑意,免了安檀的禮道:“妹妹這話可是說笑了,妹妹如今為四妃之首,哪裡有人敢勞動你四處請安。”
安檀款款落座,尋了個舒暢姿勢道:“顧姐姐一味的笑話我。最最閑暇的自然是姐姐,天寒地凍,若非規矩所限,妹妹自然樂得窩在昭陽殿躲懶避寒。”
安檀喚貞慎夫人“顧姐姐”,原是王府裡的稱呼。如今入了宮,原應改了口,安檀依舊如是喚她便有提醒顧之湄之意。
顧之湄似毫不在意,命人上了茶笑道:“妹妹今日來了合歡殿請安乃是規矩所限,老祖宗的虛禮不得不遵,咱們卻不用那般拘謹。皇上新賞的湘妃醉,妹妹嘗嘗。”
安檀捧起茶飲了一口,隻覺口齒留香,這湘妃醉入口稥,細品醇,可謂妙極。安檀不由贊道:“姐姐的好茶。聽聞這貴妃醉三年才産一斛,皇上那兒留了一斛,剩下的兩斛都在姐姐這兒了吧?”
貞慎夫人笑道:“妹妹見多識廣,本宮最愛品茗,皇上不過是瞧着本宮喜歡便着人送了來。本宮隻知道這茶珍貴,但幾年産幾斛,也都是聽妹妹方才說才知道。”
二人閑談一二,倒是氣氛十分融洽。安檀四處望望,笑問道:“平日裡姐姐這宮裡好生熱鬧,今日怎麼靜靜的呢?和慧帝姬和二殿下呢?怎麼不見他們跟着姐姐?”
貞慎夫人低眉飲茶,長長的睫毛落在眼暈上明媚不定,提及孩子,說話間也含了笑意:“瑾瑜跟着太師傅去女學了,予修那孩子又皮的緊,讓乳母帶着去上林苑玩去了。”聲音愈發含了溫軟,“要不然無論如何也要讓他來給妹妹請安。”
安檀随口應了一聲,放下茶盞,揮揮手示意如玉下去,顧之湄見狀,也對寫意使了使眼色,寫意帶着一衆侍女下去關上了殿門。安檀道:“既孩子們不在,也不礙着咱們說話了。不瞞夫人,我今日來是想同姐姐談談二殿下的事。”
“哦?”貞慎夫人的睫毛一顫,隻一瞬又恢複了平靜,“妹妹這話,又是從何說起呢?”
“咱們明人不說暗話,”安檀扶着鋪散旖旎的萬字緞花,緩緩說道,“以前在王府的事,于我而言,是時時難忘的,不知姐姐可還記得?”
貞慎夫人深知安檀所說何事,然而不以為意,隻淡淡道:“若要說起從前的事,孰是孰非已是早有定論,又何必多有糾纏?昨日之日不可留,若是煩憂舊事,本宮确實不願多想。”
安檀蹙起眉頭看着顧之湄道:“當時雨花閣裡隻有我二人在,事實是什麼,姐姐自然明白。該追究的也都追究過了,可姐姐心中的定論事實麼?今時今日,姐姐又何必再颠倒黑白,連一句實話都不肯告訴我?”
貞慎夫人擡起眼眸看向安檀,問道:“此事過去多年,當年蓋棺定論便是公道,妹妹還糾于此節麼?我便勸妹妹一句,位分初下,宮中瑣事甚多,妹妹既入宮來,便安之樂之。以往事,還是忘了吧。”
安檀心底大痛。她與顧之湄素來投緣,原本今日前來,便是等顧之湄承認當年事實,也好冰釋前嫌。現在看來,顧之湄是決計不肯松口了。安檀心下憤懑,痛心疾首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姐姐不曾體會當日我獨跪冷階之苦,又怎可知妹妹何以如此執念?這便是你所言的公道?”
貞慎夫人手中茶蓋猛地撞上茶盅,其音宛若鳴筝驚破一室寂然。貞慎夫人的聲音不冷不淡,偏偏如冰一般凝了人的呼吸,“好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妹妹自覺受盡冤屈,那敢問妹妹一句,可知我當日難産險些母子俱損是何等楚痛?你自做你的寵妃,我自守着我的兒女安然度日,我倆兩不相欠。這後宮之中,何人沒有委屈?”
“你再委屈,也安然誕下二皇子。”安檀發間流蘇晃動,“我長跪冷階以至身寒險些機理受損!你的委屈?隻怕是自怨自艾吧!”
貞慎夫人的面容一瞬間憤怒:“自怨自艾的是你!本宮亦然受損不能有孕,我同煕妃是一樣的,是你偏頗,是你忘不了!”
“你兒女雙全啊!你還奢求什麼?”安檀的眸子如同寒冰冷窖,“煕妃不一樣,你沒有資格讓我偏頗。”
一時俱靜,沒有人敢說話,貞慎夫人盯着安檀,面容早已恢複平靜,眼中如同深不見底的汪洋,安檀亦然,終究,貞慎夫人放下手中的茶盞,怆然道:“妹妹走吧。”
安檀心底怒火翻騰,卻傷懷不已,戚然道:“顧之湄,以往我道是誤會,仍對你有企盼,今日看來,是我多心了。”說罷甩開寬大的雲袖,拂袖而去。
貞慎夫人見安檀遠去,眸中才有怆然神色,端着茶盞的手緩緩落在雙腿上,靜然無語。
之湄仍然記得那個雨夜。
瓢潑大雨傾盆而下,她聽見門口泠泠笑聲,“顧姐姐,這樣大的雨,容我讨一杯熱茶可好?”
她急急讓人迎了進來,女子的裙擺和綿延的青絲依舊沾着濕漉漉的雨水,她的笑卻如同溫暖的初陽。之湄托着腰笑道:“總歸你來了,我怎麼能薄待。”她已經有了八個月的身孕。
安檀攏着薄被,吩咐人擦幹了地面的雨水,蹲在之湄身旁,仰臉笑道:“顧姐姐,還有兩月就臨盆了吧。”
之湄扶着小腹,靠坐在軟椅,溫溫笑道:“正是呢。”
安檀輕柔的撫着之湄高高隆起的小腹,不由豔羨道:“姐姐真是頂好的福氣。如若是男孩,姐姐可就有一雙龍鳳呈祥。澈郎也必定高興。”
之湄笑着,卻恍然怔住,她知安檀與奕澈情深,卻不知人後,安檀竟稱他“澈郎”!“澈郎”,這個稱呼,她在夢中念了無數遍,然而每每面對他時,她卻隻稱“王爺”,連王妃,都不敢稱他一句“澈郎”。
安檀面頰上還有未幹的發絲粘着,她是王府中最美的女子,年歲也小,輕靈跳躍,她的笑似乎能攝人心魄。之湄記得,奕澈曾對她說,安檀在江南雨中回首一瞥,就流落了江南水鄉一世的英華。彼時,之湄備着雍王府為柳府置辦的彩禮,溫柔答道:“那妾身,就恭祝王爺能與柳家妹妹百年好合。”
她想到過,安檀入府,必定是極受寵的。卻不想她就這樣生生奪取所有人的寵愛,包括韋娉之的,也包括她自己的。
“母親!”瑾瑜的聲音脆生生響起,隻見一個粉面人兒撲向之湄,之湄無力彎腰,隻得伸一雙手去抱,乳母還在孩子的身後追着:“郡主!郡主!跑不得…”
晚了。之湄的小腹一陣劇痛,之湄放下手中的孩子,她的小腹好痛,痛的幾乎要吞噬她的身體,痛的她彎下腰去。安檀在旁驚呼:“姐姐!姐姐你怎麼了,來人啊,宣太醫!宣太醫!”
之湄的雙腿間一陣熱流,寫意在身旁喊着:“側妃怕是要生了,請柳側妃回避。”之湄什麼都不知道,額頭嗡嗡的響,她用力揪着小腹處的衣服,她未出生的孩子隻有八個月,她多怕它保不住,她的耳邊回蕩着瑾瑜的哭聲。她打了一個激靈,是瑾瑜,是瑾瑜撞了她的肚子。萬一它保不住,那瑾瑜…
她的心中呐喊,不行!不行!我的孩子,不能再失去她的父王的寵愛!
王妃的聲音在殿外适時響起:“怎麼回事?”
她不能再等了,她拽住寫意的衣袖,她的額頭上有豆大的汗珠,她虛弱着對寫意說:“不是瑾瑜,不能是瑾瑜!”
後事,她便不知了。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