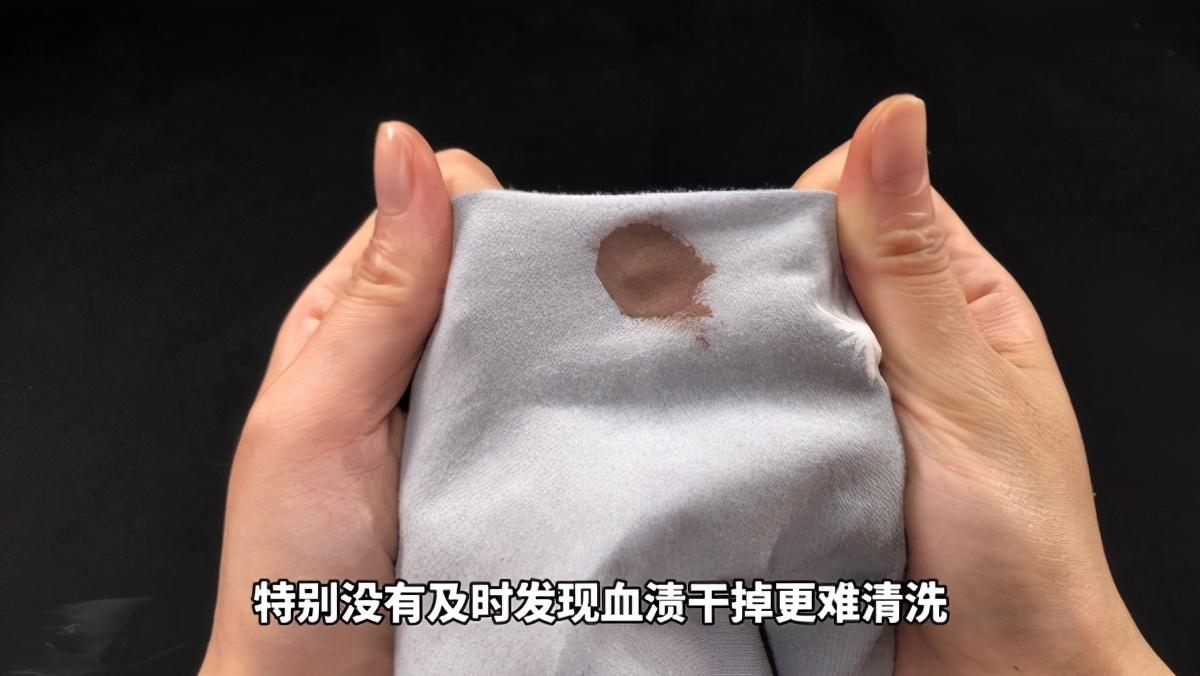張小娴有首詩寫的很好:
在對的時間,遇見對的人,是一種幸福
在對的時間,遇見錯的人,是一種悲傷
在錯的時間,遇見對的人,是一聲歎息
在錯的時間,遇見錯的人,是一種無奈
讀書也一樣。一本書需要在對的時間遇到對的人,才能有美好的故事發生。《紅樓夢》裡曹雪芹安排黛玉讀西廂是有極深的用意的,如果讓劉姥姥或者薛蟠去讀西廂,隻怕讀者比這二位還要興趣索然。再比如,十幾歲小女生讀瓊瑤、亦舒會如癡如醉、淚眼迷離,但你讓四十歲的大媽再去讀這二位,隻怕大媽撇撇嘴便去跳廣場舞去了。
武俠亦然。

如果一個人喜歡讀武俠,最好在十幾歲的時候讀金庸古龍。因為最美好的愛情,最快意的江湖,最熱血的夢想,最瑰麗的想象,隻會發生在十幾歲的時候。少幾歲可能就會不理解故事,多幾歲可能就會不相信情節。
如果一個人喜歡讀武俠,最好在二十幾歲去讀梁羽生溫瑞安蕭逸柳殘陽們。二十幾歲的人,眼中的世界自然和十幾歲有所不同,就像溫梁蕭柳筆下的江湖,遠比金庸古龍大多數作品裡構築的童話般的江湖現實、殘酷和陰冷許多。這區别,大略相當于離開校園步入職場。
過了三十歲還想讀武俠怎麼辦?難。三十多人的男人,絕大多數都是“受過戒的人”,在無數日本愛情動作片和網文的浸淫下,無論是愛情觀、世界觀都變得現實而功利,很難不對武俠小說裡的尾生、柳下惠們的“純潔愛情”嗤之以鼻,對侯嬴、朱亥們的“俠骨豪情”心動然拒。有這工夫刷刷抖音組團吃雞多好,看什麼胡連八扯的武俠小說?
然而,事情還是有例外的。夜裡再怎麼舒服,人們還是盼着天亮,盡管天亮要這要那的痛苦不堪,依然沒多少人喜歡《冰與火之歌》那樣的長夜。就像在無數個午夜裡突然驚醒時胸口的那一絲熱血,還會如毒蛇一般咬中你的心髒:此生為何而活?
《英雄志》,恰好就是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的武俠小說。

小說的主線情節沒什麼太出奇的地方:偏居西北一隅的燕陵镖局突遭滅門之禍,當地的捕頭俠(bu)骨(zhi)丹(shen)心(qian)代為出頭,卻被镖局唯一後人委以重任,自此深陷巨大漩渦。參與這個漩渦中的不僅有武林門派,還有朝廷要員,甚至牽扯到前朝遺案。小捕快一路逃亡,相繼引出落地舉子、朝廷軍官和英俊幕賓這三個主人公,在以明英宗、明代宗兄弟為原型的時代背景下上演了時間跨度長達二十餘年的跌宕人生。
等等——這就是你說的寫給三旬老漢們的武俠小說嗎?故事梗概沒有什麼太多的過人之處吧?情節上,已刊發的部分裡的确沒有宛如人生初見的驚豔橋段,甚至于說對于閱讀量大的人而言有些情節都似曾相識。大結局雖然大坑未填,可大體也能猜到會如何收官,也談不上太多出人意料。可恰如一道菜并非總以食材珍異取勝一樣,《英雄志》有它自身的特别之處。正是這些特别的地方,讓它顯得和而不群,自成一家。
第一個不同,在于它沒有駐足于武俠、技擊、權謀、宮鬥等小說常見的窠臼之中,也沒有落于影射、喻義、表征等小說家鐘愛的所謂高級套路之中,而是将觸角伸到人性的善惡、命運的起伏、世事的無常、現實的冷酷這些更高維度之中,不斷的将這個世界的斷層、切片、透視,扥出來曬給你看。某種意義上說,它與《三體》有異曲同工之妙:無論是硬科幻還是硬武俠,最終讓我們為之魂牽夢萦的其實是人類自身的人性與命運。如果說《三體》是關于未來時代人類生存的物理空間和族群命運的拟斷,《英雄志》則是在人心和命運相互交織糾葛不斷下的描摹。

第二個不同,在于它的“去中心化”結構。多主人公式小說并不鮮見,耐心點可以從《水浒傳》一路數到《冰與火之歌》。但即便偉大如《水浒傳》和《冰與火之歌》,也往往疏于對支線情節和小人物的着墨,讓許多出場的人物宛如評書一般臉譜化、龍套化。《英雄志》以柳門四俊“觀海雲遠”這四個人物為主角,雖然也有主角光環加持,卻走的是“虛拟人生”路線——每個人都像桌球,被命運撞到後滾開去,引起一系列看似随機實則早有定數的後果。沒有誰是命運的寵兒,誰都是别人生命裡的過客。這種“去中心化結構”,卻不正恰好如我們的人生?你以為你站在世界的中心,其實隻是因為那是别人為你特意繪制的地圖罷了。而你以為你掌握着自己的命運,其實不過是一連串拘囿在方寸之間的無序撞擊。
第三個但不是最後一個不同,在于每個人都看似渾渾噩噩卻又不得不背上宿命的十字架,在努力抗争和甘于順從之間反複搖擺。除了《天龍八部》和《俠客行》裡多少探讨過一些命運的主題外,金古溫梁柳蕭大多數作品就像好萊塢電影,情節主導故事。《英雄志》情節的背後,讨論的卻是理想總是輸給現實、人性和欲望的鬥争這些并不怎麼愉悅的話題。這些話題讀起來一點都不快意,甚至會讓人胸悶氣短、如鲠在喉,可又暗暗稱是、心有戚戚。某種意義上,《英雄志》其實有些反英雄,因為筆墨更多的放在英雄的弱點、人性的弱點方面。在一本武俠小說裡認真嚴肅的讨論哲學命題,這本身就是一個挺讓人深思的話題。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